“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国有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2009年央视一套的开年大戏《走西口》,被认为是曾轰动一时的电视剧《闯关东》的姊妹篇。《走西口》以山西人外迁的300年历史为大背景,把晋商文化的背景进一步放大,展现山西人拼搏奋斗的历史。《走西口》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大戏,不如说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文化寻根之旅。
这其中一段段厚重的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历史上的“西口”到底在哪里呢?这条路是如何被打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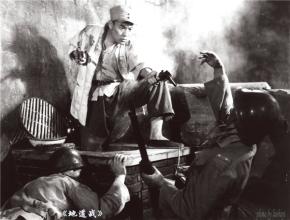
从杀虎口开始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
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距右玉老城仅10多公里。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杀虎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长、宽、高、厚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又于东西筑墙相连,成掎角互援之势。
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走西口的“关口”
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
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至今,在杀虎口那条著名的石板路上,当年晋商的车辙痕迹有十几厘米,足可见当时的繁华。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正如一位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所言:“当年南面的人上来,到在这儿来说了,一爬上这个梁,就可以看见下面(两条路),这就是说‘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这意思也就是一个顺口溜哇。”
没有把握,走西口的人们就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就等于到这儿扔鞋板,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西口、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
其实,走西口的人群中,也有经过千辛万苦而成功者,并出现了新的商业群体。成功者的榜样,给走西口的人们带来的希望。比如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王相卿(太谷人)、史大学、张杰(祁县人),当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军队深入漠北因粮食供应困难,特准商人随军贸易时,便充当随军肩挑小贩。清军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军队供应需从杀虎口运送,王相卿三人便在杀虎口设“吉盛堂”商号,经营粮食等贸易。大盛魁结合蒙古地方特点,组织货源有针对性,经营手段有灵活性,逐渐占有了喀尔喀蒙古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内蒙古各盟旗市场,并获取了高额利润,据说逢三年分红,每股可达万余银两。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7000余人,贸易额1000万银两左右,号称可用50两元宝,铺一条路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走西口尽管是一次由内地向塞外的大移民活动,但其最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就是推动了塞内外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