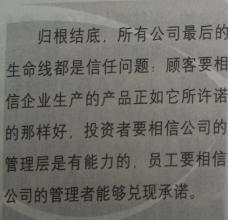1. 关于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
关于制度变迁方式,林毅夫和诺思等人对此均作过精辟的概括和阐述,我们首先对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作简要的介绍。
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的方式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他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获利导向性决定了只有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利益集团才会推动制度变迁,在初始制度安排的范围内,人们不可能得到外在的利润,外在利润内在化的自发性反应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通过命令和法律的引入消除制度的不均衡而实现的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国家与其他人一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他只有在下面情况下才会提供制度供给的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的预期边际费用。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诱因就是政府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诸如换取的税收收入,政治支持等等。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社会权力中心,在提供新的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成为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
不同变迁方式划分标准的核心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问题。制度变迁方式存在差异意味着政府主体和民间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和作用各不相同。
表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
相比之下,诺思等人对诱致性变迁更为关注,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所以,那些创新出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团体)才能够获得潜在利润。某些人或这些人组成的团体意识到潜在利润的存在,他们将受影响的当事人组成一个初级行动团体以获取这些潜在利润。如果一个或多个经济可行的安排确实存在,行动团体将选择一个报酬最高的安排。在决策时,他们必须考虑以下事项:潜在收益,组织成本,经营成本,非想要决策的“阻滞成本”(如果他们的选择涉及政府)以及分配这些成本和收入的时间。
一个制度的改变可能涉及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可能涉及由自愿的协议组成的团体,或涉及被结合在一起或其影响决策的权力被置于政府管理的这类团体。他们将制度安排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的制度安排,自愿合作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性的制度安排。原则上,一个安排的创新者会面临着在三个层次中选出一个或全部这样的安排的抉择。安排出现于哪个层次,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哪些因素是在个人、自愿合作的和政府安排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诺思等人认为,制度安排的创新到底会选择哪一种方式,这取决于该方式的行为主体需要付出的成本与可能获得的收益,以及受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和非市场力量。
一般地,个人的安排不需要支付组织成本,也不要支付“阻滞”成本。而自愿安排则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因此,它要支付组织成本,但没有“阻滞”成本;而政府性安排则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因而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也要支付“阻滞”成本,不过,由于它在作出决定时不需要有一致的同意,只要符合相互认可的组织程序即可,给定同样数量的参与者,它要支付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在政府安排下内含着一个追加的成本要素。每个参加者都受制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不管他对政府的强制性方案有多大的不满意,他都不可能退出。不过,一个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会产生极高的收益,因为政府可能利用其强制力,并强制实现一个由任何自愿的谈判都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我们注意到,诺思的制度安排三层次实际上是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层次的细分,而对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诺思的模型中,进行制度安排层次选择的决策单位(即初级行动团体)并不包括政府,在政府性安排中,政府是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出现的。政府性的安排特指那些由民间团体作为初级行动团体,同时需要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情形。
表2 制度安排三层次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对典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进行了区分说明,但是无论是林毅夫还是诺思,均对制度变迁方式的多样性及复合性持肯定态度。制度安排的形式,从纯粹自愿的形式到完全由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形式都有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半自愿半政府结构(诺思)。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林毅夫)。
.2 风险资本市场生成方式分类诺思和林毅夫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风险资本市场生成方式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是传统资本市场发生的一种制度变迁,它是行为主体响应传统资本市场在融资制度安排上的非均衡性所引致的“外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借鉴林毅夫对制度变迁方式的区分,我们将风险资本市场的典型生成方式分为强制性生成和诱致性生成两类。
风险资本市场的强制性生成是指,政府在响应传统资本市场在风险企业融资方面的制度非均衡性引致的政府效用改进机会时,政府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在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通常表现为政府作为权力中心,利用其强制力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融资安排),从而导致新的资本市场形态——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
风险资本市场的诱致性生成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传统资本市场在风险企业融资方面的制度非均衡性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通常表现为由民间主体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融资安排),从而导致新的资本市场形态——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
正如诺思制度安排三层次所指出的那样,在风险资本市场诱致性生成方式中,作为初级行动团体的民间主体将权衡自身从制度创新预期可以获得的收益和可能要付出的成本,以制度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中作出选择,即个人的安排、自愿合作的安排和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性安排。个人的安排是指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融资的制度安排在个人水平上出现;自愿合作的安排是指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融资的制度安排在自愿合作的水平上出现;政府性安排是指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融资的制度安排在民间主体主导、政府辅助的水平上出现。
微观“外部收益”可以激励民间主体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以捕获潜在利润。宏观“外部收益”来源于资本市场融资制度创新的外部性,其直接获得者是政府,因此,理论上,政府具有资本市场融资制度创新或辅助创新的内在激励。但是,由于宏观“外部收益”获得的途径有别于一般的“外部收益”,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与民间的制度创新激励有所不同。
微观“外部收益”必须是民间主体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方能获得。而宏观“外部收益”的获得可以有两种途径:1)民间主体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使政府从中受益,即获得宏观“外部收益”。进一步,如果政府意识到外部效应而进行辅助创新,可能使宏观“外部收益”提高;2)在民间主体未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不能产生外部效应,政府自行进行制度创新,以捕获宏观“外部收益”。因此,政府是否作为初级行动团体启动创新取决于民间主体行动与否以及其进行制度创新的盈利预期。如果民间主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不足以超过预期的成本,民间主体的任何一个层次上的创新行为都不会发生,从而不能给政府带来由外部效应引致的宏观“外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受宏观“外在收益”预期的激励,将率先作为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启动制度创新的进程,从而实现传统资本市场的强制性变迁。

表3 风险资本市场两种典型生成方式的比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