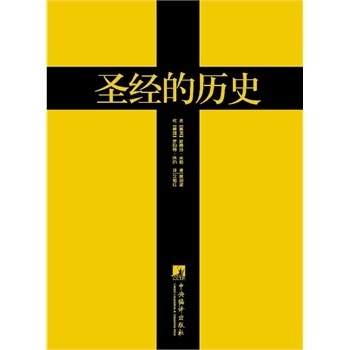心灵与其表象之间有一条鸿沟。如果它外在于我们,永恒存在于世界中,或者超越于这个世界,我们怎样才能把握住它呢?
—— 涂尔干
《标准》对网民和青少年的边缘化误区
11月8日,《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网络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心目中,汉语的“精神病”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概念,而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性词汇,其潜在含义几近于“疯子”、“无可救药”,基本上等同于宣告个体对社会的边缘化。一石激起千层浪,究竟《标准》涉及多大范围的人群无法细算,但《标准》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3个月。如此算来,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少的上网人群可以适用该《标准》。

根据《标准》,判断网络成瘾的条件(选一):因使用网络而减少或放弃了其他的兴趣、娱乐或社交活动;将使用网络作为一种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的途径。与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占用网民上网时间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传统社交活动SNS,作为网络时代帮助人际交流突破地域和空间限制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代表(FaceBook)甚至与奥巴马的竞选班子结成战略合作,为其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SNS自诞生伊始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和思维方式多元化的产物。如同其缩写所表明的,“S”——社会价值是其目的,“N”——网络作为其途径,“S”——服务、系统或者软件作为形式。这一目的的实现手段和表达方式,以解释和解构化的关系体现社会价值的经验和基础。在互联网已经深入全球化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每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SNS可能成为体现和反馈社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将来成为垄断性的社会价值需求所在。
作为互联网生活和互联网心理的代表产物,SNS恰恰是民众的需求所创造。布莱希特说,“我们的民众,不仅全力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占据历史、加快它的前进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在我心目中,他们谱写了历史,改造了世界,也塑造了他们自己。”因为在互联网文化的内核中存在着人性需求的真实情感,所以它冲击着传播、媒体与教育领域,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出任何对传统的“回归”景象;而我们的学者却太过世故了:尽管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失效,但学者们的研究却明确表现为一种思考的矛盾:用过去的形容词和概念,来作当今的审核。
在我看来,医学既不应当被人当作哗众取宠的幌子,也不能用来作为一个过度裁判的借口。如果我们忽略掉《标准》所不当涉及的大部分因工作、社交需要而长时间上网的使用者,那么所谓网络成瘾很大程度上只是上网者(根据《标准》制定者的解释,主要是青少年)的一种角色模糊或者角色危机。
互联网和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我们能够在技术上(无论游戏还是社区)轻易地实现角色自主和视觉再造。对于成长过程中尚未定性的青少年来说(这部分人群被《标准》制定者视为主要对象),在其所在的家庭与局部社会不能够正确承担其成长历程中的角色塑造和心理引导的时候,以往的趋势是选择逃避或者自我封闭;而在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社会日益发展甚至可以用虚拟的角色完成部分现实职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自然和快捷地选择通过网络去实现一个被模糊或者被扭曲的自我;其实如果观察者能够置身网络,也许可以发现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健康角色(虚拟)的他们存在。这说明一个寻求独立和暂时脱离现实的角色正在被补偿性地自我塑造。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脱网(类似于脱敏)方法只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我们从《标准》能够看到的现象是,医学与教育关注的更多是新问题与他们熟识的旧问题之间的结构性相似,而对“网络成瘾”背后的全球化、互联网化所蕴含的社会转型意义缺乏重视。这与全球化和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是极不相称的。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一个环境,全球化也并非救世福音,它给社会带来的危机感和压迫感是无法避免的,自然也会动摇传统医学所能够轻易解释和治愈的心理病例。用《标准》这样的方法来引导甚至解救因互联网应用而导致人的角色危机,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网络与毒品、烟酒不同,它无法从生理上麻醉人的神经系统和官能器官,至多只能成为人情绪、心理的排解工具和手段。虽然治疗方法和定义范围虽然有争议,但不同立场的医学专家却有相当的共识,职业性地将不同于一般习惯和反应的人当作病人,然后量化症状,再从药物、手段等方面下手。然而他们没有形成从人性关怀进行思考和分析的逻辑:究竟是网络造成青少年脱离家庭和社会,沉浸而不能自拔?还是青少年在家庭和社会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怀和正确的塑造,转而寻求网络的疏解和补偿?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被号召将世界看作是根据自己的目的控制和形成的一个环境。现代性创造出了一种自我控制的理想的个人,能够应付已经非自然化了的现代生活,应对愈加复杂和分化的社会结构所需的各种期待。然而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这一理想标准。如果将问题的分析简单地脸谱化,就会得出《标准》这一类主导文化需求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不均衡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离开互联网和全球化文化的具体环境,《标准》的描述只是一个医学的老生常谈,而不是具有什么创造意义的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真知灼见。如果无限地扩张理性,会使理性脱离自律,成为目的本身,从而导致与手段的错位,损害主体自由和人的生存价值。就像人不是上帝一样,理性也不是现实的造物主,决不能被当成不符合原有体系的新生事物的对立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