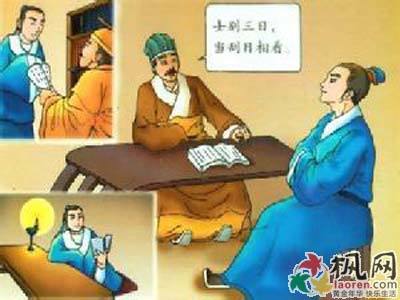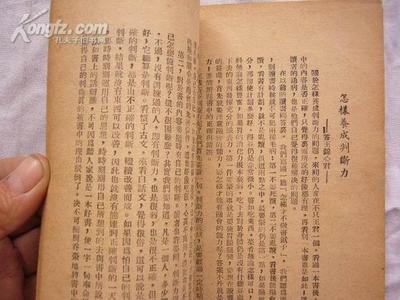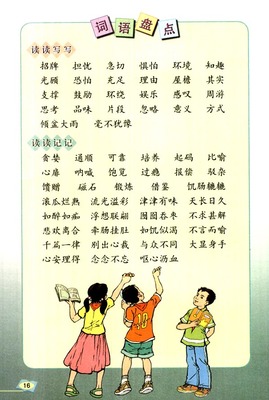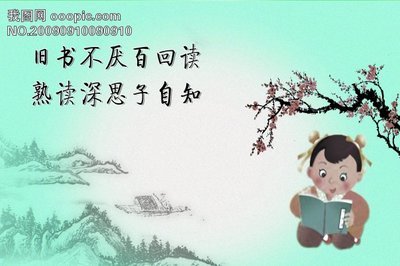人生最大的无趣在于,我们不认同别人认可的标准,却又渴望别人的认可,爱情如是、事业如是、生活亦如是。前者是我们渴望脱俗,后者是我们未能免俗。当我们在对方的标准里做不到最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的标准是否牢靠。所以,一辈子,我们都在征服对方和劝服自己之间不停徘徊纠结,大部分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一生。 关于读书人为什么要读书这件小事,先贤高人给出过许多无可指摘的定论: 哈佛教育学生:“读书的痛苦是一时的,不读书的痛苦是一生的。” 马克.吐温说:“读书让人变得文雅和仁爱。” 《论语》中对为学有详细描述,如:“人之于为学也,学之,人也;不学,禽兽也。” 以及最世俗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乃至最崇高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读书是一个开始,去帮助自己变得犀利,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心灵,为了生存,为了功利,为了改造世界的抱负,貌似总之是要为点什么才不会辜负读书这个行为,似乎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的人就不称其为一个读书的人。 于是读书姿态常常是这样一种标准模式:一卷在握,正襟危坐,每个细胞都很紧张,只为在最短时间抓出要领,形成记忆,帮助分析……可就是没有发自深心的感动。 近日,遭吐槽甚多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诠释的成功学貌似能代表大部分六、七十年代人的读书观:被欺负的小孩子,通过拼命努力,致力于终有一天变身为成功人士,搞搞致青春,时不时回忆一番曾贫穷且奋斗的往事,继而转头去欺负那些曾经欺负他的人,又伤感又美好,还挺解气。 那种实用主义的得意,其实充满了无奈。但也或者,这就是每个人寻找答案的开始。 夏尔·丹齐格在其著述《为什么读书》中提出:读书为理解世界,读书为理解自身,若读者再稍微大度一点,那么读书也可能是为了理解作者——确实如此,好比人生。 我们最初始于无知,因而对外界一切好奇,我们尝试理解世界的规则。随着成长,我们逐渐看懂世界的规则,觉得世界发生的一切正常合理,这时我们就开始由看世界反观回自己。理解自己并学会控制自己与自己和谐相处是很难的一门学问,而真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摘掉有色眼镜再去关照世界关照他人,既理解他人。就好像不知道谁曾经说过,人越成熟,越发现身边的人难以责怪,因为每个人做每件事的原因都显得合理了。 书的魔力任人皆知。人生苦短,存在无涯,幸亏有了书,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才能把见闻扩大无数倍,在书中流连忘返,善于汲取菁华者,是珍视人生的本质与自由的人。 也许有一天,人终于到了某一个年纪,时代终于轰隆隆开进某一个站台,我们终于可以放下所有心结,不用太在意好与不好、正确和错误、昂贵或廉价的事,转而去关心的是:喜欢与不喜欢。我们曾经那么渴望坚持自我,又那么渴望他人的承认,而后者本身就是对前者最大的否定。 真希望能够快一些进入那样一个次元,人们不用继承某种屈辱、不用承担某种压力,不用奋力站起来证明我们能站起来,能想躺着就躺着,只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躺着。以及,想读书的时候就愉快地拿起书,沉默地阅读,不觉天已黄昏,人渐渐睡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