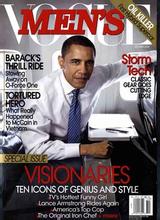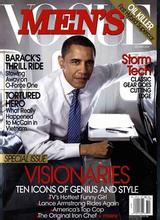系列专题:《白领世界真实体验: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我感到和莫顿还没完,我至少应该完成那个测试,让他拿到60美元,也许还能补偿那些已经与他共度的时间。WEPSS有200多道题目,每一题都以词和短语的形式出现,让我按从A到E的顺序标出这些词对我的适用程度,比如,干练、寻乐、力量、和平使者、报复心强的。我坐在餐桌前,准备最多用10分钟把试题浏览一遍,但是它却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容易。我“特别”吗?从哪个角度来看呢?怎么看“外表养眼”?或者“与众不同”在哪些方面?大多数题目都是形容词,比如说“爱评论人的”,但是也有很多名词比如“梦想”,甚至还有许多动词,比如“反对”,我能描述自己“从来不、偶尔或者几乎总是反对”吗?还有我是“有时候”、“从来不”,还是“总是大惊小怪”或者“没什么大不了”? 即使题目的语法不会令一个专业写作者—或者,我应该说“沟通专家”—感到愤怒,其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比方说“和谐的”,有时候还算吧,不过这取决于你要与之和谐的人与环境。避免冲突?有可能的话我会,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其实更喜欢来一场拍着桌子对阵的辩论。“你有权威吗?”“你快乐吗?”天哪!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会说自己“不属于某种类型的人”。 我们一直在寻找答案的性格,似乎对我,对其他任何人也一样,都只具有相当有限的适用度。自己是另一个让人困惑的概念,因为当我把这个“我”仔细地审视一番,发现它只不过是一大堆由各种忽隐忽现的关系、习惯、记忆和偏好组成的混合体,它们可以导向任何结果—依赖或独立,勇敢或怯懦。我决定,最好的策略就是避开“犹豫”、“易焦虑”和“吹毛求疵”等词汇,然后给出大家公认正确或最容易引起称赞的答案。于是,我为“几乎总是”这一条选择了“训练有素”、“充满理想”、“独立”和“有原则”,同时坚决排斥“懒惰”、“爱挑衅”、“拖沓”和“过分松懈”。 一周之后,莫顿终于抽出时间来为我的性格“评分”了,于是我们约在他家见面,以便共同探讨评分结果。他的家在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居民区里,是一幢朴素的庄园小楼,据我观察,其装饰属于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天主教风格—到处挂着19世纪的田园风景画,一个泰迪熊坐在儿童摇椅上,麦当娜在画上俯瞰着壁橱。换句话来形容,这里实在太普通了,至少在我看到餐厅的桌子之前是这么认为的。那桌子上赫然摆着几个高达3英尺娃娃—一个稻草人、一个锡人、一只狮子—这是哪部电影来着?还有一个塑料做的猫王! 我打算开始就表明我对这个测试的批评和不满,因为如果我知道测试结果之后才抱怨,他也许会认为我在利用结果,并曲解结果中对我的任何批评。我问他,到底怎样才可以说“营销”(这是测试题目中的用语)适合形容我?那明明是个名词,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也许“擅长营销”,但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象力,也不可以说“我不营销”啊。我告诉他,对于这样的不精确,是没有借口解释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么说也许刚好暴露了我性格中僵硬和不肯原谅的一面。

莫顿对我的批评泰然处之,他从箱子中拿起猫王娃娃,娃娃的双腿向右伸出,支撑着它的身体,摆出一个丑陋的姿势。他告诉我,这个娃娃可以说明一个观点,即“娃娃和真猫王之间的相似性就如同我和我的性格类型之间一样”。我想反对,因为这个娃娃并不像真的猫王,也许像他年轻没发福时的样子;不过至少任何人都一眼看得出那并不是一个芭比娃娃。但是如果这个测试毫无意义,我在这儿干什么?它和找到工作又有什么关系?莫顿把娃娃放在旁边桌上,让奥兹国的国民们自己一边待着。 我们开始讨论测试结果。原来我的分数“可以说适合任何一种性格类型”。在原创力和效率方面我得分最高,在九型人格图上标出来,诊断线指向“好人/充满爱”,于是结果表明我属于锡人类型,还带点狮子性格,莫顿一边讲解一边用手指向相应的娃娃类型。接着,他拿出一大堆让人困惑的幻灯片,它们一直都在旁边的文件夹里放着呢。这次,我决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当他打开一张写着“九型人格象征”的幻灯片,看着那3个重叠的三角形,我就晕了,唯一想得起来的问题竟是:“这个圆圈是干吗的?”他解释说:“是为了图形的和谐。”—他仅仅是喜欢它的形状吗?—当然也是为了表示“我们所讲的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大三角形呢?我怯怯地继续问,越来越没有勇气。“那是智慧的3个中心。”他回答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