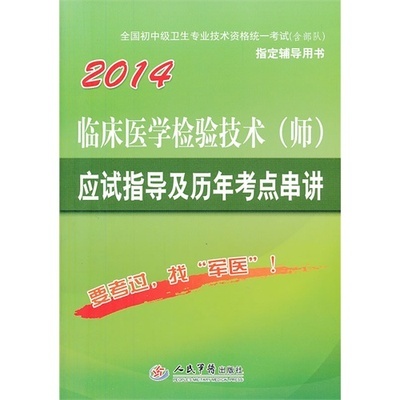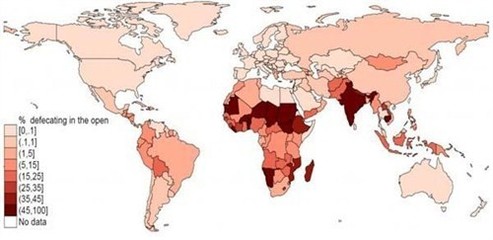在2006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典著作缩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值。
两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相关的出版校订编辑程序,即将正式将该书付梓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从华尔街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从纽约、伦敦到香港、上海,环球同此凉热,大家都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金融海啸”,都沿用格林斯潘先生等对于此次危机的判断“百年一遇”。
既然是百年一遇,自然只有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以媲美;而对于“大萧条”,从金融方面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之一,大概首先应当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了。
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人们必然会像是在此前的多次危机中一样,感到迷茫、困惑,在这个时期往往也空前关注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试图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方向感。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在危机中似乎也都呈现一个有趣的类似特点,在大牛市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是十分年轻、新锐、激进的专业人士,因为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牛市中的最大利润;而在大的调整时期,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受欢迎的,则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的资深专业投资家,因为他们在大的动荡中更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个独立而可控的影响经济很大的力量。(The main point of A Monetary History is that "money matters: " The quantity of money is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force that strongly influences the economy)。在经济历史上,可能难以再找到比当前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当前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正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刻受到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因此,在即将付梓之前,我特地对两年前的后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向读者推荐这本从原来的专业金融史著作,却因为时势关系可能变成畅销读物的种种原因。
实际上,在2005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翻译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的成名作《美国货币史》的出版合同时,我其实心中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此经典的巨著,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然有许多特定的原因,例如难度过大,翻译工作过于艰苦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的金融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中译本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我自身也深刻体会到当年上学时期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的一系列翻译名作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有鉴于此,我以“聊发少年狂”的心态,组织了我的多位研究生,开始了这项艰苦的翻译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内的中文读者能够尽快看到一个大致能够掌握弗里德曼教授思想全貌的机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瑕疵。不少的业界同仁知悉我在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时,都多次询问此书的中文本何时可以出版,我一直以“不能着急、慢慢来”回应,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复他们说,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当然这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统稿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2006年末我们完成了统稿,书稿也提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也陆续在境内外的媒体上见到了不少悼念的文字。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辞世一样,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报道,然后开始寻找新的热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来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对我们来说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之外,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现在我再次修订后记时,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投入了四五年的时间。
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变得反而并不重要。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呈现出来。
我们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研究生,竟然如此机缘凑巧,承担了这个翻译的重任。
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过,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由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以及近期的集中再次修订,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金融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译著的出版,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做 “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软件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本书的翻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底完成初稿,经过出版社两年的编辑整理,我们又在最后阶段由巴曙松、王劲松和牛播坤集中对全书进行了再次的校订,初稿翻译的参与人员分别为(根据参与翻译的顺序):巴曙松、刘先丰、吕国亮、方磊、程晓红、刘润佐、牛播坤、矫静、郝婕、尹竹青、陈华良、向坤、王凡、王淼。其间,王劲松、伍刚做了许多有益的协调工作。之后两个月组织了相互校译,在2006年中完成的初稿中发现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庞大的翻译团队加大了语言风格的统一以及对全局把握的难度,即组织了几位进行集中校对,包括: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伍刚、王凡、牛播坤。此次校对主要集中在语句和措词的修正上,但限于校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发现往往还是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在参与翻译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尝试对各章采取了小组集中讨论的形式,即由我来主持,一名同学负责主要修订,其他同学讨论前也需认真阅读并提出校对意见。不仅从语言上确保用词的准确性,还可以在相互讨论中理顺作者演绎货币历程的基本思路,深化对该书的理解,以求完整传达作者的表述。在此期间,我们组成了三个讨论小组,并在小组内设置了审读员。审读员均是之前未参加过翻译的同学,只负责从中文的行文习惯上考察翻译的可读性。三个小组的成员构成及其负责的章节分别为:第一组:吕国亮、程晓红、方磊、李晶(审读员);第二组,牛播坤、刘润佐、矫静、张旭(审读员)、赵晶(审读员);第三组,向坤、王凡、郝婕、王俊(审读员)。经过此轮集中校订,翻译质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遗留的个别难句由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牛播坤负责。随后,我又组织进一步进行了小组间的交叉校订,并由上一轮的小组负责人审定此轮所做修改。附录部分的校对王淼、向坤、王凡、谢国良、李辉雨、王琳璘、张铮和任杰等同学参与。在最后阶段的统稿和协调方面,张旭和王凡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大约五至六次的校订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承担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尽可能的查漏补缺,唯恐辱没经典,希望能以程序的繁复和巨大的投入弥补我们自身水平的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在下一步的校订中继续提高改进,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金融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发端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研究案例。我们一直在事实上把欧美金融体系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现在这些重要的参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和危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只能更多依靠深入分析欧美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和中国自身的金融需求中来寻找。因此,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引导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