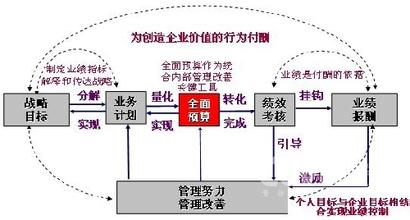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他提到,在公元前11000年的冰期时代,各大洲的早期人类都是狩猎和采集为生,然而从那时至公元后1500的漫长历史中,他们以不同步伐走在进化的道路上,形成了发展上的落差。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人仍在游猎和采集,而欧亚大陆的人类已产生了高度文明,发展起农业、畜牧、金属冶炼和复杂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原因?
他认为是客观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进化速度。首先,人类进化取决于创新的普及。从地理布局看,欧亚大陆是东西向的,气候环境类同,在某地产生的创新也适用于其它地方,所以有利于新技术的普及;非洲和美洲都是南北向的,气候相差悬殊,在某地的创新难以运用到其它地方,创新的普及就受到限制。其次,人类进化始于农牧业的发展,而农牧业的进步又取决于驯化野生植物、动物的进步,可这一过程又受限于自然界可供改造的动植物的种类。大自然为各大洲提供的机会不是均等的,欧亚大陆比其它大洲有更多的选择,从而在农牧业发展走到了前面。总之,欧亚大陆由其环境因素而取得了更高的文明成就。
所以,戴蒙德认为人类进步的差别不是由于智商、体能、生理的差别, “各大洲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进程绝然不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素质的不同,而是在于他们生存环境的不同特征。”
压力是前进的动力戴蒙德的观点予以我们极大启示,但他有些解释是不充分的。首先,看地理环境,欧亚大陆尽管是东西向的,但因地理的障碍,早期人类的东西交流几乎不存在,而中国的古代文明也是自北向南扩展的。其次,以自然环境的不足来解释美洲的落后也令人难以信服。大自然对南北美洲应该是慷慨赐予的,如北美东西海岸地区土壤肥沃、雨量适中,气候适合于植物生长,而薯、玉米、土豆、花生、辣椒等都是源于美洲,再传到其它大洲。欧亚大陆驯化了如野牛、野猪和野羊等野生动物,美洲也有同类动物,却据说因性烈而无法驯化——但今天已驯化的动物最早也可能性格刚烈,是在长年的驯化中被改变了。美洲人为什么没有如其它洲的同类那样,把更大努力用于动物驯化呢?
把亚洲与美洲的环境相比较,也许能给以我们新的启示。据考证,美洲早期人类来自于亚洲。约在30000到65000年前的冰期时代,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或是结冰,或因地质变动露出床底,亚洲人类在游猎中跨过海峡去了阿拉斯加,然后自北向南地逐步拓展,他们也就是印地安人的祖先。
然而,在历史的过程中,亚洲人取得了巨大物质进步,美洲人却长期滞留在部落社会、狩猎、刀耕火种的阶段,直到近世纪被欧洲人以洋枪洋炮征服。我们中国人与印地安人可谓同祖同宗,为什么在发展上却是天壤之别呢?
我们认为,根本的解释在于生态环境的困难程度,是这一差别造成了人类进步的差别。美洲良好的综合环境,使早期的居民很容易地从自然界获得足以生存的衣食。没有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安于现状,缺乏寻求物质进步的强大动力,从而在进化中相对落后了。所以,印地安人之所以遭受到近于种族灭绝的浩劫,不是源于种族的低劣,而是因为他们置身于较优逸的环境。
相比较,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恶劣得多。今天,人们把黄河流域看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其实,中国其它地方也有早期人类存在,但黄河流域的的居民走到了文明发展的前列,在扩张中征服了其它地区的“蛮夷”,再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逐步地发展起了中华文明。
那我们又要问:为什么是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或其它南方地区的人类走到了进化的前列呢?——就因为那里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
历史上记载了大禹治水。也就是说,4千多年前,人类就已面对着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的威胁。水灾如此严峻,使得大禹治水有功就能受禅为王。那里的居民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奋斗,“穷则思变”,是求生的本能促进了他们在农业、工具制作、政治组织上的进步,使他们在与自然抗争中崛起,走到了进化的前列。
不同人类群体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不同生产方式的对抗,中原文化能够征服“异族”(或被征服后再同化他们),就因为它当时是最先进的。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不是因为“聪明”,而是环境的恶劣促使他们逆境崛起。

压力过度则为破坏性
如果恶劣环境促进人类进步,那又要问:西藏、青海、新疆等地的生态环境更为恶劣,为什么最先进文明没有产生于那里,为什么不是那里的部落民族征服中原,成为华夏文化的起源地?
显然,环境过于恶劣也不利于发展。所以,还得有个附加前提:恶劣条件不可超过一个极限,否则将适得其反。
可以行为学专家弗洛姆(Victor Vroom)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来解释。根据此理论,激励模式为:个人努力à个人绩效à组织奖励à个人需要。而这个期望模式中的四个要素,是体现了三种关系:(1)员工预期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实现目标;(2)预期目标实现目标后将获得奖励;(3)这个奖励对于他又是很需要的。只要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就能产生出巨大的激励作用。
我们姑且以期望理论来解释古人类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心态和行为。那些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土地贫瘠、风不顺雨不调、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他们要生存就得想办法:抗洪就要筑坝修渠,这就导致了中央集权政体的形成;提高产出就要建造梯田,改良耕作技术,这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他们全力以赴,是出于危机意识,更是因为他们相信努力能够改变生存状况。
然而,青藏高原的人们面对着更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使他们无法相信努力能改变结果,也就放弃了努力,生活就不过是苟延残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命或宗教上。为那种心态支配,文明进步也就缓慢了。
总而言之,我的假设与戴蒙德一致:当历史把某个民族置于一个最佳的自然环境中,也就奠定了她的崛起基础。但我进而认为,所谓的“最佳环境”是指使人们面对巨大的生存危机,但又不至使他们放弃求生意念。这也就是我所提出的“最佳逆境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Hardship)。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