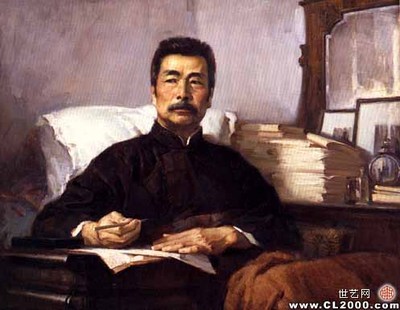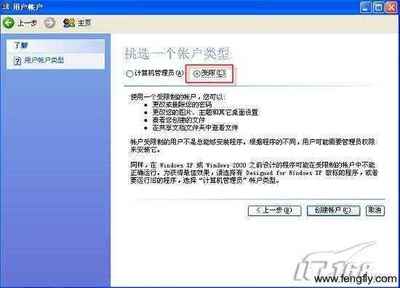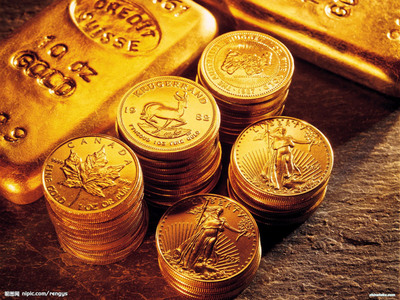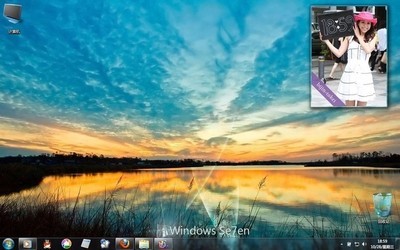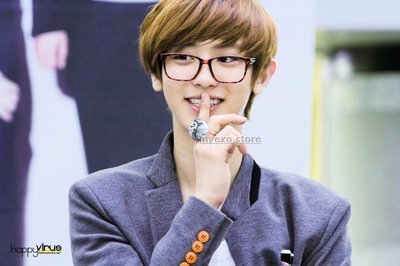巴曙松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而对于我来说,闻潜教授的逝世,更让我在悲情的气氛下,多了深深的伤痛。在喧闹的香港,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在伤感稍稍平静之后,我终于可以提笔,写一些文字,送别我的导师闻潜教授。
我在闻潜教授门下学习三年,收获甚多,无论是就读期间还是毕业之后,闻老师对我一直颇多关怀鼓励。在不断前行的道路上,我总能感觉到闻潜教授关心和期待的目光,让我感到温暖,成为督促我不断努力的重要力量。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正是因为成为习惯,所以也就习以为常地认为,这样的关注的目光一直就在那里,始终是我们这些学生的挫折与艰难的分担者,成功与快乐的分享者。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心理上并不觉得与闻潜教授有多远的距离,尽管只是不多的电话联系,次数不多的见面和聚会。
直到这一天,闻潜教授西去。
因为这段时间在香港工作的缘故,在北京的时间不多,一天我正好在京,有同学告知,闻潜教授病重住院,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闻潜教授了,几位同学约好到医院看望。为了不过多打搅还十分虚弱的闻老师,大家都约好只是简单到病房看看,简单说上几句,就出来了。我进门之后,闻老师很是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因为怕多说话影响恢复,简单寒暄之后,就从病房中退出来了。尽管一直知道闻潜教授身体并不是很好,但是这一次亲眼看到闻潜教授的身体如此虚弱,说话吐字都不是很清晰,隐约感到伤心和不安。
没有想到这匆匆一见,竟成诀别。
第二天我返回香港后,有同学就短信告知,闻老师病情又恶化并且进入重症观察室,与外界已经没有交流。中间也一直通过不同渠道询问闻老师的病情,希望真的是如同我在病房安慰闻老师时所说的,也不是什么大毛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养病不能着急,慢慢恢复,我们等您出院后再来看您。直到26日,同学告知,闻潜教授逝世。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从闻潜教授身上学到了许多。在悼念闻潜老师的时候,在闻潜教授门下学习期间的种种,彷佛就在昨日,历历在目。
长期以来,中央财经大学在培养财政以及金融会计等专业人才方面有卓著的成绩,毕业的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在财政和金融领域。但是,这种相对狭窄的学科设置,以及过于强调实用化的教学风格,也在事实上制约着这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研究能力的提高。当时,中央财经大学面临的一个现实约束,就是因为博士点的缺乏,导致缺少对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平台。闻潜教授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点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也是这个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被师生们私下称为“首席博导”。与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博士点学习的前面几届的同学,有不少都是中央财经大学的青年教师,通过这个平台的学习,现在都活跃在中央财经大学的不同专业,成为这个学校的骨干力量。
与财政、金融、会计等相比,经济学是更为基础性的学科,在中央财经大学这样一直十分强调实务训练的大学,经济学科教育的强化,也促使学生有更为扎实的经济分析基础和更为灵活的适应能力,这对于一个学校学科建设的完善,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履历看,闻潜教授应当是同龄人中的优秀者,他1949年3月就读于华北大学, 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 1953年7月研究生毕业,此后一直在首都高等学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从当前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看,他和他时代的学者一样,接受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训练。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钻研精神,以及分析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把握,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许多的教益。但是,与不少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不同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成为他面对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现实经济问题时进行研究转型的障碍。他在娴熟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同时,很快汲取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在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著作,简直就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位勇于探索、具有深切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探索历史的代表,在经济转型刚刚起步的时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趋势,先后推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3月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复合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经济失衡并面临经济调控的压力时,他又推出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管理均衡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1月版)、《宏观控制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在宏观调控刚刚成为决策者面临的新课题时,他继续推出了《中国宏观调控通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在经济转型框架基本完成时,他又继续转向对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把握与分析,推出了《中国经济运行--层次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9月版)。翻阅《闻潜经济学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中不同时期闻潜教授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这种不断探索的足迹。已有的成绩,已有的分析经验,并没有成为他前进的包袱和障碍;直面现实的研究勇气,使得他不断突破自己,成为经济学领域一名不断推出新成果的探索者。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是,我看到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不少新的判断,特地推荐到香港主流的财经报纸《信报》发表,也许这对于一个成长于西方经济学教育环境中的学者只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是对于闻潜教授这样的内地学者来说,确实显示了他在不断突破自我方面的过人之处。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但是,闻潜教授这种不断自我突破的勇气,一直成为鼓励我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重要动力。
在《光明日报》2008年6月28日刊登的闻潜教授的讣告中,评价他为“均势市场理论和消费启动理论的创始人”,我认为是十分恰当的,也是对闻潜教授多年来积极探索的理论成果的很好的总结。他很早就深刻意识到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方式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矛盾,也深刻意识到只有启动以本土消费为主导的内需才可能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平稳的运行轨道,并且一直在为此鼓与呼。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再次证实了他在理论上的洞察力,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外需、过分依赖为支持外需所进行的过度投资,而过分忽视本土消费的培育与启动。可以让闻潜教授欣慰的是,经过艰难的转型,2007年消费超过投资,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而2008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之投资和出口会更为明显。
闻潜教授毕生在高校任教,指导了许多学生,从他指导的博士生构成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跨度很大,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颇大,大家私下开玩笑说,闻老师指导的博士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很有特点。我现在也指导了不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对不同类型学生的包容也使我深受教益,在实际的招生中,我也有意识地招收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学生,这不仅体现了“有教无类”的古风,也在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促进的平台,在实务操作上有特长的学生,与理论研究上有成果的学生可以相互学习;在研究机构工作的学生,与在决策部门工作的学生,同样也可以共同交流。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交流,也给我许多的教益与启发。
“夫子不求名与利,后世漫传七二贤”。提笔之际,我仿佛又回到闻潜教授经常给我们上课的他们家中的客厅,休息时抽着闻潜教授的香烟,喝着师母泡的绿茶,与闻潜教授请教研究与论文。
在我写完这段简短的文字之后,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实际上死亡,对于闻潜教授这样的不断探索的思想者和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来说,在学生和家人朋友而言,当然是一种深深的伤痛,但是,当我们翻阅他的著作,看到他的思想的闪耀,看到他的学生的成长,我们也要说,闻潜教授,我们的导师,他还在与我们同行,还与我们同行在中国经济的起起伏伏的探索进程中,还与我们同行在人生际遇的漫长旅途中,无论我们是在什么行业,什么城市。
谨以此文,送别我的导师闻潜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