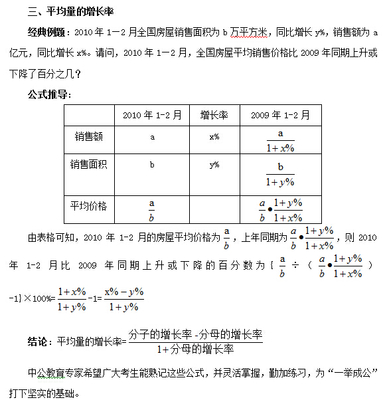下午4点钟,阳光暖暖地照在杨洪武的身上,这是他每天休息时间。在太行山腹地这个仅有50户人家的山村里,杨是个小有名气的“老板”。“一年也就挣五六千块”,杨说,但他对此十分满足。此前,他曾到内蒙古的砖瓦厂打小工,每年只能带回来二三千元。
杨今年36岁,三年前开了这个面食作坊。刚开始他只有一台冰柜,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四台,还雇了5个小工。五个人一天加工的面粉将近两袋,而每做一斤面,每个女工就可以得到0.4元报酬。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项目给他帮了不少忙。2001年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试点带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项目,他们与当地扶贫办合作,成立“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面向贫困农户,发放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小额贷款。2003年,杨洪武向住在隔壁的自立服务社的信贷员李瑞平提出了贷款申请,几天之后,他拿到了2000元贷款。杨用其中1700元买了台冰柜,剩下的全买了面粉,加工厂就这样开张了。
生意越做越红火,杨洪武想追加投资,这次他找到了当地信用社贷款,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们要拿存款作抵押,否则不放款。”于是他只得再次把目光又投向了自立服务社,贷到了第二笔总额为3000元的贷款,拉回了面食加工厂的第四台冰柜。
“小额贷款就是给我们这些人量身定做的,慢慢贷,慢慢还,到年底钱也挣了,贷款也还完了,很方便”,刘评价说。
以一搏十
杨洪武所在的上水磨村,行政上隶属于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全村190口人,年收入不到1500元,是中国中部典型的贫困山村。迄今为止,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福建、贵州、河北、山西、海南、辽宁等地已经建立了14个小额信贷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无一例外都是在国家级或者省级贫困县。
“我们小额贷款项目虽然也是扶贫,但是并不是给农民发钱,而是通过给农民提供微型贷款来支持农民的发展,而在其中,我们也能够获利。”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贷款部主任刘东文向记者强调。
记者在扶贫基金会2006年的年报上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净盈亏表为,2004年为亏损22.3万,2005年为盈利29.1万,2006年盈利52万。短短三年,变化十分惊人。对于这种变化,尤其是2005年的扭亏为盈,刘东文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行政管理成本的降低,二是坏账率极低。由于无法吸收存款,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资金困境,纷纷寻求村镇银行转型,甚至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向记者坦言,其成立之初即意在成立村镇银行。对于这些呼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实践似乎可以证明,变身村镇银行并非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给记者提供的材料中,记者看到,他们这样描述他们以一博十的策略:
我们在每个贫困县建立穷人银行的基本贷款本金规模为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社会、政府和银行三个方面筹集资金:
种子基金200万元,主要是面向社会筹集赠款作为种子基金;
政府配套200万元,一旦有了种子基金,我们就会与当地政府协商,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支持;
批发资金600万元,主要从国家开发银行和渣打银行批发贷款。2006年底,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1亿元的批发贷款授信,目前已经申请使用了3000万;在08年1月份,与渣打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渣打银行同意为小额信贷项目提供批发资金。首期2000万已经到位。不过,每个县的银行批发资金不能超过70%。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200万的本金,就可以达到1000万的资金规模,而且这些资金还可以永久循环使用。
“在扶贫基金会总共8500万的资金中,其中,1200万是赠款,2300万是政府的配套资金,还有5000万我们是商业贷款。”刘向记者介绍说,“我们贷款是商业贷款,要支付8%-9%的利息。而能够做到商业贷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还款的提高,实现了小额贷款项目的商业化运作。”
成本低过孟加拉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项目始于2000年。1996年,世界银行就开始在中国进行小额贷款业务,2000年,扶贫基金会全面接管了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当时中国小额贷款项目区一度达到十几个县,但是04年之后,一下子锐减到了4个县。对此,刘解释说,问题主要出在管理上。当时的做法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当地政府合作,设立一个专门的机头,由扶贫基金会提供技术,当地政府负责管理。“应该说,在运作小额贷款项目上,技术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由当地政府管理,有时候不服从我们的管理。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政府劝说村民不还款的事情,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是扶贫款,根本用不着还。”刘东文告诉记者。
2005年,扶贫基金会做了改革,不再和当地政府合作,而是设立直属的分支机构,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统一管理,其统一的名字是“ⅹⅹ县农民自立服务社”,刘东文是这些直属分支机构的法人代表。
改革并不仅限于此。不和当地政府合作之后,成本成了扶贫基金会必须面临的问题。为了最大程度节省资金,服务社将机构设置分为两个层面,县一级办公室,主要包括出纳、会计等管理人员;以及乡镇一级的信贷员,这些信贷员都是当地居民,对本地的情况十分了解。

“相比孟加拉模式,我们最大的创新就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刘东文介绍说。
孟加拉模式一般是3级管理机构,县一级的办公室,然后是乡镇一级的办公室,然后才是各个村的信贷员,这样在县和乡镇都要设立营业网点,相应的要有办公和人员的配置。中国扶贫基金会则节省了一个中间环节,节省了很多中间费用。
这是通过和当地农信社的合作来实现的。“我们实际上成为了当地农信社的一个大客户。”刘东文说。扶贫基金会的资金是存在农信社的,既节省了保险柜等的支付,同时还利用了农信社的联网功能,信贷员在放贷的时候,可以从乡镇的农信社的分支结构支取,还款的时候也可以存到相应的账号上。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做法,却让他们节省了大量费用。扶贫基金会分支机构中,管理人员的数目都不多,最多的只有18个人,少的只有7、8个人。
他们在管理上的第二点创新是在还款周期上。孟加拉模式的还款周期一般为一星期一还,而他们推行的是一个月一还的还款周期。“其实农民的还款意识还是挺强的,不会故意赖账,一个月一还的方式更符合中国现金流的现状。”刘东文告诉记者。
改为一月一还之后,虽然贷款利息稍微有点降低,但是每个信贷员管理的客户规模扩大了。刘举例说,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是在中国推行小额贷款的先行者之一,他的一名信贷员大多只能负责300-400名客户,而扶贫基金会的信贷员负责的客户则可以达到700-800名,是其两倍。信贷规模扩大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贷款利息带来的经济效益。
极高的还款率
“跟杜老师比起来,我们的管理更为严格,规模更大。比如说,对农民的贷款额度,我们最多可以达到一万,而杜老师之前只有5000,最近才刚刚开始向我们学习。”刘东文颇子为自豪地说。
至于还款率,刘也颇为满意。他向记者表示,拖欠超过30天的不良贷款比率不足0.01%,还贷款率几乎为100%。与之相比,杜晓山教授的累计还款率为96.6%,另一位先行者茅于轼教授的还款为97%左右。
“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和杜老师他们其实差不多,也是采用5人联保的方式,互相担保,只不过,孟加拉模式个人贷款的时候,5个人都签字就可以了,我们则要再和个人签。不过,还款率我认为原因在于建立更好的奖惩制约机制。”刘介绍说。
惩罚机制对应两部分,第一是对信贷员。他们招聘的信贷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当地农民,由于当地农民对农户的信誉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几乎没有不良贷款。在奖励机制上,信贷员的基本工资只有不到100元,90%的工资都来自贷款回收,所以信贷员的收入就取决于他每月的回款数量。
“把信贷员的收入和工资挂钩是确保回款率的一个有效途径。”刘评价说。当然,我们也给农民一些其他制度上的保障,比方说给农民上保险,基本失业、养老等保险都有,甚至有的地方还有住房公积金。
奖惩制约机制对贷款农户同样有效。他们建立了会员升级的激励机制,一级会员可以获得不高于4千元贷款,如果按时还款,就可以升为二级会员,二级会员可以贷款7000元,如此可以升至三级会员,三级会员就可以贷到1万元。
农民不能及时还款的话就会失去从小额贷款机构的贷款资格。而对贷款农民来说,小额贷款项目几乎是他们融资的唯一贷款途径。记者在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材料中也看到,其在左权县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农户每1000元贷款可以增收500-600元,60%的增收3000-400元,还有10%的只增收150-250元。投资回报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融资能力。
“现在虽然部分农信社也推行小额贷款,但是他们的客户对象主要还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或者个人。如果有能力从农信社贷款的农户,他们肯定不愿意从我们这里贷款,因为我们这里利息高。所以到我们这里贷款的都是被农信社等排斥在外的,除了高利贷几乎没有其他融资途径的农民。相对于高利贷来说,我们10%左右的贷款利率要低的多。所以一旦失去我们这个贷款来源,农民基本上就没有其他融资途径。”刘说。
此外,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了一套先进的管理模式,可以对设在下面的试点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随时对每一笔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回收的动态情况进行检查,这样就可以对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防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