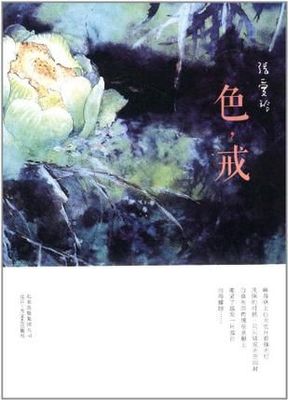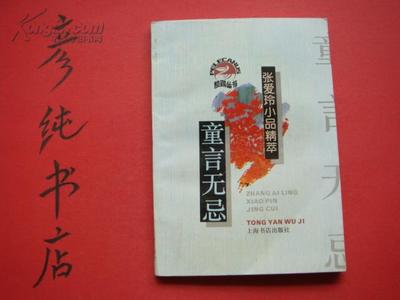王德威教授温文儒雅,但不会随便忽悠。凡涉及学术,他倒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也不虚与委蛇,展现出学者的赤诚。我与他见面的时候,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卷入了所谓的抄袭风波。而在这之前,中国学界的知名人物汪晖、朱学勤也因为著作的抄袭嫌疑而闹得纷纷扬扬,海内外学界各执立场,莫衷一是。我请王德威谈谈他的看法。 王德威一点都没有回避这些涉及名人的话题,而且还给出了完全与人不同的答案。王德威引述孔子“述而不作”的历史经典,指出中国的文学创作传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抄袭”概念,创作与延伸、因袭、模仿分不开,“原创”的概念并不存在,唐诗宋词莫不如此,东西方在“抄袭”的语境上没有契合。更进一步,王德威认为汪晖等人在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进行研究创作,承担着东西方交汇的思想学术启蒙工作,难免有文本应用上的混乱出现,这是不得已的。不过,王德威强调,“这是宽容的说法”。他虽然尊重三位专家、作家的苦心但也真心期待他们有自我批评的自觉。毕竟,“我们处在二十一世纪,智慧财产权已成为共识”,“抄袭”踩到了当代法律的红线,无法规避。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中,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作家,都必须谨慎,不能一概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的创作语境以及不同的规范做借口。

既然谈到张翎的小说《金山》,我顺便请王德威比较一番她与另一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王德威说,张翎创作很认真,但是生活经历比严歌苓狭窄很多,后者嫁给美国外交官,走南闯北,在小说题材和人物把握上占据很大的优势,再加上文字功力—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更精深的格局。不过,王德威补充,她们都已经超过了早年於梨华所代表的台湾留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水准。 王德威最喜欢的女作家,当数张爱玲。自夏志清教授把张爱玲与鲁迅、茅盾等大师级文学家相提并论,由此开启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王德威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张派传人”的研究。因为与夏教授一脉相承,夏志清还曾邀请王德威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我问王德威,你把白先勇、施叔青视为具有张派风格的作家,但你最欣赏的还是上海作家王安忆,认为她是张爱玲海派风格的真正传人,但王安忆自己并不认同?我问这个问题,是有些私心的,我也是上海人,有兴趣知道王德威如何比较这两个名闻海内外的女作家。 这个问题显然激起了王德威的热情。他坦承,当看到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就认定她是张派传人,但是,王安忆自己不同意,说王德威是误读她。王德威理解王安忆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张爱玲的阴影下,“她具有很大的野心”。而且,《长恨歌》之后,王安忆的写作风格离张爱玲越来越远。我追问,王安忆是否已经超越张爱玲?王德威不假思索,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有两个:一是王安忆的写作数量多,而且每部小说都保持相当水准,“这个很不容易”;二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已经远远超出了张爱玲的“上海范畴”,最近的一部小说即以明朝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编者注:即《天香》 )。但王德威随后补充:“张爱玲的传奇身世造就了传奇的张爱玲,这种巨星般的风采,其他女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我问王德威,刘心武醉心用符号学研究红楼梦,后又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你怎么看?王德威回答得很妙:“创作者的想象力无人能够预估评判。”他又说,为《红楼梦》做续,刘心武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倘若要用“续红楼”来证明刘心武的符号学研究,恐怕不易。《刘心武续红楼梦》是刘心武研究红学的一份心得报告,但不等于是成功的文学作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