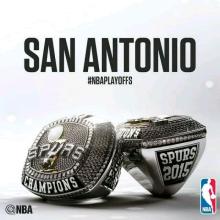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