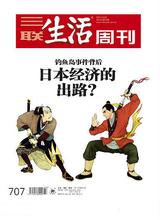系列专题:《创新的力量:了解过去十年市场发展变化》
改变人们的行为并不只是卫生保健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也是商业团体在动荡的世界中进行生存竞争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约翰·科特在研究了几十家正在经历剧变的公司后说:"战略、结构、文化或系统从来就不是重点,事情的核心总是关于人们行为的改变。"那些人也许不得不应对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产生的剧变--比如说,一个新的全球竞争对手的出现,或者是从一个受管制的环境到自由的环境的转换--或者是应对公司的重组、合并,或是新的业务领域。而作为个体,我们也许想改变自己工作的方式--比如,如何指导下属,或者如何面对批评。然而,我们经常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做不到。 CEO们理应是公司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他们经常像别人一样拒绝改变--甚至倾向于倒退。迈克尔·艾斯纳就是近来最声明狼藉的反面教材。在他几乎死于心脏病之际,艾斯纳终于听从妻子的建议,提拔迈克尔·奥维茨为第二执行官,以减轻他管理迪士尼公司的压力。但是,艾斯纳还是没有看透这个道理,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奥维茨任何实质性的权利。 传统经验认为,危机能有效地引起改变。但是,严重的心脏病已经是最严重的个人危机了,它都无法激发人们改变的意识--至少激发得还不够,精确、客观地分析人们的处境也不行。到底什么才有效呢?为什么对人们来说,改变在一般情况下会这么难呢?我们的大脑构造与我们顽固地拒绝改变有关吗?既然我们知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利无害,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科特切中了要害。"动之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行为发生改变,"他说,"这就算是对那些注重分析和数字测量的公司和那些自认为像MBA一样聪明的人都是适用的。在成功率极高的改变的努力中,人们不只对别人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从而帮助他们看清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的方法"。 不幸的是,学生在商学院里学不到那种以情动人,而对那些做事的技术统治论者--工程师、科学家、律师、医生、会计师,还有那些因受过训练的分析性思维而自豪的经理--来说,以情动人是非常别扭的。产生变化的心理背后有强大的科学理论做支撑--涵盖了像认知科学、语言学以及神经系统科学等新型学科--但是,通常情况下,这方面的洞察和技术似乎都是荒谬的、非理性的。

再来看看心脏病人的例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全球医学论坛"的精英们也许不知道怎么让他们作出改变,但是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教授迪安·欧尼斯博士。他和科特一样都意识到不受表面事实束缚的重要性。"告诉患者其健康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往往还不足以使人们作出改变,"他说,"我们还需要借助经常被忽视的心理、情感及精神层面的东西。"欧尼斯在最主要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设计的以素食为主、脂肪的卡路里含量不超过10%的整体计划,无需手术和药物治疗就能从根本上治愈心脏病。尽管如此,医学机构仍对人们能否坚持生活方式的变化持有怀疑。在1993年,欧尼斯说服奥马哈保险公司投资做了试验。研究人员找到333名患有严重动脉阻塞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帮助他们戒烟,并按欧尼斯提供的饮食方法进食。病人参加每周两次的、由心理学家指导的互助会议,还要学习冥想、放松、瑜珈、有氧运动等课程。这个计划只坚持了一年的时间。但是,研究发现,在三年以后,77%的病人仍能坚持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无须接受涵盖在保险里的代管或心脏搭桥手术。因此,奥哈马保险公司在每个病人的身上节省了大约三万美金。 制定改变的框架 为什么传统的方法失败了,而欧尼斯的计划却取得成功呢?一开始,欧尼斯重新确定了进行改变的原因。他说,医生一直以来主要利用病人对死亡的恐惧来激发他们改变的欲望,但那是行不通的。在心脏病发作后的几个星期,病人感到非常恐惧,医生说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死亡太吓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于是,他们就会出现排斥的心理,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