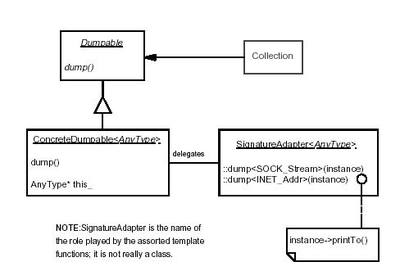关于哲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她是关于人的对象世界为我客观化规律的主体性把握;是这个世界中物在的和属人的价值性规律,通过人们行思于物的认知原点(知域构成),向着人的存在关系历史转换、社会生成的功能构造及理论生成。 在这里,“行思于物的认知原点”,不仅在人的主体性把握方式上给定了最好的动态性注释,且在对哲思形态的运作上给出了心-物涵合的内在规定。以至,经由这个认知原点的哲思展态,一开始就从它“物在的、属人的价值性规律”中(亦即从媾和着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社会生命状况中),实践地、理论地向着人的现实存在(关系)历史转换、社会生成。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将人们熟知的哲学定义重新改变呢?回答说,这是由哲学关注世界的天然使命及其功能所决定的。 哲学的天然使命和功能就在于:她总能在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层面上,寻找到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性关系,以便形成借以控制这一历史进程的知域构成与切分(认知)原点。而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和视野,为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构建彼此通约、相互融合的价值(理论)整合模式。 那么,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性关系是否改变了?人类控制这一历史进程的知域构成和认知原点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我们来看: 随着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面拓展及其对人类自身的社会改造,人类的知域构成亦随着对象方面的拓展和主体性的社会改造,从自我意识的本我提升至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类-我。哲学从她关注人类精神和命运的智慧之学,提升为关注人类共同生产生活及其与生存环境乃至宇宙演化系统之间,具有协同机理的整体流变之说、动态发展之学。 无疑,在这种哲学展态中,哲学的发展,不再限于个体自我意识引导的能动之思,而是超乎其上,成为一种有人的存在关系和社会生命(即现实类生活)媾和其中的类我合一之思,是对人的‘类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完整之思。 这里的类-我,就是我所强调的作为类属文化单元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亦是以其独特文化精神投身全球经济生活、把持自己历史命运的民族国家。实际上,这也就是有我思寄存其中的‘类我合一’的物在之思,一种动态发展、历史流变的物-我之思。 至此,我们将会发现:‘思’的认知原点(‘思’之主体)改变了,‘思’的运行方式及其哲学展态也与从前竭然不同! 从前的落实在生命个体这个认知原点上的自我意识之思,是在类我分离的矛盾关系中辨证展开的能动之思、应变之思,是隶属不同知识范式(科学结构)和我心文化的取向之思。明显带有个人智慧与机巧的现实选择性。以致不同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定义也各自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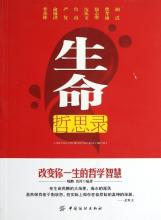
而那个有我思寄存其中的思之载体,那个作为类属文化单元投身全球经济的(承载人的社会生命和全部价值的)物化载体——民族国家,既包含了我的人之为人的固有文化心性,又包含了类-我合一(心-物涵合)的知域构成。因此,当我们从人类变换自然的这个认知原点出发,就把‘思’之主体由生命个体切换到人类变换自然的物在本体之上。人类的‘哲思’亦便在不同类属文化单元之间(所有民族国家之间)的生产生活和市场文化运作中,获得了类我合一、心物涵合的全新展态! 当然,这时的哲学定义就不再向从前那样:依照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那个独特的认知视角而定。而是按照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性关系,及其切分自然的涵合人类全部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那个认知原点而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