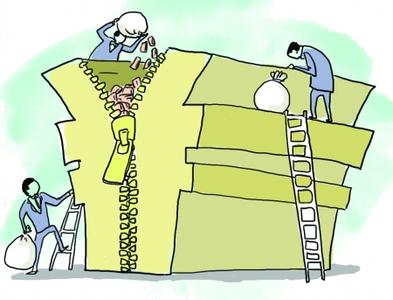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好景不长,沙祖康一家九口人在农村的生活日渐拮据。“特别是在3年困难时期,家里负担非常沉重。我兄弟姐妹共七个,我是老大,老三、老四两个弟弟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我就这么看着他们死在母亲的怀里,活活饿死的。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里长大,一年四季很少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有时候就吃野草,说实在的一到冬天连野草都没有,非常艰苦。” 沙祖康说,他能够坚持学习,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父亲对自己的教育。“经济恢复后,生活变好了一点,但总的来说,农村还是很苦的,很贫穷,没有钱读书。从初中开始,我就一直拿助学金,尽管不很多,但作为一种补贴还是支持了我。” 当年,沙祖康要上学,母亲坚决反对。“她每天就拿着扫把等在门口,只要你一背上书包去上学,她就打,就要我干活。她从来不管我旷课老师要批评啊,或者会成绩不好啊,她心底里想的就是生存是第一位的。”然而,沙祖康的父亲站在儿子这一边,支持他上学。每每母亲拿着扫把阻拦自己上学,背着书包的沙祖康就设法躲过母亲的“围追堵截”,急速冲出门去,“哗”地上学去了。“要是我父亲在场的话,就一手把我母亲给挡住了,说‘干什么呢?让孩子上学嘛’。就这样,我是否继续学业的问题上,父母亲是不一致的。” 日后,沙祖康曾逗母亲:“哈哈,当年您不让我上学啊?今天,您有什么感想?”老太太苦笑了一下,感叹:“孩子啊,你该明白当时多苦啊。没有办法呀!”当然,沙祖康也很理解自己的母亲。

一个贫困的农家,从小干过种麦、插秧、割稻等农活儿。沙祖康风趣地说道:“除了罱河泥,一般农活都干过,如可能将来可以继续当农民。”他还说:“我长在江南,对水有特殊的感情,我很喜欢游泳,见水我就疯。每次一下水,游泳绝不少于3000米。我曾在水温16摄氏度情况下,成功横渡过日内瓦湖。在日内瓦湖游过一个来回,有四五千米。” 沙祖康特别喜欢家乡的唐装,他曾经在走马上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前回国公干并省亲。紧张的行程中,还特意请江苏名牌产品“陶玉梅”为自己和夫人设计了具有浓厚“中国风”的唐装。当时为沙祖康及夫人具体负责设计制作唐装的张师傅回忆说:“大使先生和夫人在看了我们提供的设计样装之后,很快就挑选了自己喜爱的款式和颜色,我还记得大使先生选择的是一套绛紫色、同色系圆喜的唐装,下面是缎子裤;夫人则选择了一件织锦缎金色大花的旗袍,配貂毛烂花绒坎肩,还有一件旗袍是黑丝绒的,绣凤凰。另外还有一件大红底梅竹花的上衣,和一条丝绒裙。” 如今“沙式风格”闻名于外交界,然而在沙祖康刚进入外交领域时,周围的同事以及领导甚至扬言说沙祖康在外交领域根本就待不下去。 沙祖康说:“你越说我没前途的话,我还非要给你看看不行,我是个牛脾气,我就扎根外交部。非常幸运的是,中央或外交部希望我去达到的目标全部实现了,我没有失败过。” 沙祖康的外交生涯是从1971年走出国门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担任职员开始的,那一年他24岁。早年选择外交道路完全是出于偶然。 对于出身于贫寒农家的沙祖康来说,当年能够上大学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千万不能考上大学,她还烧香呢,祖宗保佑,千万别考上大学。因为家里太穷,需要劳动力,考上了大学也付不起学费。我考上大学以后,她非常愤怒,要撕我的大学通知书。”沙祖康坦陈地说:“凭良心,当时也没有为了革命学习这样的志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就知道农村很苦,要离开农村,这是真话。当年报考学校,考虑自己是南方人,填志愿时填的就是南京和上海的大学,其他的哪里也不填,更不清楚北京是什么样。” 1965年,沙祖康考取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当时家里没钱供他念大学,公社书记吴海清闻讯后,以个人名义担保沙家从当时的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22.5元钱。于是,他得以成行上学深造。今天,沙祖康对此铭心刻骨,对当年那位公社书记心存感激。“公社书记曾给地主家当过长工,放牛娃出身。当上书记后,他深感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积极地支持农村的孩子上学。” 沙祖康常常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官。他说:“我确实是农民出身,身上冒着乡土味,讲话也带着农民的幽默,讲话比较坦率、直爽,不喜欢弯弯绕。同时我也有农民所赋予我的智慧。我觉得农民最朴实也最勤劳,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家乡。我做农民外交官,我爱自己的祖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