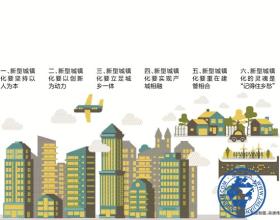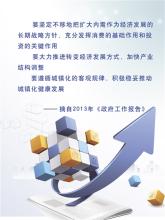本届政府履新百日之际,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并引起各界热捧。 将一国领导人的名字和经济学联系在一次的做法并非孤例,近有旨在扭转长期困扰日本的通缩状况、重启经济增长“安倍经济学”(Abeconomics);远有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带领美国成功走出“滞胀”困境,创造了全球经济的“大稳健”时代。可以看出,这几个新造词语的出现,其背景都是一国面临经济困局,新任领导人上任带来革命性的经济政策变化。

“李克强经济学”亦是如此。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选择了有别于上一届的政策路线,其关键的经济政策框架由三大支柱搭建: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逐一分析之。“结构性改革”是上届政府也一直强调的,若不看改革具体内容,似无太大新意;而前两项则是明显区别于上届政府执政思维。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紧急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固然保住了一时之增长,但也被很多观察人士认为造成了信贷规模膨胀,流动性泛滥。而“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两项,显然是直接着眼于解决过往的弊端。其出发点是,政府主导投资的刺激政策不可持续,与其维持旧有的经济模式而延缓病症发作,不如早下药早治疗。 假如巴克莱“三大支柱”的观察准确,则“李克强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不无相似之处。里根经济政策的三个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供给经济学”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货币主义”主张通过稳定货币发行遏制通胀。而中国新一届政府多次强调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分工;在金融层面,虽然从CPI指数看中国并无明显的通胀迹象,新一届政府也表明要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 然而,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进行政策转向,无疑将面临种种挑战。六月下旬以来的“钱荒”即是一例。正如有论者指出,钱荒的根源是过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形成了一种政策惯性的预期;而央行等宏观调控当局则着眼于去杠杆化,消弭金融风险,没有按照市场预期进行操作,最后导致一场影响远超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缺风波。 更严峻的考验则是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镇化等同于新一轮投资刺激的“机遇”。这无疑与“无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李克强经济学”正面相撞。我们不难察觉围绕城镇化路径而发生的冲突。 被喻为“最高规格”会议的全国城镇化会议召开时间原定于今年四月,但一再推迟。据分析,原因可能是高层对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不满意。六月底,一份题为《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终于由发改委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有不少委员痛批目前的城镇化“贪大求快”。 应当说,这种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据报道,一些地方新一轮的“造城运动”已经借城镇化之机动土。另外,随着城市轨道项目审批权的下放,轨道交通将迎来建设潮。仅在当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就达36个,到2020年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 “李克强经济学”号准了中国经济的脉,但药方能否剂剂服到位,则需经受住利益博弈的考验。第一道大关,即是被寄予厚望的新型城镇化。 实际上,在思路正在明晰,落地遭遇困难的时候,提炼“李克强经济学”还为时尚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