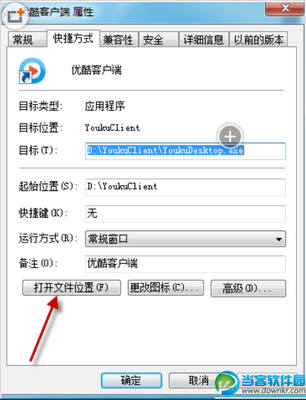为什么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倾向于推断中国将立即取消户籍制度呢?从技术层面上看,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运作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要消除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就必须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这一户籍上的差别,但他们忽视了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

在城乡移民领域(农民工),区分持有本地户口民工的关键是看他们是否获得所进入城市(镇)颁发的户口。 中国的农民工有两大类别:一是获得了本地户口,拥有当地正式居民资格的民工;二是没有本地户口也没有在当地取得居住权的民工。第一类民工成功实现了迁徙权,对于第二类民工来说,他们没有迁徙目的地的户籍身份和相应权利。在中国,只有得到了迁徙地户口的人才被官方承认是迁移人口,任何其他形式只能看成是流动人口,这就大大降低了迁移人口的统计数量,使当地拥有永久居住人口的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 非户籍迁徙人口在官方看来是不能在迁徙地永久居住下去的,尽管他们或许已经在目的地居住了多年,但他们只算做“暂住”人口,而且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保障和福利之外。拥有迁移地户口的迁移人口则被纳入“计划迁移”的范围,享有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资源。 户籍之墙仍坚如磐石 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农村户口居民,这部分人口流入城市,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从而形成了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现状。在中国,各种原因综合下来的结果,是形成了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户籍制度,该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大的一部分未改革的内容,被视为影响广大民工生活水平提高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 户籍管理系统的不统一和局部化强化了中国的矛盾和冲突,常常抵消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效能,使之难以达到理想效果(比如减少社会不公平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现状)。拥有户籍管理权力的地方官员也乐于利用这个工具,将“更优秀”的人口和财富吸引到城市。同时,地方政府也倾向于开发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的土地征用后盖政府大楼或批给某些人作为发财之路。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保持劳动力资源优势对中国政府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要求中国必须具备廉价劳动力优势。很明显,户籍制度在保持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要从实质上废除当前的户籍制度,中国人前方的路曲折而漫长。 我们要讨论问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内迅速采取措施废除户籍制度的限制。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和运作的机理,以及当前改革的实际情况。如果从中国户籍制度的两类划分标准和农转非的出现以及改革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户籍制度的复杂性。近年来,中国继续扩大废除农转非的试点省份数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户籍制度。尽管中国媒体将改革描述得多么美好,但现实是明摆着的,政府没有对户籍制度进行多大程度的改变,其地位并没有受到威胁。 户籍制度将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它就像一堵墙,以“隔离”的方式阻止了大量农村人口疯狂涌进城市。“雷声大,雨点小”,这句中国俗语可以描述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户籍制度实际上从属于城乡人口转移这一巨大的社会现实,对当前的中国社会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废除“农转非”的启示 过去,农转非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主要途径,但现在,户籍制度的地方化管理使这一途径风光不再。根据中国公安部2005年的一份报告,农转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乡分割的负面效应。不过,这一政策与取消户籍制度和其他限制国内迁徙的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农转非被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的“进城条件”所取代,其目的是吸引有财富的人和高学历人才进入城市,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作为一项新的全国性政策,废除农转非的法律条文显示,允许四川的农民工获得广州的城市户口是不合理的。 户籍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主动推进的。假如打破了城乡分割的现状,相信其他形式的分割之墙会随之形成并更为有力。过去,城乡分割的定义取决于政府对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不同解释,但现在,城乡分割继续存在,而主要依赖于政府对本地人和外来人(农民工)的区别对待。这是中国当前财政分权和人口及户籍管理地方化的必然结果。 取消限制未必保障农民利益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户籍制度现在还没有被废除,中国媒体上有太多的声音要求加强农民工在城市的权利保障。我们发现,所谓保障民工的权利只在很少一部分地区被列入计划。为了不至于对本地人构成威胁,实施的计划也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在中国,本地农民的土地很多已经被政府占有。外地的进城农民依然保留着“外来人口”的身份,这些措施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即便是那些取得了城市户口的少量的本地农民,政策的改变能否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也是值得怀疑的。从农村出现的大量抗议和请愿活动可以看出,保障农民权益的政策效果不尽人意。 那么,为什么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倾向于推断中国将立即取消户籍制度呢?从技术层面上看,我们发现,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运作的复杂性。他们不了解以进城门槛公平化取代农转非制度的这一重要事实。他们认为,要消除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就必须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这一户籍上的差别,但他们忽视了户口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具有选择性这一特点,也就是说,制度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汉语对操作规则和户口定义与西方有细微的差别,同时,改革也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所以西方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时,在翻译这一步就很容易将概念混淆。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看,研究者的焦点可能会更多集中于毛泽东时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在毛时代,中国被西方描述为遮挡着一层“竹幕”。 通过这层半透明的“竹幕”,外界可以观察到中国允许观察的信息,对其他的信息只能凭想象和推断了。这层“竹幕”现在依然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卸除。在转型时期,媒体通常特别在意中国的变化,并假设这种变化和我们西方一样,是向市场经济和开放自由社会过渡的连续、直线型发展过程。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政府对媒体实行管制,媒体也趋于一个声音。结果是,外界观察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继续影响下的中国(比如一党制继续存在)。 毫不奇怪,作为马列主义的遗产,惯性力量使户籍制度很难有实质上的改变。同时,在“不断进步”的宣传声中,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也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从简单化思维看来,在市场快速转型过程中,取消户籍制度和对农民进城的限制被看做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必然的。有趣的是,户籍制度很明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存在并继续产生效率的现实表明,中国离市场转型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时候,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按照我们为中国假设的道路去思考,而应该着重于中国基本政策变化的实际效果。 来源:华盛顿大学 2008年9月 作者:Kam Wing Chan /Will Buckingham 编译:杨政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