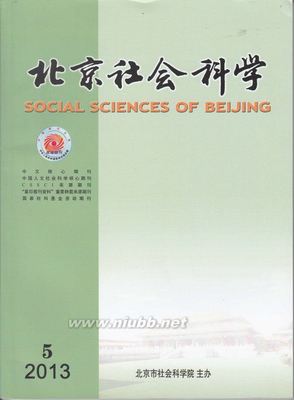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应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必须是对男权保持批判态度的世界。
作者:汪丁丁
某日,凌晨,我恍然觉察,原来启蒙与启蒙理性是男性的特征,故而启蒙以来的世界只好仍是男权的,虽然那里的人们声称将一切事物拉到“理性法庭”去审过。也因此,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象它是远比现在更美好的,我推测它必须是对男权保持批判态度的世界。 男女确实有别,且差别极大。脑科学家向我们说明过,女性在情感脑和基于情感的社会认知方面具有超越男性的神经生理基础。另一方面,男性在逻辑脑和基于逻辑的社会认知方面具有超越女性的神经生理基础。此处,“情感脑”究竟何指?极难准确定义,大致而言是“哺乳动物脑”(外缘系统)和“大脑右半球”的某种复杂的联合。这一定义仍在演变,随脑科学家的研究而发生位置和结构的变动。例如,我对场景记忆的情感功能深信不移,然而,场景记忆的脑区似乎没有被归入外缘系统或大脑右半球。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的某一阶段,主要是为了照料幼兽,从孩子的哭喊声判断他们是否面临以及面临何种威胁,哺乳动物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脑结构。根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结构最初形成的部分,是“杏仁核”——它产生“恐惧感”,典型地,当一条蛇被我们脑的视觉区辨认出来时,杏仁核便被激活。 在哺乳动物当中,人类的幼年期出乎意料地漫长——人类个体的脑区大约需要25年才发育成熟,难怪柏拉图理想中的“选民”都是中年人。也因为幼年期如此漫长,对人类而言,儿童特别需要母亲的照料。这一事实的演化论含义是,那些特别愿意照料自己孩子的母亲将获得更高的遗传概率。这样,人类的情感脑在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直到“启蒙理性”在最近200年内表现出强烈的负面特征之后,人类才重新关注自己的情感生活。保守派政治家们呼吁家庭与传统价值,自由派政治家们则呼吁人权与妇女权益。 或许,我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启蒙理性”的特征是怎样的?有些读者甚至会询问一个更初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所谓“启蒙”,根据康德的看法,就是每一个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这样一个过程。欧洲当时处于教会垄断之下,虽有宗教改革及改革派倡导的新教理性,与斯密对教会的暧昧态度相比,康德号召每一个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显然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 康德阐释了理性的涵义并为它划定了基于先验哲学的界限。在康德所继承的希腊哲学传统里,理性与计量二者相通。首先,它们有同样的词根“ratio”,意思是“比例”、“度量”、“合理”以及与“无理数”相对的“有理数”。其次,康德阐释的先验理性与逻辑性,二者是相通的。任何命题之真理性,必须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才不再需要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明。逻辑,它的基本定律具有最高的普遍性。第三,在古希腊文字里,由“逻各斯”一词繁衍出了“逻辑”“真理”“计量”“叙说”和“对话”等涵义。我曾查阅英文版的《牛津中级希腊文词典》,我记得与“逻各斯”分享着更古老的词根的语词,是“树段”——通常所谓“木材”的原始形态。伐木者需要记住木材的数量,于是有了这一语词。 许多读者知道德里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他说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或“语音中心主义”的。大致不错,因为西方语言与西方理性确实需要沿着直线才可展开其真理性。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字是基于形象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至少,它的最初形态不是基于声音的。 若不考虑已经消亡了的文明,基于形象的语言与理性,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先秦诸子,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名家似乎消失得最为彻底。有特别的原因吗?我推测,名,或逻辑学,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与理性的优势所在。我们或许可以培养出毫不亚于西方人的逻辑性,但归根结底,那是将西方的语言与理性翻译为中文而有的结果。 儒家学者,只有梁漱溟曾认真地要建立一套中国人的心理学,从而古代儒家的伦理学才是“有的放矢”的伦理学,才不是空洞无物的伦理学。遗憾,梁先生尽管以高龄辞世,仍没有机会知道今天已经极大地普及了的脑科学研究成果。在梁先生的著作里,我逐渐注意到的,是他阐释的古代儒家的情感学说。他的阐释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中,早年习佛的经历特别重要。也许是儒释互释的结果,梁先生的情感学说尤重“心性自然”。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本原状态,只要我们努力去蔽,总可明心见性,然后经过“保任”而能“一任本心”,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这里“去蔽”,就含有“为道日损”的意思,与西方的语言和理性恰好相反。后者,其实总是“为学日益”的。基于情感脑的语言和理性,我推测,与梁先生晚年所说的“一任本心”关系密切。也因此,我推测,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应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