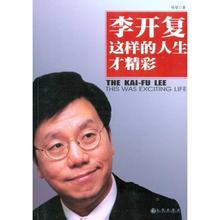四月是硅谷的冬天。
这个以盛产梦想和圆梦者著称的地方,有着常年的强烈日照和好天气。直到冬天,迎来短暂的雨季,硅谷才是绿色的。 “我为雨天表示歉意”,谢尔盖·布林对来自中国的客人说,仿佛他就是那个控制天气的人。即使并非如此,他仍被视为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人之一:8年前,这个长着大鼻子、娃娃脸的俄罗斯裔年轻人,和他羞涩的搭档拉里·佩奇,在乐高玩具和匹萨的包围中,创造了Google,然后将它变成新世纪以来最大的商业奇迹。 这是又一个关于创新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在古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术后不到500年,首度有一种方式显现出编织、分享全世界所有的信息的可能。如果说它和爱迪生发明灯泡有什么不同,其一:它没有用25年时间才成正果,其二:它是免费的。 虽然自信息革命以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诞生一颗“超新星”,如1971年的英特尔、1980年的苹果、1986年的微软和1995年的网景,但Google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到来后,第一家将巨大的破坏性创造力结合以罕见商业成功的公司。这就让全球网民、投资者乃至同行目睹了它用6个月时间将股价超过200美元,在接下来5个月内升至300美元,又用了另外4个月时间跃上了400美元的平台——当通用电气们为将股价拉动几美元而费尽苦心,Google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相当于雅虎与亚马逊、eBay的市值总合,或者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市值之合的4倍。 很大程度上,这种“狂热”并非源于Google的业绩(虽然那些数字相当好看),而是因为它的神奇。正如近年来国内学人开始将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的名言“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通俗翻译成“世界不再令人着迷”,随着流水线生产将一切物质乃至大众生活同质化,人们对外界的好奇心就被磨平。 而Google则恰好在扮演一个多数企业无意扮演的角色:每每以自己的方式挑战外界想象力的极限,给世界带来惊喜。而其行动及成绩则在不停改写众多商业规则:它极大改变了整个网络业的商业模式乃至思考方式,也将广告业推到升级的临界点,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将学院派研究方式和商业结合的最佳手段。这让过去两年间,人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一个专属硅谷的神话:两个斯坦福大学肄业生,在车库里编出了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几年后,他们成为了身价百亿美元的富豪,和比尔·盖茨最忌惮的竞争对手。
即使更富戏剧性的讲述这一切已经足够有吸引力,《环球企业家》仍希望回答一些新问题:在这个越发重视创新的世界,Google这台创意机器的运行方式是否可被复制?而它的未来通向何处?为此,过去一个月间,本刊记者在中、美两地采访了包括Google创始人、CEO和数位高管,以及大量相关人士。 “什么是互联网业的下一件大事?”我问布林。这就像询问鲍伯·迪伦“音乐的未来是什么?”,其实你只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推出下一张专辑。 布林站在那里,神情有些木讷,用带有些许俄罗斯口音的英语说:“我们尝试很多事情。因为无法确认什么是下一阶段最受欢迎的产品,所以我们尝试很多帮用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抱歉,鲍伯·迪伦说:“答案在风中飘”。 三幅面孔 在我们将话题深入之前,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Google是什么? 显然,它是搜索引擎,但这并非答案的全部。很大程度上,Google的成功正因其不将自己拘泥于某一种定位,从而按需配置出一套复杂体制。或许,这将成为21世纪公司普遍的DNA。 读解Google,需要从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三个层面入手。 在它那强大的搜索引擎背后,首先是一套尽可能自己开发一切的技术体制。除了对外发布的产品,它还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基于Ubuntu改善的Goobuntu)、数据库和分布式运算系统,甚至自己搭建服务器。 这种行为很容易引来误解。早在2003年12月,比尔·盖茨就在浏览Google的招聘页面时深感惊讶,这家搜索引擎公司在招聘大量操作系统设计、编译器优化、分布式系统结构设计等领域的工程师。这让他深感警觉:Google会对外免费提供一套操作系统? 即使Google一再对外否认将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或浏览器乃至个人电脑,此类疑问从未消减。来自《环球企业家》的建议:有两个原因让你至少暂且搁置这种疑问。首先,Google的愿景是“让全世界的网络用户随时随地获取所有所需信息”,无论生产PC还是操作系统都是对此方向的一种偏离。其次,跟比尔·盖茨针锋相对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从Google的风险投资者到CEO到众多高层管理者,都不乏与微软竞争失败的惨痛经历)。它真正需要这一系列技术的本质原因,也是广受误解的关键,是Google在做一件IT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搭建一套计算机系统,将全世界信息搜集到一起,并进行处理。这一巨大的雄心,迫使其寻找各种方式让成本更低,效果更优。比如,它把超过10万台PC机改装为服务器,其成本,大概相当于外部购买的1/3。
Google的定位——信息处理及分享——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意味着信息开始像石油、钢铁一样成为一种资源,也注定了其商业模式不会等同于软件公司。2005年,Google的收入达到61亿美元,其中99%以上来自于广告。它所采用的将用户搜索的关键词与相关广告业务配对的广告发布方式,被《紫牛》的作者、网络营销大师赛斯·高汀称为“50年来第一个新而有效的广告媒介”。此外,它还将大量广告投放到如美国在线和《纽约时报》的网站上,使其更像一家具备规模的网络广告代理商。 至少目前看来,Google在广告方面的探索仍有很大余地:仅美国的年广告投放额就达2500亿美元,其中网络广告仅占100亿。而且,网络可以突破任何传统广告发布方式之处在于,随着对用户信息的丰富,它就能找到真实的需求。 “看看Myspace,非常有趣。”不久前,在接受Newsweek杂志采访时,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说。这同样让很多人迷惑:Google会看重一家针对年轻人的社区类网站? 4月中旬,施密特来到北京,《环球企业家》特意就此向其询问:这是否意味着,Google羡慕Myspace拥有的丰富且深入的用户信息?他对此并不否认:即使Google并不会变成一个Myspace,它至少会朝获得更多用户信息的方向努力,以更精准有效的投放广告。就在施密特及公司一半以上的高管在北京发布中文名字“谷歌”的第二天,Google推出了其日历功能Google Calendar,这个能让每个用户在网络上撰写自己的日程安排的产品,确有可能获得别人无法企及的信息。 如果认为同时管理技术公司与广告公司的混血文化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再加上一些风险投资公司的基因如何?与以往你所见到的任何技术公司有所不同,它像孵化器一样收集、生产来自各处的想法。它给予那些有好想法的员工足够的时间、经费及人力支持,让创新自下而上产生。当一款产品取得巨大成功,创新团队甚至有望获得千万美元级别的创始人奖金——这样的奖金一年会发3、4次,因此,也有人将Google称为“硅谷最奢侈的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创新工厂
架构此种特殊肌体且让其运转起来的,并非某个杰克·韦尔奇式的管理大师,而是一种纯粹的创新气质。在2006年4月Business Week与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最创新公司”排行中,Google名列次席。而在IT和技术类同行的评价中,Google更是超越了苹果。 需对这一认可作出注脚:即便在以创新为首要推动力的IT业,坚持创新者并不多见。那些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公司,总会被接踵而来的低成本复制者包围,并通常迅速败下阵来。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创新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创新与效率有机平衡的难度也就急剧提高。正因此,人们倾向于相信,革命性的想法只集中于年轻的小型公司中。 这就让已经拥有6800名员工的Google显得格外特殊。“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已经成熟了”,公司副总裁玛丽莎·梅耶称,“成熟的含义是,我们不会轰然倒塌。”但这似乎没有妨碍它频繁推出让人惊讶的作品,比如Google地图搜索、富有趣味性的Google金融,甚至Google火星。 保持活力的关键在于,Google的管理者意识到,既然管理一个大型创意团队是困难的,为什么不试试管理许多个小规模的创意队伍呢?“当我们有6名工程师,你可以选择组建一个6人小组,或两个3人小组,我们宁可选择后者”,梅耶说。这正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Google有着风险投资公司一样的管理、激励方式。 让这家“风险投资公司”运转起来的基础是,Google确信自己的员工都是最好的。正如全世界在过去一年内所看到的,为了将最好的工程师罗致门下,它展开了一场极富雄心的人才搜索行动。在过去几年间,Google的确每年都在将员工数量翻上一倍,现在则以每周超过100名员工的速度引进新血。 除了充分利用自己的炙手可热定向猎头,它还采用各种富有创意的方式广撒网。如它曾在旧金山的101公路上放出一块广告牌,写着:“常数e里出现的连续的第一个10位质数(first 10-digit prime found in consecutive digits of e).com”。这个没有任何提示的广告,只对那些数学天才开放:任何做出这道题的人,登陆这个网站后,将会遇到新的数学题,顺利完成后,他将获得前往Google面试的邀请。Google还曾将一种包含21道难题的“Google实验室能力测试”刊登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其中包括解出“wwwdot-google=dotcom”这一方程式中的每个数字,或者“用最多29个字写写你来Google实验室后最想做什么。”甚至,它通过收购遴选人才(详见辅表《买家Google》)。收购数据统计、分析公司Measure Map时,Google与对方的母公司Adaptive Path达成这样一项协议:自己有权从对方管理团队中聘请两人。合同达成后,它对Adaptive Path所有高级管理者逐一进行了面试,最终挑出了自己最需要的两人。而当Google在澳大利亚收购了一家叫where2,发现其公司创始人拉丝姆森兄弟之一的妻子是古巴人,不能进入美国,干脆让他们在澳大利亚设计研发中心。
此种不遗余力的人才吸纳,让Google的每名员工都会津津乐道于这家公司有多少“天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研究了3年如何遥控火星探测设备的彼得·诺维格现在Google负责搜索质量,一位前脑外科医生负责Google的服务器搭建,而一名火箭专家参与到广告业务的算法工作中。甚至火狐浏览器的主导者之一本·古杰尔、在微软负责IE的亚当·波斯沃斯也加盟于此。而随着Google越来越国际化,各种想法已经从世界各地涌来:2006年3月推出的金融页面Google Finance的开发在印度班加罗尔完成,桌面搜索则是一名叫做王忻的中国工程师最早开发的。 正如Google希望追求微型管理结构,它还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人数增加一倍,就意味着同时操作的项目也要增加一倍。 自2003年以来,Google一直在内部实行“70-20-10原则”:将70%的力量投入核心业务,20%的力量投入相关业务,10%的力量放在探索业务。在这一精力划分体系下,每名工程师都有自己20%的时间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项目尝试。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创意无穷,但只是帮助那些有想法的工程师,已经可以让Google的管理者省去不少微观协调的力气,这一制度更大的价值在于,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意生成方式,效率极高。传统的创新管理办法中,通常由某一个超级大脑设想好一套完整的创新方案,然后布置给很多人分头完成,最后整合到一起——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过于复杂,而且操作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也很高。但如果是某个人独立实现其想法,就免去了很多沟通成本。如Google最初的图片搜索,是中国工程师朱会灿一个人用6个月时间搭建的,随着这一项目成熟,更多人再参与进来。 即使Google尊重每一个新想法,它仍必须度过三重考验。首先来判断其价值,或说负责决定将20%的时间由一个尝试变为一款产品的人,是公司副总裁玛丽莎·梅耶。
这个Google第20名员工,每周会有几次时间听取新的想法:那些最好的想法将在不久后被送到布林和佩奇那里讨论,然后变成产品,它们还会被加入到Google的Top 100任务列表中,任何员工都可以在内部网络上看到这一列表,甚至主动要求参与其中。对那些有一些亮点的想法,她将提供一系列建议,让对方完善。即使似乎并不合适转化为产品的,她也不会说“不”,而是说:“现在还不合适”或“还可以做的更好”。当然也有时,她会直接告诉对方:“我不太确定我妈妈能弄明白这个。” 经她“过滤”,布林和佩奇就有足够的精力判断那些“下一件大事”。当一个项目被送至他们两人那里,工程师们会用极尽细致的数据支撑其想法。比如,有工程师测试发现,如果Google只是把广告的字号加大一点,就能增加数以千万的广告收入——Google内部的官方语言永远不是“我想……”,而是“数据说明……”。 当然,并非所有好看的数字都打动两个创始人。不乏有Google员工称,谢尔盖·布林经常在会在听取报告时,非常直截的问一句“这能让世界变的更好?”,然后将一些可以大赚一笔的项目放弃。如当有工程师建议在图片搜索中加上和图片大小相等的广告条,拉里·佩奇问到:“我们还挣的不够多吗?”即使工程师们预计将为公司带来一年8000万美元的收入,两个创始人仍不为所动:“我看不出这对我们的用户体验有何改善。” 最后,是市场反应。虽然Google的产品均为免费,但每款产品发布后,仍有非常细致的产品跟踪和分析。一款获得20%用户认可的产品可以称为极大的成功,而那些认可率低于10%的则会被比较快叫停:获得成功的产品将得到更多人力支持,失败的小组则立即解散所有人并入其他小组。“这很残酷”,施密特承认。 Google管理创新的方式可以被复制吗?埃里克·施密特点点头。那为什么还没有其他公司效仿Google?“I don’t know”。“对‘不可能之事’持一种健康的漠视”
即使Google的人才招徕及创意管理体制算得上成熟,仍需指出:没有一种体制本身能够确保创新的持续进行。 几乎每个硅谷人都熟知这样两个教训:1970年代施乐公司成立的帕洛阿托研发中心(PARC),曾创造出鼠标、图形操作界面和激光打印机等影响IT业历史的技术,但没有人知道如何把好的技术变成商品。而1992年,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试图进行同样的实验:投资1亿美元创建Interval研究院,让最好的研究者自行其事。这最终演变为一出闹剧:1990年代中期,李开复曾被邀请前去演讲,介绍其语音识别方面的心得,他所看到的是全球著名的科学家们东倒西歪,甚至躺在地上听其演说,与其进行哲学层面的辩论。1999年时,在取得140项专利但亏损2.5亿美元的情况下,Interval终于关闭。 在Google内,这同样是一个“与魔鬼同行”的过程。其员工曾被合作伙伴指摘为不守时,缺乏必要的商业素养,甚至有传闻说,拉里·佩奇一度在内部表示,有些时候Google的研发过程显得不够聪明:比如挑选项目过于随意,分头开发时不使用共同的基础组件……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家公司的管理者清楚,为了让所有好的想法浮出水面,什么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原则。 1998年,当佩奇和布林创办Google时,他们的年龄不过25和24岁,这就让Google在其成立之初有着强烈的学校生活色彩。 虽然两人性格差异巨大——前者内向、低调,喜欢思考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后者精力旺盛,好动,喜欢对即成事实进行改善——但两个人都热爱在工作中游戏:佩奇喜欢单板脚踏车和乐高积木,他用乐高积木搭设了Google第一台存储器的外壳(讽刺的是,这台存储器现在摆在斯坦福大学比尔·盖茨电脑科学楼里),而在他现在Google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台用乐高玩具搭的打印机。布林则外向的多,夏天几乎每天中午,你都能在Google园区的沙滩排球场里看到他,以至于很多下午的会议开始前,人们看他一边往会议室走,一边掸脚上的沙子。他学过杂技,甚至仔细考虑过加入马戏团。 Google正是在这样的人格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尽量让员工快乐工作的文化。在规模尚小时,它就成为了硅谷唯一一家用期权招聘厨师的公司。多年来,Google每天为所有员工提供免费的三餐,以及免费的医疗、牙医、美发、洗衣、干衣等服务;在Google的办公室里,随处可以找到免费的十几种巧克力豆和几十种饮料,台球桌、桌上足球、按摩椅散布于其间,员工可以带狗上班(猫还不行),每个员工还能获得100美元布置自己的空间(有人买了《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R2D2和尤达大师的模型,有人则买了个红绿灯挂在自己脑袋上,还有人买了一座英式电话厅)。虽然Google的薪水在硅谷并不算顶级,它仍有大量员工一天12小时以上待在办公室。足够宽松的工作氛围下,佩奇和布林倡导着一种近乎理想化的价值观:思考那些可能让世界变的更好的大事。他们本人就是这样。2006年二人在达沃斯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后,他们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观了当地的天然气生产基地,当他们回到美国时,连Google的员工都感到吃惊:他们几乎已经成为了天然气知识方面的专家。“他们几乎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而且往往是对的”,一个在Google任职4年的员工对本刊说。
因此,在Google内部,没有人会轻易否定哪个想法太傻,或者太大,相反其领导人愿意刺激员工思考,比如让大家设计一部通往月球的电梯。在Google的办公楼里,设有两块约10米长的白板,一块写着Google的外星计划,另一块是“Google的大师计划”。上面均是员工书写、绘制的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如买下火星、消灭罪恶、开办Google银行,当然也有做出Google的操作系统——这其中一些注定不会实现,但也有一些已经变成了现实:比如有人曾写下“雇来温特·瑟夫”,随着这位互联网之父来到Google,这一条目下已经被划了勾,不过他距离Google员工为其设计的工作:“重新设计TCP/IP”和“第三代互联网”,还相差甚远。 这就形成了一种“没有限制”的开发哲学。Google的工程师可以在设计一个产品之初,不去考虑CPU计算能力、存储、带宽、商业化等众多局限想象力的问题。因此,Google内才能进行大量多数企业难以开展的项目:运用其搜索技术编辑基因和生命科学数据库;扫描上百万本已经不存在法律问题的图书;追踪每一次网络上的扫描:谁在扫描?并对每个用户的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尝试着建立一个全球手机姓名地址簿;把其电子邮箱Gmail里的所有信息永久保存下来,即使这可能让他们因滥用权力而被告上法庭…… 让这种文化不致失控的,是相应的制衡力量。比如,CEO施密特会较多从商业角度与两个技术导向的年轻创始人寻找平衡,而在管理技巧上,前Intuit软件CEO、Google的顾问比尔·坎贝尔则扮演他们的教练与智囊。 甚至,在企业文化上,也有一种无形的平衡:有两句口号在Google内影响深远,“对‘不可能之事’持一种健康的漠视”(a healthy disregard for the impossible),与“不作恶”(Dont be evil)。前一句话让Google保持着对破坏性创新保持着热情,后一句则让其始终保持反思意识。虽然在日益全球化、但文明之间始终存在冲突的今天,没有人能永远看清“作恶”与“不作恶”的界限,这种合力至少让它不至于太轻易因为利益丧失信誉。引爆广告业革命
如果试图概括Google过去8年的工作,其成就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突破:技术上,佩奇和布林在斯坦福开发的对网页的重要性进行评估的算法Page Rank(这个Page并非指网页,而是佩奇的姓),这一算法不是简单地查找关键词,而是对关键词出现在的页面的价值进行打分,分数高者显示在更主要的位置,这就让搜索结果能把无序的页面变的更为相关;商业模式上,另一家搜索引擎Overture率先采用付费广告影响搜索结果,Google借鉴了这一思路,但坚持在搜索结果旁边单独列出付费广告结果,这就是日后为其带来绝大多数收入的Adwords。在此基础上,它又开发出一种叫做AdSense的技术,通过分析每个页面的关键字,投放相应广告。经其代理的广告广泛出现在美国在线或个人博客上:最高时,它能接触到全世界约80%的互联网用户! Google的广告业务之所以能长足发展,因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传统广告产业最大的悖论在于,所有人都知道广告花费中的一半是浪费的,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半被浪费。而Google至少能更有效的找到相对准确的广告投放对象。虽然仍有较为严重的点击欺诈现象存在,但如果未来的广告在购买行为发生后付费,则这种情况就将被避免——至少Google是通往这一方向最接近的公司之一。 甚至,广告的推广不一定只发生于搜索过程中。2001年,一个叫保罗·布克黑特的工程师曾向玛丽莎·梅耶汇报,希望能制做一个Google的邮箱,并把相关的广告放进去——比如你在邮件里约别人去打网球,邮件的一侧就会出现拍子和球鞋的广告。梅耶认为这会让用户感觉被侵犯了隐私,两个人一直讨论到凌晨,并最终决定不捆绑广告。但当第二天Marissa登陆邮箱时,她发现广告已经出现了,幸好她和其他在测试Gmail的5个人也发现这并不是那么让人讨厌。3年后,当Gmail最终发布,整个商业模型已经非常成型。 2005年,Google的广告收益达到61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任何报纸、杂志、电视网的广告收入。而到2006年,该数字有望达到95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第四大“媒体”公司:在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和迪斯尼之后,超过了NBC环球和时代华纳。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担心:Google的光速增长正在逼近天花板。在其发布2005年第四季度财报时,其同比增长仅86%的消息令股价应声而降。虽然这一情况在2006年4月20日发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时为之改变——它再度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答卷:收入比上一季度提升79%达到22.5亿美元,利润提升60%达5.92亿。业绩公布后次日,Google股票开盘前就长了30美元。但不可否认,对于Google成长空间的担心即使不是多余,也是合理的:没有公司能够总比市场增长的更快。即使Google有望从雅虎、微软那里获得更多网络广告市场份额,因为网络广告业本身尚不算巨大,想保持此前每年收入翻倍的势头仍将非常困难。质疑声中,Google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向传统媒体产业进军。听起来不合理?其思路是,把它从网络上获得的广告,销售给纸媒体、广播,甚至电视上。
从2005年起,Google已经跟3家专业类杂志和《芝加哥太阳时报》签定和约,把它在网络上获得的广告发放到报纸上。2006年1月,Google以1.02亿美元收购了dMarc广播公司。这家打包购买广播电台广告时段,然后根据节目特色进行针对性广告投放的公司,被视为Google下一阶段的重要方向。这让Google一下增加了500家广播电台的投放可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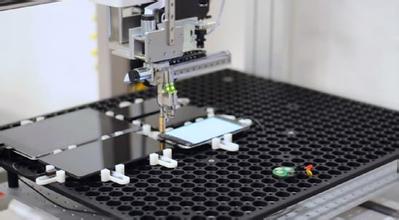
虽然这种逆向而动还在尝试阶段,但逻辑似乎足够充分:Google在网络广告上积累的最大经验就在于让广告与信息尽可能吻合,从而产生最大的推广效果。依靠其广告分类手段,结合传统媒体的丰富内容,它将获得更多的广告投放。而且,相对于网络广告,报纸、电视和广播的广告投资资金要大的多。全美每年共有2500亿广告投放,互联网广告虽然高速增长,但只占其中1/25。 这一可能引发广告产业革命的努力究竟能否成功,最合适的试金石将是电视广告。至今,绝大多数美国人仍将收看视频作为自己行为的第一选择:来自Veronis Suhler Stevenson媒体投资银行的数据,2004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在电视、电影和DVD上消耗的时间达1625小时,相当于每天有超过4小时时间坐在电视前,只有176小时用于互联网、108小时用于阅读——后两者加在一起,平均一天尚不足一小时。 一个障碍是,好莱坞的游戏规则与硅谷的远为不同,2004年末,Google开始录制旧金山地区播放的电视节目,但没有征求节目拥有者的同意。这引发了电视公司随后的勃然大怒。即使现在Google与电视网络的关系有所改善,谈判获得相应版权仍比网络上数之不尽的免费信息的成本高太多。 但Google似乎找到了迂回的路径。一家据说与它关系密切的位于洛山矶的公司Spot Runner,不久前发布了一套针对电视的广告系统。广告主可以通过Spot Runner的网站购买当地电视台的广告,其成本之低,一个黄金时段的30秒广告的价格甚至只要100美元。这就方便了很多业务集中在某个具体城市里的中小型企业,通过信用卡和网络,告别一切中介,广告的效应就实现了。 Google的未来 真正富有诱惑力的,也很可能是一个超越了媒体能力的话题是:未来的Google是怎样的?
这不仅因为作为商界的超级明星,所有人都对Google的兴衰走向高度好奇。更为重要的,如一些评论者所预言: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正从客户端软件转向互联网。Google所在做、将做的事情,无疑是此一进程中的重要风向标。
对于未来,Google的高层三缄其口。即使公司CEO施密特说:“事实上这家公司有精确规划”,但佩奇更愿意指出:“我们不谈战略,因为它是战略性的。我宁可让人们认为我们晕头转向了,也不愿意知道我的竞争对手们知道我们的方向。” 事实上,虽然拥有“精确规划”的战略,你仍不难发现Google的战术随时在改变。上市前,它曾表示“不做星座预测,不做财经咨询,也不做聊天”,但过去一年间,Google的聊天软件和财经频道陆续登台。如果有人能在10%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有趣的方式提供星座预测功能,很难想象它会被Google放弃。 至少在上市以来,Google变得越来越像一家门户网站。虽然它的每个页面仍将保持绝对的简洁,每个服务与服务之间也只维持若即若离的联系,但Google已经在搜索引擎的概念上走开了很远:它有自己的网络服务(电子邮件系统、即时通讯及日程管理),信息平台(Google新闻、Google Finance和地图相关产品),和电子商务系统(Google Base、Froogle)——所有产品,都在逐步整合过程中,而它们都可以为Google的广告销售提供支持。美国已经有观察者将其称为第二代门户。所有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仍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个影响其收入的公式:收入=用户数*(搜索次数/用户)*(广告数/搜索)*(点击数/广告)*(收入/点击)。提升上面每一项数据,都有可能帮助Google延续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虽然它无数次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华尔街的预期,但拉里·佩奇也曾认真表示,自己不想像其幼年时的偶像尼古拉·特斯拉一样,在发明出交流电后穷困不知所终。 在此逻辑下,除了探索国际化(“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百度”,Google高层们喜欢这样说)和丰富其客户端(比如它在尝试一种叫“线下”的手机搜索功能),业界普遍认为,随时可能进入在线音乐搜索及销售、在线支付系统等市场。但这并不会让Google变成另一家雅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都会坚持搜索引擎公司的定位。它摸索着根据用户的个人情况定制搜索结果的方式,并早在5年前,就注册了声音搜索相关的专利。
这就像一条无限延伸的未来之路。拉里·佩奇曾说:“最终的搜索引擎应该能理解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并永远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即使Google已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搜索引擎,距离其理想仍相去甚远。 而让搜索引擎“理解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也就等于让电脑具备真正的人工智能。“搜索不一定是人工智能的答案,但海量信息一定是,而搜索是唯一能够处理海量信息的方式。”李开复说。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教会电脑进行翻译。Google高级工程副总裁艾伦·尤斯塔斯认为这是当前最让他兴奋的技术:通过在海量信息中进行搜索、比对,让电脑找到最佳翻译方案。不过,这个工作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甚至,Google在跟生物学家克雷格·温特等人合作,借助其搜索技术,结合大量的人类基因组数据,很可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对海量基因信息的分析,将指向新药的开发和对疾病的治疗。这是谢尔盖·布林最热衷的项目之一,他认为未来终有一天,通过比对遗传密码的工作,人类将能告别很多疾病。 “为什么不能改进大脑呢?”布林反问:“也许未来,我们能可以把一个小Google插入人的大脑,这样你就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全世界的知识了。这可够刺激的。” 同时必须进行的,是Google自身的进化。玛丽莎·梅耶记得,当她来Google应聘时,曾被要求列举三条Google的缺点,她只能列出两个。当时对方告诉她,他可以列出1000条来:“从外面看,你看不到什么缺点,但在公司内部,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问题”。 这正是施密特所担心的。在北京接受采访时,他说点击欺诈这样的技术问题并非Google成长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只有一个:管理增长。对于一家每年人数增加一倍的公司,保持其文化不变质,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而且,按照现在的速度,Google将可能在两年内全球拥有超过2万名员工——其内部的看法是,这将是一个临界点,到此规模后,Google一直采用的“70-20-10原则”很可能成为效率的瓶颈。一场大变革不可避免。 如果说未来有谁能阻止Google,人们所能想到的首选答案就是它自身。毕竟它太快获得了成功,这不可避免地在公司内带来骄傲。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就曾开玩笑说:“布林和佩奇太自信了,即使跟上帝辩论也不会犹豫。” 幸好,他们还没有骄傲到认为Google已经做到了顶峰。“我想我们只做了想在未来20年做的事情的一小部分”布林说。而他的搭档应和说:“如果这就是顶峰,我会非常失望,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年去做点什么。”(80438) 在最新、最酷也最绚丽夺目的网络经济中,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对一家将创新视为灵魂的新技术企业来说,如何充分发挥文化因素的价值,以便更有效也更直接地激励企业的创新精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