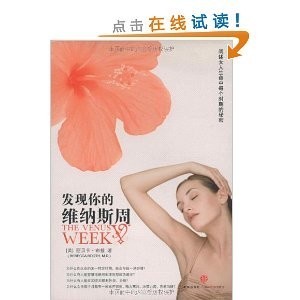崔大柏抱怨说:彭真当年就在邻村蹲点,从来没有领导想起小堡。现在它是宋庄最有钱的村落,人均年收入1.3万元。
◎ 孟静

“我们在中国宋庄画家村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向导服务,如果您对宋庄画家村不是很熟悉,来到宋庄又很迷茫,没关系,请您联系我们,我们将带您走遍宋庄!我们将让您满意而归!为了节约您的时间,如果您需要找某位艺术家,请您提前一天通知我们。如果仅对宋庄不熟悉而需要我们为您带路向导,可以来之前和我们电话联系。我们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50元,如果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再另行商议。” 假如你在网络上搜索“宋庄怎么走”,会出来这样一条广告。到了小堡村我才知道,没有人带路,这505户人家是汪洋大海,没有路标,街边商店里都是外来人口,交通工具只有“摩的”。艺术家们的家都像深宅大院,门户紧闭,家家养狗。这也是为什么圆明园画家村给政府以聚众的感觉,而宋庄绝对不会。想找栗宪庭的人,可以问开“摩的”的:“那个帮你们解决纠纷的白胡子老头家在哪儿?” 路 画家马越说:“有一些住小堡的画家,在一些体面的场合不提宋庄,只提小堡,动不动就说我们小堡画家如何如何。”所以我们所说的宋庄画家村,其实就是小堡村,尽管还有辛店、北寺、小杨各庄、喇嘛庄……宋庄镇的22个自然村都住有画家,但和小堡的核心地位比起来,它们就如同通州和CBD的关系。至少栗宪庭当年的老宅就被画家们称作“中南海”。可是在画家入村前,由于邻近河北,小堡村的GDP会被邻省划走,上级绝不会用小堡作为示范点。崔大柏抱怨说:彭真当年就在邻村蹲点,从来没有领导想起小堡。现在它是宋庄最有钱的村落,人均年收入1.3万元。 你可以从国贸大北窑站坐938支9路,或者930支线到宋庄铸造厂下车。第一批来小堡定居的杨少兵说:“我一般是搭从唐山过来的长途车。”艺术家们是938路上的一景,年景差时,他们蓬头垢面,比农民穿得还破;当代艺术市场火爆时,他们集体进城洗澡理发,回村时焕然一新。画家马越还趁着小堡村没有夜班车的借口,哄着一位洋妞送他回家买画。 这个占地90亩的铸造厂已经不复存在,它和养鸡场曾经是小堡村的两大支柱产业。废弃的铸造厂那里要建造11层公寓,村民全上楼,把民房租给艺术家。这14万平方米的小高层拥有大产权,留一半对外出售。 “村里没变化之前的样子?就说养殖场吧,如果关上窗子打农药,死苍蝇能用簸箕往外撮。再说村里面,因为家家户户搞养殖,1995年时,一方面北京市场上的肉鸡每6只就有1只是小堡村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但另一方面,村里简直没法待:出门是粪,进院是粪;睁眼是鸡、猪,闭眼是恶臭。许多企业来的人都是看一眼扭头就走,根本不考虑投资。”村支书崔大柏说。鸡雏50天就可以长成肉鸡,小堡每年要宰上百万只鸡,谁家一结婚炒菜,苍蝇能把房子铺黑。 现在你远远就能瞧见巨大的“中国宋庄”铁门。“宋庄”的商标倒是艺术家设计的,本来向全国征集了300多个方案都不满意,再由栗宪庭找了村里的几个艺术家,采用上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流行的错体字,把“宋”和“庄”两个字结合起来。这个大铁门非常关键,它使宋庄镇上唯一的饭馆失业了。那个四合饭店骑车需要15分钟,过去是画家们聚餐的必去处,2002年有了大铁门之后,小堡村自己的饭馆风起云涌,到现在已经发展到51家,其中只有两家是村民开的。我们坐进一家招牌和门脸都很大的“中国生态酒店”,店内铺设了假的小桥流水,老板是山西人,一个月顶多来视察两次。菜单上有金元鲍、三文鱼这种豪华食品,也有物美价廉的手擀面。 正对着大门的这条路别名“长安街”,所有故事都发生在这条主路及它的支线上。有一届宋庄艺术节的主题就是“宋庄之路”,名字是艺术家们起的。他们管当年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叫“百货大楼”,现在百货大楼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栗宪庭、方力均他们的老宅所在之处是一条小土路——“柳荫街”,因为一侧路边有几株拇指粗细的小柳树,现在已经颇具规模。小堡的第一家饭馆在人们的叙述中不太统一,老栗的印象是台湾人开的,马越则认为是某个画家的亲戚办的“三元里饭店”。何为三元里?就是每个菜都是三元钱,瓜子免费,墙上贴满了艺术家和画商的联络电话。 崔大柏很尊重画家们,有一次修路时还请艺术家们起名。画家们都很感兴趣,有说叫“学院路”的,有说叫“画家村大道”,也有叫“地主大街”,把名字报到崔书记那里让他选。马越说:“挂牌子那天我们大吃一惊,铁牌楼上的霓虹灯字是:佰富园工业区。书记还说:过两天给你们配两个保安。”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年前,崔大柏书记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后回忆说:“我刚接手这个村的时候,村里根本没有办公室,只有两个老头儿当广播员,他们必备的工具是一个脸盆,一双雨鞋,一下大雨就得往外舀水。村里2/3的农户用不上电,电线东拉西拽的,村民们看哪条线有电就接哪条,我们做干部的寒心着呢。村里也没条下脚的正经道儿,雨一下根本就不知道深浅,我曾眼睁睁看着卖鸡蛋的崔大娘一不小心把满车的鸡蛋全摔了,蛋清蛋黄顺着污水流得四下都是,大娘吧嗒吧嗒的眼泪一下下敲在我的心头。”村联防队队长李学来的形容是:“晴天洋灰路,雨天水泥路,水和泥组成的路。”解放前这段路基是大渠,供田间浇水,废弃多年。如今“长安街”沿路画廊88家、饭店51家和三四十家美术用品商店,画框、画笔、颜料、画布都可以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1995年时村里只有六七位画家,老栗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晚间固定娱乐是搓麻将。没有路灯,杨少兵会借着月色去唯一有保姆做饭的方力均家蹭饭,然后把饭钱输掉。那时“长安街”的东侧是葡萄棚,西侧是村民住宅。 1997年,崔大柏决定修村口和村东的主路,需要村委会投资120万元。村民们集体反对,嫌太贵了。路修好后没有路灯,最早的17盏“长安街”上的路灯是画家们集资2万元,每人1000元。现在小堡村有800盏路灯,是整个宋庄镇的总和。捐完灯后村民有点觉得画家们挺可爱,“非典”的时候,画家们捐矿泉水、捐画,还集体凑了21万元,强烈要求到村口站岗,盘查可疑分子,村民们觉得他们更可爱了。以前画家们挺烦人的,晚上喝多了唱歌、打鼓,有些穷画家总是赊小卖部的账。除了方力均等少数先富起来的人,艺术家们都懂得向新来的人借钱,因为他们身上还能揣着几个月的生活费。李学来收拾画家的办法很多,其中之一是剪电线,他就剪过画家王强的电,等他乖乖认了错,还得自己出50块钱“开口费”才能把电接上。“城乡差别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当地人每度电0.46元,我们0.6元。事无大小,一律不一视同仁。”画家邢波的妻子梁芳在日记里写道。 房 小堡的地理形貌是以“长安街”为干,向东西扩散,主要的文化经济实体多坐落在街边。这条宽14米的大街平时很寂寥,只有“摩的”无聊地等客。一位“摩的”司机告诉我:“艺术节那几天才能多挣个十块八块,平时也就是糊个嘴。”前几百米路程就是普通的城乡结合部的样子,不同的只是美术用品商店奇多,据说今年就新开了7家。再往里走,才会觉出它的特色:前哨画廊是小堡第一家画廊,还兼着饭店功能。那片黑灰色的青砖建筑群叫做国防工事艺术园区,是崔大柏的杰作,他曾经是个泥瓦匠。也有设计师们的作品,第一家民营的上上美术馆、全玻璃结构的龙德轩、香港阔太太筹建的新美术馆。 我随老栗看了他在小堡的老宅——小堡北街126号,对门就是赠他这片土地的艺术家刘炜家——小堡北街124号。刚批下这块地时它是栋歪歪斜斜即将倒塌的房子,石膏顶、土坯墙,几乎没有院墙,杂草把门堵得推不开,门也比城里一般的门要窄小。栗宪庭的妻子廖雯说:“哪里是草,简直是‘森林’,小风一吹,沙沙作响,仿佛《聊斋》中的鬼院。”但是这片小院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其他艺术家也是一样。杨少兵最爱房顶那个黑黝黝的老柁,“你看它,多漂亮!”他赞叹不已。老栗的老院子也非常舒服,现在用做他的“独立电影论坛”办公室,占地近一亩半,一进门几竿翠竹,爬墙虎爬满墙壁,有杏、桃、李子、樱桃、柿子、香椿各种果树,来他家的人都可以品尝。他每年除夕必定要煮上千个饺子,来者有份,院子里养着流浪猫,见人就亲热地趴在身上。廖雯的书房被改造成电影室,你可以随便进去看电影。小院子里摆着艺术家们的作品,贴满了他写的春联。“最得意是我给岳敏君写的:笑脸迎四海看客,大嘴吃八方藏家。” 这样的院子在小堡算中等,最少的租3分地,最大的占地有4亩。越是有钱的艺术家越是高阔的大屋。2003年前的小堡村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公用电话,通讯基本靠吼,村里的大喇叭直到去年还在喊:“方力均,有你的信!”威尼斯双年展的信只能通过邮局,杨少兵每年给邮递员200元钱,才能保证收到邀请函。艺术家们喜爱这里就是因为有足够的土地。杨少兵请董豫赣为他设计工作室,拿来的设计图里厕所2平方米、厨房8平方米。设计师只有小公寓的经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老栗在宋庄美术馆办展览,他的设计师看到美术馆后哭了,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施展。 如果说老栗的老宅算“老区”,他的新宅就应该是“新区”,官方称呼是“小堡文化艺术园区”,沿着“长安街”一路狂奔,看到一汪深水就到了。2003年,老栗看中了这块地,一个落差两米的大坑。当时崔大柏正为这块地头疼,沙地不能种植,有高压线不能建工厂,挖六环挖出的地下水在这里积成了一个深达9米的大水坑,倒是波光粼粼。2002年时,曾经有开发商试图说服崔大柏卖出整个村子,全部盖成两层的商品楼。老栗苦口婆心规劝他保持原始状态,崔大柏想通了,这才有了小堡文化创意园。老栗的新院子就在这里,饭厅就有100多平方米,曾经同时容纳70个人吃饭。有时依然会有初进京的艺术家伫立在门口,迟迟不敢敲门,瞅见老栗的大黑狗“如果”一露面就吓窜了,其实“如果”扑上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和你亲热。 新区采用集中供暖,每年28元/平方米,明年还将引进三河热电厂的废水取暖,相比较穷艺术家烧蜂窝煤、富艺术家自建小锅炉方便了许多。新区里多是已经成名或者很有希望成名的艺术家,他们的入住资格经过了老栗的审核。起初租金是10万元/亩,现在30万元/亩。 艺术园区对面的工作室区就没有这么严格了。有位抱着黑猫、中式棉袄的老头冲我们微笑,老栗说:他从山西运来了每一片瓦,垒成一幢非常完整的、两进的四合院,他们都管那房子叫“深宅大院”,而另一个画家就依着妻子的趣味弄得屋子里非常小资。这个村子就是这样,怪异的、现代的、仿古的,都能存活。老栗不敢停留,新来的艺术家总要拉他进屋去看画,以为这样就可以名扬国际。 老栗说:“小堡是全世界为艺术家服务最好的地方。无论多晚,你要多大的画布,订多大的框,都有人上门服务。”农民们从周边产业尝到了甜头,李学来的哥哥在1997年开了第一家美术用品商店“日月星”,赚钱之后改做大生意——建筑行业,把房子租给外地人。村民史永杨自己开了裱画店,他和老伴两个人干活,外面要600元一幅,他们开价400元,“反正吃饭是没问题”。他以前是修车的,专门上琉璃厂花钱学装裱,我和他说话时他一直没停下手里的活。 最早的农民画廊叫做“韩燕画廊”,民房改建的结晶。门口挂着经营示范点的铜牌,外来游客的参观项目,进去看一眼要交10元钱。韩燕本来只是把房子租给艺术家,她喜欢和房客聊天,聊着聊着发现可以开画廊。不过栗宪庭不太赞同这种做法:“农民找不到下家,客户是画廊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嘉德拍卖公司即将进入小堡。联防队队长李学来说:“等画家们过50年死了,他们的房子就成了故居,卖门票,暂定10块钱一张吧。” 每年宋庄艺术节都会办一次艺术品交易,直到今天“长安街”上还摆放着这届艺术节来不及搬走的装置和雕塑,它们使“长安街”的前后两段泾渭分明——前段是平凡村镇,后段突然冒出个“798工厂”。老栗和镇上商议着要建一个类似于跳蚤市场的低端交易市场,不能让宋庄仅仅成为画家的工作室,还能为他们提供机会。 小堡的房子按建筑模式可以分为几种:工作室、农家小院、美术馆。也有一种聚居型的工作室,比如嫘苑,它建造在养殖场原址上,俗称“鸡场”。与之相对的是喇嘛庄的鸭场。有趣的是,鸡场是为女艺术家准备,花了100万元的改建费用,鸭场住男艺术家,当然现在也没有那么纯粹,男女朋友、夫妻也可混居。小堡散居的七八十名女艺术家终归不太安全,王思丁在日记里记录了一次很惊悚的过程:一名歹徒夜袭,将她脖子划伤。这种翻墙的事时有发生,李学来认为和村民无关,是艺术家们之间的互动。 有了艺术家入住,小堡人心思变,总会发生些其他村子闻所未闻的故事。“长安街”上原来有一家日出画廊,老板娘50多岁,名唤日出,她不太会讲英语,却总和外国艺术青年交往。有一位30来岁的黑人青年保罗,和她好了一阵,借故说要回国,却在某次艺术展览上碰见。日出愤怒地质问保罗为什么还在国内,俩人大打出手。还有一个女村民是寡妇,爱找房客男艺术家聊天,希望他们的关系有所发展,被男艺术家以“她是村妇”为由拒绝了。 小堡的房价是从何时涨起来的呢?起先宋庄一亩地的租价是五六万元,画家严宇看中一个大坑,在上面盖了300平方米的大别墅,村民们看了都感叹,画家们真有钱啊!从此,价格涨了几倍。谈好价格后要立刻拍钱,否则第二天农民就会变卦。2004年一个小院每年租金是五六千元,现在是一万五六千元。奥运会之后,房价有所回落,画家单智说:“很多地方美协退休老师、刚毕业的学生在奥运会前来小堡租房子,村民们大肆把小院改成工作室,至少有上千家个人工作室。大家都想着奥运期间外国人会大量地来看画,没想到最萧条,扛不住的人都走了。” 谁是小堡最有权力的人?李学来说:“基本上你提大柏书记就管用,但也不是全管用,要分片。”村委会5个干部,村子分为4个板块,工业区、艺术园区、商业街归3个姓崔的村干部管,原生态村庄归周副村长,在不同的管片提不同的人。“在艺术园区提老栗也行,很多村民不认识他,但管理层都认他。” (参考书目:马越著《长在宋庄的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