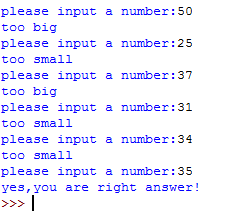◎袁越 在云南省怒江州,有一个普米族小村子,为了保护原始森林,至今仍然拒绝修路。 从地图上看,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玉狮场小组位于丽江的正西方向,两者直线距离只有50多公里。但是,要想去那里,先要从丽江坐5小时的班车到一个名叫“81公里”的地方,再搭蹦蹦车到一个名叫通甸的小镇,从镇上包车去河西乡玉狮场小组只有一条被废弃的山路,全长35公里。我花了350元钱包了一辆面包车,这种车在当地人眼里就是越野车。 这是我走过的最颠簸的路,开了两小时只走了不到20公里。那位司机实在心疼他的车,把我转交给一个当地青年,用摩托车载我走完了余下的15公里。山里有个锌矿,来了不少外地工人,这辆摩托车就是这些工人往来河西乡唯一的交通工具。据开摩托的青年说,这辆价值5000元钱的摩托车开半年就会被这条路给颠坏,于是他每年都要买两辆新的摩托车。不过,他运一次人收费100元,可见这份工作还是能赚钱的。 和云南的大多数山路一样,这条路也是80年代为运木材而修的。如今大树早已砍光,只剩下光秃秃的荒山,以及少量退耕还林后慢慢恢复起来的杂木林。 玉狮场传奇 玉狮场在中国的环保界非常有名,但起因却是一个文化人2002年的一次意外邂逅。那一年,著名作词人陈哲到云南采风,意外闯进了玉狮场。这是一个纯粹的普米族村落,周围是大片真正的原始森林。村民们依然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家祭祀祖先,出门祭奠山神。为了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森林,他们一直拒绝修路。 陈哲被感动后组织了一个普米族传统文化学习班,拉来赞助在村里建造了一个文化馆,甚至还自费邀请村里的年轻人到北京表演传统歌舞。由于陈哲的宣传,包括“地球村”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都曾派人来考察,不少媒体以“保护森林,拒绝修路”这样的标题报道过这里的情况。这些报道中提到最多的人就是村里一个头人的后代、曾经当过8年副社长的杨金辉。 杨金辉今年刚满50岁,身材消瘦,肤色黝黑,不苟言笑,头上永远戴着一顶粉红色的绒线帽。他自己介绍,80年代初期,他领导玉狮场村民用暴力对抗前来砍树的国家林业工人,被当时的怒江州州长称为“一次小型的农民起义”。 “为了不让他们砍树,我们去乡里打官司,没用,于是我组织了几十个村民,晚上偷偷过去把他们切割好的木板砍坏。” 由于村民的努力,村子周围保留下来将近8万亩原始森林,但这个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99年退耕还林时我们玉狮场退掉了1000多亩耕地,可国家的赔偿金一直没有发给我们。”杨金辉说,“乡领导说,不修路就不给赔偿金,这是国家规定。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规定?还不是因为领导看中了我们玉狮场的原始森林?” 云南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玉狮场拒绝修路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杨金辉家算好的,一家6口人住一幢用圆木搭建的二层小楼(当地人叫做木楞房),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组合音响,此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杨家一年的收入有5000多元,大部分花在了3个儿子的教育上。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生和初中生可以不交学费,但生活费还要自己掏。玉狮场的小学只有3个年级,大一点的孩子要想上学就必须寄宿在河西乡,每个月伙食费至少要120元。当年杨金辉的3个儿子都在学校读书,每年要花5000多元。后来大儿子杨笑天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读中专或技校的话每年要掏8000元学费。杨金辉供不起,只好让他回家务农。 “我们家的生活算是可以的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杨金辉说,“但我们再穷也不能砍树,那是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 “传承”是杨金辉最爱说的两个字,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玉狮场文化馆馆长,这个馆是由福特基金会出资修建的一幢传统式样的小楼,就修在杨家门前。小楼有两层,一楼是图书馆,里面散乱堆放着几百本书,大多是小说,还有一些致富小窍门之类的实用书。二楼是活动室,墙上贴满了当年“办活动”时拍的各种照片。如今通向二楼的楼梯被封上了,因为杨金辉把二楼当做了晒麦子的地方,怕猪偷吃。 文化馆前有片空地,几个孩子在比赛用手抓苍蝇。杨笑天也在,但他只是呆坐在一旁看一群小猪吃奶。我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我:“想搞音乐。”说完又立刻补充说:“这是不可能的,想想罢了。”他有一把木吉他,是陈哲托人从北京带给他的,从学校里回来后他一直在跟着一盘磁带自学弹琴,可惜他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和弦,只会弹单音,弹出来的竟然是《香水有毒》的旋律。 杨笑天的表姐,也就是杨金辉的侄女杨德秀,当年也和杨笑天一样,初中毕业后因为读不起高中而回乡务农。陈哲把杨德秀带到了北京,和其他几名普米族少男少女一起组成了一个表演团队,参加过多场演出。如今杨德秀已经在北京待了5年,中途只回来过两三次。她妈妈常常会拿出女儿的照片,细细端详。虽然想女儿,但她仍然认为女儿应该留在北京。山里人能走出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当天晚饭吃的是米饭,菜是用大锅熬出来的土豆青菜汤,里面有几片切得很薄的腌肉。第二天晚饭也是如此,只是把米饭换成了玉米面。 晚饭是围着火塘吃的。传统普米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火塘,他们用火塘取暖、烧水、烧饭,晚上则睡在火塘边。普米人烧火不用灶,热量的利用率很低,所以每天都要烧掉大量柴火,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烟味。“以前烧掉的还要多呢!”杨金辉说,“后来我们用上了棉被,冬天睡觉没有那么冷了。” 火塘面对大门的一侧是不准人坐的,那是祖先的位置。普米人对祖先的敬重溢于言表,他们经常会指着某样东西说“这是祖先使用过的”,或者指着某个地方说“这是祖先曾经坐过的地方”。在玉狮场这样的古老村寨,人们仍然住在祖先住过的房子里,很多东西都已经用了上百年。 如今的玉狮场,围坐在火塘边喝茶聊天的只剩下了老人,年轻人要么在外面读书打工,要么被陈哲带到了北京。留守的年轻人也已经发现了新的精神图腾,那就是电视。晚饭后,杨笑天和几个小伙伴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一部描述富豪生活的电视剧,剧中人住在带花园的洋房里,开着名贵跑车出入高级社交场所。这几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出过县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全都来自电视剧。 原始森林印象 第二天,杨金辉带我去参观原始森林。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公园的人,真正的原始森林似乎并不好看。这里的林木参差不齐,地上随处可见被风刮倒的树干,没人清理。由于林木长得茂盛,阳光照不进来,加上松针的覆盖,使得杂草很难在林子里生长。于是,林地里通常只能放羊,牛和马都被赶到很远处的一个开阔的草甸上放养。 原始森林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大树。玉狮场周围就有很多胸径在1米以上的榧木,树干笔直,没有明显的结点,在如今的木材市场上肯定价值连城。附近的杉木也有很多,红豆杉、冷杉、云杉和铁杉都很容易见到。不过这片森林里最多的树种就是云南松,估计要占总数的90%以上。相比之下,云南南方到处可见的桉树在这里连一棵都找不到。 “北京的环保组织曾经发起过一个认养大树的活动。”杨金辉说,“绿家园(环保NGO)的汪永晨亲自来这里给很多大树编了号,从1号一直编到66号。我们村分到将近1万元的认养费,每户人家分了100元。” 100元钱在这里可以买到50斤大米,而大米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口粮。据玉狮场主管行政的副社长杨道光介绍,玉狮场一共有85户人家、360多口人、589亩耕地。如果只是人吃,这些地出产的粮食肯定够了,但是玉狮场几乎家家有牲口,喂牲口需要粮食,这样一来589亩地就不够吃了,只能下山买粮食。 卖牲口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现金来源。一头肥羊能卖400元,马和骡能卖1000元,牛最贵,一头能卖到1500元。但是玉狮场人不轻易卖牲口,它们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帮手。 随着一阵铃响,两名妇女赶着3匹马从远处走来。她们是去自留林运柴火的,每趟单程要走半小时,一天能走6趟,运回家的柴火可以烧一个月。我告别了杨金辉,跟随她们进山运了一趟柴火。一路上她俩抱怨不停:“前两年来过不少城里人,在村子里挂了好多牌子,可我们仍然没钱,生活一点也没得到改善。” 路上我还遇到一个上山挖药材的小孩,他挖了一天只挖到小半篮子的草根,晒干后大概有1公斤左右,能卖10元钱。“现在这种根很难挖到了,必须要爬到很高的地方才能找到。”他说。他是一个小学生,今年上5年级。 “我听环保组织的人说你们这里的原始森林出产一种蘑菇,能卖很多钱呢。”我问那几个运柴火的妇女。 “那是羊肚菌,每公斤能卖500元。可是森林里很难采到这种菌子,必须放火把林子烧掉才能长出来。” 一路上我看到好几片被烧掉的树林,杨金辉曾经告诉我,这里的冬天气候干燥,很容易着火,我看到的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山火。“附近有很多黎族人为了养菌子,会偷偷地放火烧山。”两位妇女偷偷对我说。 林权,改还是不改? 运完柴火,我又回到村里随机拜访了几户人家,发现他们大都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村民杨黎是玉狮场的社长杨胜的哥哥,他家一共5口人,住在一幢黑乎乎的木头房子里,屋里都是苍蝇,一只小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家的现金收入全靠卖牲口,每年能挣2000多块,大都换成了大米和孩子的生活费。他连每度4毛钱的电都用不起,每个月只用二十来度电,那台电视机明显只是个摆设。 “你家里现在一共有多少钱?” “不到100块吧。”他笑着说,“不过我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饿不着。我们玉狮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路,看一次病很麻烦,去年村里有个老人就因为送治不及时,死了。” 杨黎对我说,村子里其实还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下的河西乡。但是,按照乡领导的说法,这条连接河西乡和玉狮场的小路属于“乡组公路”,国家不管修,要修的话就只能修“乡村公路”,即从河西乡修到箐花村的村委会所在地箐口小组,再想办法绕到玉狮场。 “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就是为了边修路边砍树。”杨金辉说,“我们玉狮场只同意修这条小路,全长只有8公里,从这条路走路下山比坐摩托车(绕道)还要快。” “可是,这条路只方便了你们小组的这360口人,也许国家觉得这样做不划算吧。”我对杨金辉说。 “那也不能砍树。”杨金辉坚决地说,“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明白一点:现代科学再发达,也造不出这些千年古树。” 有意思的是,箐花村其实已经开始砍树了。箐花村现任村长杨周泽是玉狮场人,曾担任过玉狮场的社长。他当年和副社长杨金辉并肩作战,是保卫原始森林的功臣。可当上村长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去年林业部门拨下来一批采伐指标,他批准箐口小组采伐了一批林木,卖了70万元,箐口小组的村民每户分到2800元。这件事对玉狮场人震动极大,不少人眼看邻居们发了财,很眼红。 “你们为什么不可以采取间伐的办法呢?”我对杨金辉说,“你们村有8万亩山林,即使每亩每年新增的木材蓄积量只有0.3立方米(中国森林的平均值),每年也能新增2.4万立方米的木材。假如你们每年只采伐其中的1/3,而且严格采取间伐,每片林子只伐一棵。那么,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你们村每年能多得300多万元,而森林依然能够可持续发展,这不是两全齐美的办法吗?” 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不行,坚决不能开这个口子。”杨金辉的态度依然坚定,“现在很多地方领导一点党性都没有,一心只想着捞钱。只要口子一开,后果很难预料。” 作为一个当过8年公社领导的人,杨金辉的话很可能有道理。但是,他一个人的坚持能起作用吗?尤其是去年开始的林权改革,把集体林的处置权下放给了老百姓。在金钱诱惑下,玉狮场的老百姓还听得进杨金辉的话吗? “我们玉狮场没有进行林改。”杨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去年他们几个领导开了个会,宣布说玉狮场的集体林不分了,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

“玉狮场的决定是村民投票做出的,我们有8万亩集体林,确实很难分清楚,所以就没分。”副社长杨道光向我解释说,“而且集体管理对于森林的防火防虫都很有好处。” 说这话时,杨道光的眼神飘忽。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没有跟我说实话。 等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和杨金辉又一次坐在火塘边聊天。我说起我在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村民们的真实想法。 “他们都是外来的,对森林没有感情。”杨金辉摆了摆手,对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虽然是党员,但出身不好。当年我考大学时因为成分是地主,被另一个出身贫农的人给顶替了。玉狮场最初只有3大家族,整片山林都是我们3家人的。后来因为劳动人手不够,就从外面雇了不少奴隶,解放后这些人都成了玉狮场的村民,所以现在我们有5大家族了。你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来户,对森林感情不深。” “我们想把附近这8万亩森林都变为玉狮场的集体林,但是政府不同意,只分给我们2.37万亩,其余的要变成国有林。”杨金辉又说,“可是,当初要是没有我们的保护,现在哪来这8万亩原始森林啊?” 原来,玉狮场之所以至今仍未实施林权改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天晚上我俩讨论了很多看似既能保护森林,又能脱贫致富的办法,比如发展生态旅游,或者采药等特种经济,结果都不可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政府。”杨金辉叹了口气,“政府要是肯出钱修路,就不用砍我们的山林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