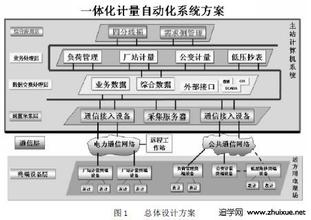肖知兴 东西方的很多不同都可以归结到分工产生的各种专业和专业精神上。涂尔干首先在《社会分工论》阐述了现代“有机”社会与前现代“机械”社会的最重要不同在于社会分工的多样化。分工不发达的社会中,社会与个人间的关系是“机械性”的,让整个社会保持凝聚力的是一种所谓的“集体感情”,人们以“报复性”行动惩罚对这种集体感情的偏离,维护这种集体感情的神圣性。而在分工细化的社会,立场和利益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不得不平心静气,依靠“恢复性”的法律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里目光如炬地把“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当作儒家的中心思想,阐述了儒家对各种专业技能的轻视以及这种轻视如何成为中国社会的理性化、科层化发展的根本障碍,与西方新教中的“天职”观念和建立在这种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现代职业精神、专业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儒家也往往辩解说,“君子不器”不是轻视专业,是强调通才。如孔颖达说“圣人之道弘大,无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为诸器之本也”,朱熹说“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话虽然说得好听,但在现代社会讲“无所不施”“体无不具”,听起来就有点不着调。 令人叹服的是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李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业余主义”的概念。他说,集绅士、文人、官员三种身份为一体的中国士大夫们的真正理想是成为一种“业余爱好者”:“他们是最完全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致力于各种有品位的高雅活动,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感觉,对商业没有同情,对各种实用的东西没有好感。在治理国家方面,他们是业余的,因为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在艺术上;即使在艺术上,他们也有一种业余爱好者的偏见,因为他们正式的职业是从政。” 我觉的他说的还算是客气。很多这种中国特色的“业余爱好者”,一方面打着弘扬“圣人之道”的旗号,瞧不起任何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专业:如何讨好上峰,讨好皇帝,在权力金字塔上更上一层楼。张爱玲说“女人都是同行”,言下之意他们都要想尽办法讨好男人,“妆罢低声问夫婿,化眉深浅入时无”,其实中国的男人同样也是同行,他们都要想尽一切办法讨好权力。权力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过是雕虫末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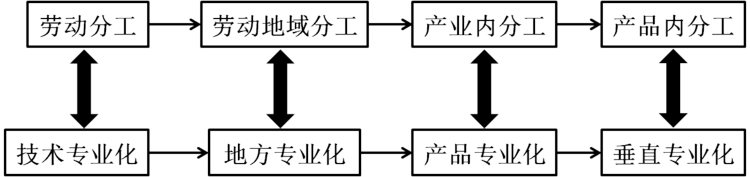
了解了这个大的背景,中国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例如,张鸣慨叹,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以及这种官场化在意识形态空洞化之后变本加厉形成的“黑社会化”,其实都是这种业余主义的自然结果。我做学问应该算是半路出家,与国内的学术圈交往非常少,最近才发现一些中国教授好像从来不读书,而且非常心安理得地不读书。一个教授一天两天不读书不难,难的是十几年、几十年不读书!大家有时候也嘲笑西方学术的专业分工,有时候确实也细到让人觉得荒唐的地步,但至少他们也能做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没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可我们中国的教授们,首先什么是他们的专业,你就不太容易弄清楚。学水电专业的人力资源教授,宏观经济学家摇身而变成的管理大师,最奇怪的是那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工程”: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才培养系统工程、金融创新系统工程、城市交通系统工程...... 又例如,最近某著名经济学家升了“世界级”的官,把一些人给兴奋坏了。其实,真要以专业的标准衡量,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成绩,不过是“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权在有关国际机构提升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媒体们受宠若惊地享受着“反射的荣耀”的时候,我注意到的是该经济学家给拥上来的粉丝们签名的书,还是14年前由三个作者合著的那本内容颇有争议的书。如果这就代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那我们真不知道应该为中国经济学喜还是忧。最可怕的是他那些完全放弃了学术原则和专业精神的荒唐言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以10%的速度增长30年,中国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奥运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之类。他难道不知道扮演这种能掐会算、跳大神的角色给自己的专业名声带来的伤害吗? 你可以跳,我也可以跳,最近大出风头的是同一研究机构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与人对赌深圳房价是上升,还是下跌。只见他一会儿说我赢了,不会道歉;一会儿又道歉了,但又说我没输。学者不是不能在公共问题上发言,学者转型做或兼做公共知识分子,古已有之,西方的好榜样也同样多得是,但公共知识分子也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性。我就是不明白,所谓“媒介常客”、“快思手”之类的这些人,怎么就是有把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演成闹剧的本领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