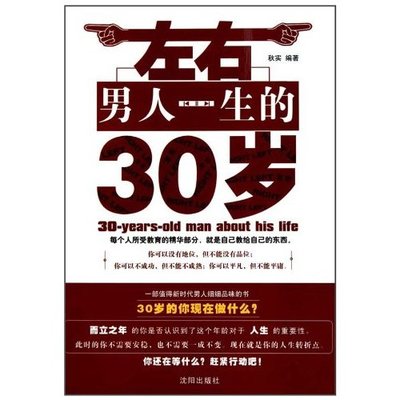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撰稿·毛尖 华东师大副教授、专栏作家
饭桌上,罗岗这样描述最可怕的人生:你在师大出生,你爸是师大的,你妈也是师大的,你们住在师大宿舍,你跟对门小姑娘青梅竹马长大,她妈是师大的,她爹也是师大的。你和小姑娘先在师大附幼,然后师大附小,然后师大附中,然后师大,一路同学上来,毕业以后双双留在师大。你们结婚,你们生孩子,孩子继续,师大附幼,附小,附中…… 可吴晓东淡淡一笑,他不这么看。《漫读经典》中,他用“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解释了传奇。托纳托雷的影片《海上钢琴师》,他拿来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对读,“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一种以有限去叩问无限的逻辑,他们穷极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以有限叩问无限,几乎就是晓东的姿态。十年前,我们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认识,罗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绍他,他眼神温暖、温文尔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苏曼殊云“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感觉,所以大家使劲说话,小时候那样,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结果表现出了疯癫。但晓东只是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没听他说过他妈的,没见他笑到头发乱,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他没有一分钟失态,也一分钟不曾苟且。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事实上,正是在晓东身上,我第一次意识到,狂热或者说狂爱,并不是文学研究者的DNA,换句话说,敏感和沉潜才是激情的最佳赋形。 “敏感又沉潜”,这是晓东对青年加缪的概括,后来,“敏感”被他用来描绘过张爱玲,“沉潜”被他用来形容过“S会馆时期的鲁迅”,我觉得这也准确地概括了晓东本人。读《漫读经典》,很多次,我为他无与伦比的诗学解读能力所倾倒,而这种能力使这本书的写作,遥遥地越出了批评范畴,成为创作,成为激情的隐秘表达。 《阳光·苦难·激情》是晓东的一篇早期文章,我记不清自己在各种场合多少次地读过它,因为他文中引到的茨维塔耶娃的著名独白,“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我看了茨和有关茨的很多文章和书,终于在茨的传记中重新看到这句话,却反而不那么激动。后来我明白,这些引文经过晓东的再叙述,恰似春雨楼头尺八箫,不必再问樱花桥。 所以,拿起《漫读经典》,你可以先把书中的引文看一遍,它们就像加密的线索,勾勒了晓东的抒情地图,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张代表性的抒情地图,一半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中国阅读,一半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陆阅读,合在一起,它显示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激情和抱负: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 同时,这个备忘录,因为其鲜明的中国胎记,也可以被视为吴晓东对中国感性世界的诗学整理。书中,无论是卡夫卡的寓言,博尔赫斯的想象,还是福克纳的时间、昆德拉的存在,都在指向这些作家的中国旅程。而且有意思的是,异域十篇和本土十篇有着几乎是精心策划的对称性,比如,1990年8月,他写下了《失落者的歌唱》,讨论了萧乾的激情,隔了四个月,他描绘了加缪的激情;2004年3月,他完成《尺八的故事》,追踪了卞之琳的文化乡愁,5月,他写下《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深化了同一个主题,用他的引文来表达:“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绵不断,比生命更长久。”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很多人事变迁,但晓东一直在北大。这些年,也只在大大小小的一些会议中和晓东碰面,好像总在告别。那年山西会议,我们一帮上海去的打道回府,晓东因为比我们晚走,一个人来送我们一帮人,买了很多吃的喝的,我们在检票口和他挥手,想起一句话,“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学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