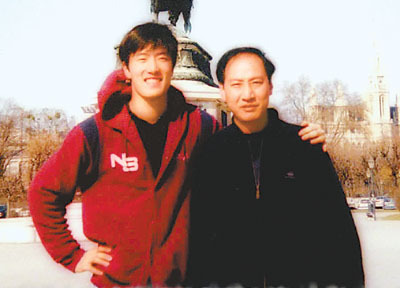“他始终站在三种力量的交叉点上:主流政治、知识分子和民间大众。”
◎ 曾焱
比别人更幸运的“前进青年” “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走到一起来了。”毛主席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说的这句话,字面上看来简单,对上海电影界的很多当事人来说,却是一场磨合的隐痛,长久不散。 上海解放半年后,1949年11月成立了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段时期,一批私营和公私合营的电影公司也继续拍电影,《武训传》和《我这一辈子》就是私营公司文华的出品。黄佐临、桑弧、石挥等明星艺术家都在文华,它的片子卖得好,那时在私营公司里面是唯一有钱给员工发红包的一家。“两支大军”,实际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文的和市民大众的上海电影,革命的和政治的延安电影。上海电影传统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主流,在重庆和上海接受艺术启蒙教育的谢晋自然受到上海电影传统影响。不过和石挥、吴永刚、汤晓丹、孙道临这些老上海电影人比,谢晋1949年以后的处境要简单很多,没有太多旧包袱需要卸下,努力跟上就可以。 那个时期的电影人,怕的就是被新时代抛弃。谢晋、孙道临在世时,上海电影集团的总裁任仲伦和他们都是私交很好的朋友,常过去与老人聊天。任仲伦说他曾问道临老师,最喜欢自己演过的哪个角色,是不是《早春二月》里面的萧涧秋?孙道临说不,是《渡江侦察记》的李连长。任仲伦先是惊讶,后来也就理解了他的心态:“刚解放那两年,道临老师这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电影人很惶恐,他曾主动写报告要求不再演戏,说我外语好,让我去做资料翻译吧。《渡江侦察记》成功后,他成了国统区演员转变的一个标杆,连上官云珠也敢演革命人物了。这个角色给了道临老师走向新时代的勇气和自信。” 谢晋比他们都幸运,几乎和新中国一起站在了起点上。他先是离开大同影业公司,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长江电影制片厂。这是个新厂,有技术人员,没创作队伍,只好遵照领导指令从私营公司借人,谢晋就这样作为副导演,被借进了长江厂的《控诉》剧组。1950年,领导又选送他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8个月。分配时,谢晋没再回私营的大同公司,正式调进长江厂。对于谢晋,这不仅是组织安排,也是他私人最乐见的选择。虽然私营电影公司的薪金更高,民营公司的人还是都愿意转投国营或者公私合营厂,去了这些地方,意味着告别旧环境而被全新的政治文化氛围接纳。回想那时心境,谢晋在2007年对上海大学教授、谢晋研究者石川说过这么一段话:“其实我过去的片子,特别是‘文革’前的片子,按照现在的观点看,主体内容还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一种新旧对比……这种对比现在也许有人会认为有点简单了。毕竟那时我还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思想还不是很成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不深入。但是,这种对比,却是我自己一种真实和强烈的生活感受。”1957年他拍《女篮5号》,讲的是田振华这个老运动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种命运;1960年拍《红色娘子军》,是吴琼花参加红军前后的不同思想境界对比;到1964年再拍《舞台姐妹》,仍是一旧一新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对比。“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单纯解读为谢晋迎合主流政治并不确切。”任仲伦说。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始终有一种要拥抱着、欢呼着的情感,他们确实从心底认为社会是进步的,而社会的每一个变化,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命运,“大情大义,忧国忧民”。 1952年,文华、昆仑、长江等20多家私营和公私合营公司全部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的速度这么快,是因为北京的工农兵电影人对上海的市民电影开始了批判,已经竭力靠拢新中国政治氛围的私营公司不知所措,维持不下去了。之前两年‘剧本荒’的时候,观众没戏看,时任上海军管会艺委会主任的夏衍为了鼓励创作积极性,提出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反人民、不反苏联就可以拍,但实际操作时出了问题。比如在1951年拍摄的影片里,石挥导演的《关连长》、郑君里导演的《我们夫妇之间》就遭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批评’。”石挥的罪状之一是他让关连长在影片里说山东方言,有意丑化解放军。到批判《武训传》之后,私营公司都不敢拍片了。谢晋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进入国营上影厂,作用很快就凸现出来。“科班出身,新中国成立后受过革命大学的文艺政策培训,他的机会比单纯国统区背景或者来自解放区但不懂戏的人都要多一些。1953年谢晋得到拍淮剧戏曲片《蓝桥会》的机会,1954年又受命和东影厂的林农联合执导影片《一场风波》,剧中演员有大明星舒绣文以及后来出演《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的师伟。谢晋跟我说,林农比他大几岁,也爱喝酒,两人相处很开心,拍完这部片子后成了莫逆之交。”石川看过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资料,在中央电影局上世纪50年代的一本内部刊物上他发现了一则通告,文中提到电影局艺委会的人对《一场风波》很欣赏,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蔡楚生还特别表扬了谢晋。石川觉得,应该是从这时候开始,谢晋进入了高层的视野。“这些内情谢晋本人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我把通告内容说给谢晋听,他惊讶极了。” 1955年中央电影局以文件形式公布,提拔4位年轻副导演升任导演,当年这在电影界是件很轰动的事情,“我记得有上影厂谢晋、东影厂林农、北影厂郭维,另一个想不起来了。这种提拔类似行政级别,而且以文件形式下达,是很大的荣誉”。林农后来拍出了《党的女儿》、《甲午风云》、《兵临城下》这样优秀的影片,郭维执导的《董存瑞》也成为经典。资深电影评论家罗艺军说,林农和郭维都是从解放区过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唯有谢晋来自国统区,可见业务非常突出,政治上也得到了信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把上世纪50年代的谢晋归类于“前进青年”,一个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按照那个年代的工农血统论,谢晋的出身并不怎么好。老年谢晋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跟主持人聊小时候看越剧的事情,说自己在家是个大少爷,经常坐在长工的脖子上去看戏,见到那些唱戏的孩子很同情。抗战胜利后,谢晋从重庆肄业回到家,书香门第的父亲坚持送他到南京续念两年国立剧专、拿到文凭,如果不是碰上解放,父亲还为谢晋安排好了去美国留学。“不过放在上影厂,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已经算是单纯的了。国统区的电影人背景交错复杂,有张瑞芳这样的左翼影人,赵丹、秦怡这样的进步影人,也有自由主义的费穆、桑弧等,后来还有一批从香港回来的人。谢晋是后辈,在上海时间不长,背景简单,关键是他业务好。”石川说。 谢晋运气也好。他刚被提拔为导演,就到了酝酿电影体制改革的1956年,创作自主权下放到电影厂,他才有机会自己选本子,参与成名作《女篮5号》的创作。改制前,电影界完全照搬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拍什么、谁来拍,都由北京的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决定,各电影厂只是生产部门。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石川举出一个例子:有一次,上影厂录音车间的灯泡坏了,打报告给北京的电影局技术组,得到批准后才敢换。1956年秋天,蔡楚生率中国电影代表团到东欧访问,主要目的就是考察电影改革,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自由选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上海电影界领导也倡导自由结合创作集体。在这种气氛下,上影厂人自发成立了3个创作小组:应云卫、孙瑜、陶金和吴永刚自组“五老社”;沈浮和赵丹、郑君里等人是“沈记社”;石挥、谢晋、白沉、徐昌霖和编剧沈寂组了“五花社”,石挥当社长,谢晋是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谢晋是体育爱好者,参加了上影厂足球队,1954年还在球场上被人踢断过右腿。因为喜欢体育,他认识了很多老运动员,经常和他们聊天,运动员身上那种扬眉吐气的翻身感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强烈,这在谢晋身上找到了共鸣。”谢晋用两个月拍摄、两个月制作完成《女篮5号》,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用来对外交流的影片,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拍当代生活题材,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谢晋巧妙利用了这柄“尚方宝剑”,在这部政治主题片中,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呈现了自己的文化趣味和处世智慧,就像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后来评价谢晋电影,“将革命的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和好莱坞的故事策略成功加以融合,将革命主题和中国早期电影的市民传统结合,成功地寻找到把革命转化为感伤的文化经验的方法”。石川说他反复看过《女篮5号》,觉得谢晋很“狡猾”。刘琼演的男主角,离开上海后那段经历在剧中并未具体交代,谢晋只是在他的球衣上印了“西南军区”4个字,实际上这就补足了人物的身份背景,意味着此人已经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城市球员变成了革命者,剧情往下顺理成章,让人无从挑刺。石川说,观众如果愿意,从这4个字还可以得到更多联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西南军区是新中国体委主任贺龙的部队,西南军区篮球队在解放初期也确实是全国实力最强的球队。在政治主题之外,谢晋也不轻易舍弃旧上海的市民电影传统,他擅长把个人的小我感受,放到影片的大背景里去,而且在这一点上他很执著,但做得也很聪明。刘琼在剧中穿的那身仿革夹克,是谢晋自己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街头最时髦的衣服样式设计的,他一直很得意这件事情。剧中秦怡父亲的装扮也是当时最好的。还有两个细节耐人琢磨: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刘琼总带一盆兰花,比赛前给队员排兵布阵,他使用的道具是一套木偶不倒翁。“兰花、不倒翁,这些都是当时上海市民最熟悉的生活趣味,观众看了当然觉得亲切。我后来和谢导谈起这几处细节安排,他都不记得了,所以我说这是他的一种本能。”同时期其他电影厂其实也拍过体育电影,观众都忘了,因为缺少人情和生活,光剩下政治符号。“这就是谢晋的不凡之处。正是这些生活的小情小趣,使革命叙事不再僵硬,有了市民阶层能接受的柔性外观。” 陈山则把《女篮5号》称作一部“新时装电影”,既保留了谢晋上世纪40年代末在大同影业公司学到的海派时装片风格,又有新中国的风貌。“他选这个题材,其实糅合了各种流行因素:旧时明星、爱情戏、新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最时尚的运动,连配乐也是上海的轻音乐风格,而不是革命歌曲。”这部片子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拿回银奖,在电影院放给观众看的时候,票房又极好。从这里开始,谢晋其实认同了一种渗入和融合的方式,最终建立起谢晋的电影哲学。“他始终站在三种力量的交叉点上:主流政治、知识分子和民间大众。”石川说。于创作,于生活,这都是他一生不变的哲学。 总有不愿妥协的时候 谢晋苦中作乐、随遇圆通的性格在四川江安时期就形成了多半,据他跟石川说,抽烟、喝酒也是那时候学会的。《庐山恋》的导演黄祖模大谢晋1岁,上世纪40年代两人同在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求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同进上影厂,两家一直要好。黄祖模和夫人贾舜华的婚姻,还是谢晋无意中做的大媒。关于少时这段求学往事,黄老在2005年第4期《电影故事》上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他写道:当时曹禺、张俊祥、洪笙、陈白尘、焦菊隐等人都是他们的老师,整个学校二三百人,有高级职业科、乐剧科、话剧科,唱唱跳跳都特别开心。为了筹集伙食基金,学生们经常搭台演京剧,通常是黄祖模唱、谢晋打钵、另一个班的陈同学打板鼓——此人后来成了北影的大导演,就是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农民们没钱,拿着鸡、捧着菜过来换戏看,学生演一次,得的伙食能吃好几天。 石川听谢晋在江安国立剧专时期的同学说,1949年前,谢晋并不是个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学校搬去四川的时候,“皖南事变”刚发生,寝室里的同学热衷讨论时事,谢晋很少参与,只是埋头读书。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大家很服他:为了管理年轻学生,国民党往戏专派驻了一批学监,三四十人住的学生宿舍,每间安置一个。他们寝室的同学都讨厌这个学监,又不敢公开和他冲突,不关心政治的谢晋这回却乐意帮忙,因为他也不喜欢这个人。他逮了一小瓶子臭虫,塞进学监的被子里面,就这样把人给赶跑了。
在谢晋的一生里,某些时候他会执拗地显出这份不肯妥协来,变得和别人眼中“有判断本能和生存智慧”的那个谢晋不一样。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编辑给谢晋找来了《红色娘子军》剧本,他一看就很喜欢,尤其偏爱里面洪常青和吴琼花的3幕爱情戏。1959年片子拍摄制作完毕,谢晋把爱情戏都拍了,结果在审查时通不过,上级领导要求把爱情这条线删掉,谢晋抗命不干。电影局开会讨论后,改为删掉爱情场面,谢晋还是不干,说除非是党委决定。他在国立剧专的老师、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张俊祥于是说了一句话:“谢晋,那就算是党委决定吧!”谢晋沉默了半天,照办了。《红色娘子军》得了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也为谢晋带来无数荣耀,但他对剪掉的爱情镜头始终耿耿于怀,到晚年仍经常提起,引为大憾。 《舞台姐妹》是谢晋在第一个高峰期的转折点上的作品,也是在他“文革”前创作中,唯一一部和主流政治气氛不搭的电影。1964年片子拍出来,1965年被批判,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公映过,全国都是作为内部批判片来放映。谢晋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回忆更有意思:刚拍到一半,就知道上面要批这部电影了,而且不让改剧本,张春桥的意思是就按初衷拍,一个字不许改,改了找你问罪,因为改了批判就没了靶子。“那我就拍吧,该怎样还怎样。”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谢晋的倔强一面反而显山露水了,像老朋友形容的晚年的他,“别人的话都不听,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拍摄完成后的《舞台姐妹》镜头优美,充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那两年,全国有多部电影成了“毒草”,《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和《北国风光》3部片子受批判的等级最高。谢晋另一部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也和《聂耳》、《白求恩大夫》等影片一起进入毒草行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认为,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谢晋已经隐约意识到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在竺春花身上,实际上寄托了谢晋的人格理想,“这部片子里,新海派的味道又出来了,但已经不同于《女篮5号》时期的明亮,已经向悲凉处转,是他自己心境的反映”。 “文革”期间,谢晋被下放奉贤干校,和杨小仲导演住一个屋。杨小仲是第二代老导演,也是中国拍片数量最多的一个导演,1960年他执导的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深受观众喜欢。他们两人经常坐在一起聊些电影圈里的事,谢晋每次都眉飞色舞,看不出一点发愁的样子。杨小仲奇怪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还能开心,谢晋答,在那种环境里,你自己不去寻开心,你怎么活?石川说:“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心态。谢晋追求中国文人传统中的诗情画意,但这个文人传统是多维的,有诗意,也有大丈夫不平则鸣的诗骚。在谢晋身上,我有时候能同时看见李白、杜甫和八大山人的影子,所谓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一些谢晋研究者会有意回避谈论他的两部作品:1975年的《春苗》和1976年的《磐石湾》。2007年,谢晋的儿子谢衍和两位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6册本《谢晋电影选集》,选入18部电影,在面对“文革”这个历史阶段的作品时就很为难,最后选的是1977年那部《青春》。谢晋自己提这两部电影也少,但至少非常真实、坦率地谈论过一次:“有人问我:你在‘文革’中拍《春苗》、《磐石湾》,艺术家的良心哪儿去了?我的回答是:‘文革’的时候,我们都还没觉醒。那时,徐景贤宣布我和傅超武‘经过七斗八斗,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时,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不是张志新,张志新特别可贵,但作为电影人物来拍,却就不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问我话的人恐怕也当不了张志新。”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谢晋就是这样的人,永远领先一步,而不是十步。 和老电影人的交往1947年谢晋进入柳中亮经营的大同影业公司,这是从话剧转向电影的第一步。大同拍商业片较多,作为助理导演和副导演,他参与了《哑妻》、《欢天喜地》、《几番风雨》、《望穿秋水》4部影片,跟的都是“张石川系”导演,比如重庆时期的老师吴仞之,还有黄汉、郑小秋、何兆璋。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李道新认为,这段经历对谢晋艺术风格形成有难以忽视的影响:在协助“张石川系”导演拍摄的过程中,谢晋更多地学到了如何讲述一个曲折动人的电影故事以及如何照顾最大多数电影观众欣赏趣味的电影手段。尽管这种电影手段并不具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尖锐色彩,也不具有《太太万岁》的汉学蕴藉,更不具有《小城之春》的探索特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大众做派颇为类似。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蔡楚生和郑君里合导的影片,这两个导演,日后都对谢晋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导演里,都说郑君里是最善于把中国传统戏曲、绘画和诗词艺术这些表现手法用到电影中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一点谢晋在《舞台姐妹》里也做到了部分。“中国电影界,有3个导演的影片既关注民众,又具有士大夫式的传统诗情画意:蔡楚生、郑君里、谢晋。他们是三辈人,但在精神上有传承。好莱坞的架构经过了他们中国文人式的咀嚼之后,就变成了中国的东西。”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看见谢晋拿着剧本来家里找父亲讨论的样子,“他一点不拘谨,叫我父亲‘君里’,对我母亲黄晨也直呼其名。谢晋比父亲晚一辈,但父亲很尊重他的意见,每次要拍新片了,就叫人去把谢晋请到家里来参加创作会,经常是在一大片中年人里面,就坐了谢晋一个小年轻。父亲拍《聂耳》和《枯木逢春》两部片子的原始讨论记录中,都找得到谢晋的意见。”“文革”之后,郑君里不在了,谢晋还常去看望他的夫人黄晨,过年过节也打电话问候。上世纪80年代末,谢晋听说在电视台工作的郑大里不想去美国读书,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未能出国留学的遗憾,他特意打电话到郑家,说:大里啊,你一定要去读书,有困难的话,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他的关心不是知冷知热的那种,而是关心工作和学习。”在郑大里的童年记忆里面,谢晋瘦瘦高高的,长得很帅,“他常来家找我父亲,两个人说戏的时候神情很相似,很激动,仿佛在吵架。他年轻时也是个活泼的人,会逗孩子,喜欢从背后给我变出糖果来。每次他来家我都高兴,因为总有吃的”。 在石川看来,有4个老电影人影响谢晋最多,第一个就是黄佐临。“1958年黄佐临拍《三毛学生意》,他对谢晋说,就是把这部戏拿到法国去,也是最好的喜剧。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曾把苏联专家请去看滑稽戏,专家大为惊奇,说为什么还要请我来讲课,这就是最好的表演。大师和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让谢晋更加意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后来他拍《大李、小李和老李》,就直接受了老师黄佐临的影响。” 张俊祥、焦菊隐和石挥,是谢晋受益终身的另外3个老师。张俊祥是老师,又是领导,年轻谢晋能够有那么多拍片机会,和张俊祥不无关系。焦菊隐重罚过谢晋,谢晋到老了还记得: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焦菊隐带同学排演《哈姆雷特》,他在前面说戏,谢晋在幕后偷偷说话。他从小嗓门就大,干扰了排戏,这下把焦菊隐惹火了,大喝:谁在说话,站出来!谢晋认了,被焦菊隐罚去站城墙,不叫不许回来。这种排戏的认真在谢晋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当导演后,也以排戏严格闻名。著名演员秦怡对记者说,“当年拍《女篮5号》时,谢晋导演把剧组全部人员集中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里体验生活两个月,所有人都像运动员一样生活。进组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拍戏前要变成一个团队。然后我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跑步,请专业教练训练篮球,每个演员都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既有深刻的体验,又有恰当的体现,这是秦怡和谢晋这唯一一次合作后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前,石挥的片酬在老电影人里面是最高的一个,他在《姐姐妹妹站起来》里面不过演了几个镜头的人贩子,片酬就500块大洋。谢晋和石挥的交往,应该从1953年他进《鸡毛信》剧组才开始,石挥是导演,他是副导演,两人性格相投,表面都喜欢嘻嘻哈哈、满不在乎。1955年自由组成创作集体,石挥就选了和谢晋一起组‘五花组’,每天讨论剧本,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直到1957年石挥自杀。谢晋强调演员体验生活,要求把剧中人物关系带到生活中,也是从石挥身上受到影响。谢导一直怀念石挥,有次跟我说起他为什么喜欢姜文,因为他在姜文身上看到了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石挥,另一个是于是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