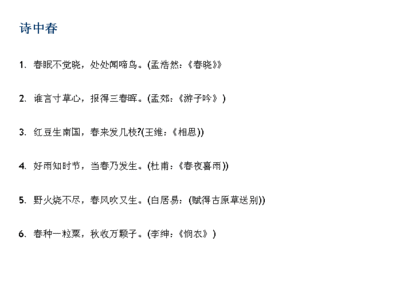吴梦

赵川:作家及戏剧工作者,并为海内外媒体撰写艺术评论等。 Biljana Ciric:独立策展人。 为什么是“亚洲” 吴梦:在我的印象里,以往大陆人都很少用“亚洲”艺术这个概念来归纳自己,似乎中国就是亚洲。从双年展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运用这个概念? 赵川:我觉得是从1996年光州三年展开始,韩国人一出来就是谈亚洲,这里有韩国人的文化特点,比较强调他们的位置,开始形成一个话题。之后日本人开始做福冈三年展,澳洲做亚太三年展。到了近几年,新加坡也开始做双年展。对于新加坡来说,做这样的国际展览,只讲新加坡的东西是不够的,所以也会加到这个大主题中。以往中国一直不参与亚洲这个话题的,现在也不是有心要来讲,而是说大家联合在一起操作起来比较有意思。ShContemporary是拿亚洲话题来主导的,但它基本也是西方人主导操作这个话题,中国人本身不太关心“亚洲”。 吴梦:在中国,虽然也零零星星有展览在谈论亚洲主题,但是规模大一些,有些影响的还是ShContemporary,但是这个“亚洲”概念还是从西方人的艺术市场的角度来概括的,这样似乎比较好概括,也比较好操作。 Biljana Ciric:我始终觉得把艺术归纳为一个区域,是在害它。因为你马上给它打上了另一个商标。纽约也有一个亚洲博览会,这个纽约的博览会打这个“亚洲”牌是有目的性,但对艺术来讲未必是个好东西。 吴梦:那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9个城市这样联动起来。当然首先是好操作,西方的评论家、策展人、藏家、各种关心亚洲艺术的业内人士只要花十多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展览全部看遍,虽然也挺辛苦的。这之外呢? 赵川:双年展是在全球化下的话语方式下,也是整个艺术系统的一部分。这是西方人设立的一个游戏,游戏就有特定的玩法,现在你加入到游戏里面去,必定涉及到一个权力问题,话语权利系统,所以韩国人做双年展一跑出来就要讲亚洲,其实也是一种策略,一种游戏的策略,但是这样的策略有多少价值,是否能带动亚洲的艺术,或者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 亚洲双年展印象 吴梦:以往那些亚洲双年展在你们的心目中都是什么印象? 赵川:我从2000年回国,就开始关注双年展,特别是上海双年展,好像是件大事。但几年下来,我会觉得最初有的问题,在后面的历届里都没有解决。另外,官方的展览就是有一些很明确的要求,像明信片般干净漂亮的。在我来看,双年展这种策略是浮在上面的,是一种我们突然拿进来的方式。我们从90年代中期开始做,现在也号称有二十几万的观众参与其中,但整个艺术是被一小撮人在操纵的,它跟城市文化是一种很表面很肤浅的关系,它也只对行业里面的人有意义,对其他人来说只是开了一扇窗而已。 Biljana Ciric:今年对台北双年展比较期待。去年的新加坡双年展评价不错,南条史生试图在主题、作品和场地之间试图发生关系。在新加坡的寺庙里,在礼拜堂作礼拜的时候,在马路上都能看到艺术作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这是有意思的实验。今年,我听说他们也加了一个博览会在双年展里面,种双年展搭配博览会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新的模式。 吴梦:你们刚才都谈到双年展和它所在城市的关系,这其实很重要。离开了这层意思,双年展似乎就和任何国际性展览没有太大区别。 Biljana Ciric:新加坡是个很多不同信仰的人混居的地方,所以这些点就会构成问题。我比较感兴趣的双年展是有一个正常的展览框架,在这个框架上去发展双年展的模式。做一个大的群展是比较容易,就是一个国际展,但是这个国际展在这个本土里面是否能扎根很重要。不然展览在哪里展出关系不大。 赵川:上一届台北双年展就做的很小。台北美术馆有好几层,但双年展只用其中的一层,像主题展那样,我就觉得很好。而悉尼双年展其实还不太像一般东南亚的双年展,它还是西方人的文化。 世界艺术的新中心 吴梦:亚洲9月9城艺术联动是否会展开世界艺术新格局? Biljana Ciric:我认为好的艺术,好的艺术家,无论他是哪里人,应该都在一个平台上,无论放到哪里,都是重要的。现在世界艺术的中心是纽约和柏林,这些亚洲双年展的集结,似乎在试图找到一个多中心的局面,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通过一个双年展就能办到的,是整个城市、社会大背景的融合才可以。但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或者说上海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不太在乎,似乎觉得自己是够的,无所谓交流。这些人来三天走了,过两年再来,因为好玩。过十年他们不一定再来了,那最后留下来的东西是属于这个城市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赵川:双年展的这种模式,它其实不是在一个正常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大家说好,我们两年弄一次,现在又是9个城市的联动,里面就有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你参加这个联动,是希望被看到,问题是说大家都希望被看到,那你拿什么东西去给人家看。我刚才的感觉是一下子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一下子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别人看。里面始终有的一个问题是:你拿出来给人家看的和人家希望看到的是种什么关系?其实中国始终还是在一个拿出来给你看的过程中,而没有去看别人。为什么?就像刚才比利安娜说的,在澳洲、美国、欧洲也好,尤其是在法国这种地方,可以允许一部写中国的小说得他们的一个文学大奖,反过来,这在中国是不可以想象。 吴梦:我们自己就太大了,不看外面的东西,难道艺术也是这样? 赵川:我们现在在经历的这些当代、现代艺术都是在西方的脉络中慢慢成长起来,它最大的受众,普遍社会能够宽容这个东西的是中产阶层。我刚才在想,为什么像这些双年展在悉尼就不觉得那么奇怪,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也有人觉得满好玩的。那这个艺术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掐头去尾,核心还是中产阶级的艺术。另外,在西方从前一个世纪末到上一个世纪初的整个中产阶级的形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中国缺少这块东西,所以当代艺术对这个地方还是蛮奢侈的,整个社会环境大多数人还是不接受自由意志这件事。另外,我觉得比利安娜说的对,我们当下的艺术和外面的连接是有问题的,连接这个工作也不是双年展能够完成的。要完成这个工作,就是要靠你我,靠这些艺术家,艺术怎么在这个地方生成,而不是变成飞来飞去的东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