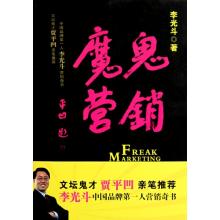170万是伦敦市长在最近演讲时反复提到的数字,伦敦市长说:“这是我们将很难超越北京的原因。”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是4.7万人,雅典是7万人,而前两届奥运会预计观赛人数都是500万人次,北京达到了700万人次。“城市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项目共有140万人,这是中国的首创。”北京市团委书记、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刘剑对本刊记者说。
◎葛维樱 王墨馥
9万余人的90分钟疏散 8月8日15点,2080名“鸟巢”志愿者和3500名奥林匹克公园志愿者全部集结完毕。8月9日凌晨2点,最后一辆志愿者班车离开“鸟巢”。这还不算在周边站点上服务的2100名城市志愿者。尽管媒体都愿意报道志愿者是如何背对着璀璨的礼花和华美的表演,可对于志愿者们来说,每个人都是繁忙和踏实的。“一条警戒线什么时候抬起来什么时候放下,都是心里有数的。”这才是保障开幕式的最根本要求。因为“鸟巢”附近标识众多,每个标识下都站着志愿者,用扩音器不断以中英文讲解交通路线。尽管一个观众从出口到乘车离开不到5分钟,但是在9万人的基数上,这成了考验奥运志愿者的第一道难题。 开幕之前的人流涌动时间较长,此后在90分钟内顺利撤出是早已经演练好的情景。“从地铁10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枢纽开始,人流就需要引导,我们不断重复请持票观众从正确的入口进入。即使人潮涌动,我们的声音也必须停留在人群上方。”每10米就有一个志愿者,形成人墙,提示观众走向正确方向。但是经过多次的演练和总结,两条平行线已经不能满足奥林匹克公园宽阔的路面和流向难以控制的人群。有3路志愿者形成一个“川”字,中间一路志愿者随着两侧人流量的变化,不断转身照顾另一侧的观众。这是开幕式结束后迅速疏散的方法之一,翻转人墙。 志愿者杨萍说,“两边上不仅浪费人力,还缩小了观众行走空间,速度也不行”。“鸟巢”共有11个出口,9万人前往公共区出口、公交车站和地铁,基本上各占1/3比例。无论是公交车站还是地铁站附近都有不同阵形的志愿者队伍,“雁行阵”是个三角形,从外向内输送,而每5米一人的“长城式志愿者分布”,就像长城城墙上凸起的垛口,每隔一小段一个人,均匀分布在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很多老年观众走特殊通道的时候都很吃惊,也有残疾人在大家的注视下被志愿者们接力护送,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从不自然变成了享受,我心里特别舒服。”杨萍说。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都对这些“决心给全世界留下好印象”的“蓝衣服”做出了“高兴、礼貌、友好”的评价。“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某位体育明星,而是甘愿为奥运会和北京服务。维持交通的志愿者比场馆内的更加激动,因为能接触到更多来北京的人。”大卫·布莱特是悉尼奥运会志愿者部负责人,现在他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部的顾问,他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刘剑的标准倒比盛赞更务实,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目标是三个层面,让直接服务的国际奥委会、国外媒体,赛事中的运动员,还有来赛场观看的观众满意”。这些看起来宽泛的评价体系,实际上是整个奥运会顺畅进行的保证。 赛会志愿者的申请人数达到1125799人,为什么最后确定的是10万人?刘剑解释说,“10万人不是一个空想的数字,而是根据61个业务领域和2940个岗位定出来的。”事实上是在校大学生占76%,35岁以下占91%。这些活跃在奥运会核心区的年轻人是服务质量的最重要的保证。奥运会赛会志愿者在往届都分布在各年龄层,并且有意识地强调各行各业参与,不过中国的语言环境决定了必须以“英语够用”作为赛会志愿者的素质底线。北京需要国际化的形象来沟通和服务。大学生并不能保证英文完全过关,可至少在沟通上是“够用的”。“大学离场馆很近。北京奥组委一直都意识到使用年轻的志愿者是有风险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如何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从招募到培训,都对这些学生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大卫·布莱特对我们说。除了这些必要的核心服务人员,北京奥运会的另一个目标是,把赛场外的服务做得和赛场内一样好,这是往届没有的。40万名城市志愿者,保障北京市信息咨询、语言翻译和应急服务,更广大的100万名社会志愿者,分布在社区治安、交通站点等一个个最细小的分支上。这三层服务网络,几乎囊括了从一位外国观众走下飞机一直到回国上飞机前的每时每刻。城市志愿者有550个站点,3000个岗位,社会志愿者有3万个岗位,还有20万名拉拉队志愿者负责169场次的助威。这160万人分布更加广泛。“每一辆公交车,每一节地铁车厢,都有我们的社会志愿者。这都是配合‘平安奥运’的措施。”城市志愿者则是为了让“整个北京的城市运转不因为客人数量受影响,而是更加通畅方便”。这种必要性体现在,奥运会期间,秀水街等热闹的地点一天的客流量达到了几十万人。 刘剑说:“过去我们说起志愿者,偏重于体力劳动,现在更多的城市和社会志愿者偏重于信息服务。”北京所谓的信息服务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容量。“往届奥运会你问路会得到一个路线图,而现在北京的志愿者有的亲自把你送到目的地去。”在有关奥运志愿者的规则中,并没有强制要如何对待问路的人,但每天的报纸上都有关于志愿者重复性工作或者耐心细致到让人感动的地步。“中国把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伸展到赛场之外,延伸到北京全市。”《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悉尼的志愿者如果不是特别忙就会离开了,而北京的志愿者即使没事情做也会保持快乐和热情,绝对不会离开。”每个人都希望做得更多更好,大卫·布莱特觉得这简直让人吃惊。 “你应该记得‘申奥’时我们的民众支持率,97%。在整个奥运会申办过程中,这个支持率是最让国际奥委会惊讶的数字。国际奥委会专门派公司来北京调查,结果数字比我们报的还高。”民众支持率是当年‘申奥’的最大法宝之一,时过8年,“奥运志愿者成了民众情感释放的平台”。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对本刊记者说起最常见的志愿者大爷大妈,“哪怕没事也要盯着那个岗”。此外,更让外界赞许的是志愿者的“快乐”印象。“感受到干着又苦又累的活,什么感觉也得不到,只是在脑海中存在一个虚妄的概念。”张巨明说,现在对于奥运志愿者的更多引导是“奉献中你自己收获了什么?”“这毕竟是一个临时性的、繁重的、高要求的事情,仅凭热情根本无法适应。” 谁来管理志愿者 “这看起来是一个太庞大的系统工程。”张巨明告诉本刊记者,志愿者部作为奥组委的部门之一,实际上是一个综合部门,志愿者的分布涉及所有领域、部门、空间,“说到底是为了满足奥运会整个人力资源的需求”。赛会志愿者是奥运会最受关注、责任最大的核心群体,完全服务于竞赛,按照场馆进行组织管理。“场馆化管理是国际奥委会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各竞赛单项组织是落在场馆的。”每个场馆有专门的场馆主任,志愿者由他来管理使用,而同时又有一个志愿者经理,总体负责志愿者的调配。志愿者经理由志愿者部派出,及时沟通和协调场馆和志愿者部的工作。 “体制的优势在志愿者工作中体现明显。”志愿者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工作协调小组,是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奥组委三方力量共同架构的。“这三个方面统筹各方资源。国外是按照志愿者部或人力资源部门,但不会有协调小组。”专门负责高校的政府机关很容易把学生们组织好,主力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热情本来就特别高,加上身体好、整体素质高、外语够用,高校又是最便利的培训管理场所。而城市和社会志愿者,则由各级团组织来完成招募、选拔和管理。志愿者工作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同时,也利用了现有体制优势。“这是一种身份明确。”张巨明用中国人最熟悉的街头形象举例。看似简单的举动一旦正名,使“志愿者”这个称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鲜明起来。一个原来大街上戴红箍巡逻的老大妈现在穿上制服,凝聚在更加崇高更受尊重的情感之下——奥运会。“国外70%以上的志愿者是老年人,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奥运会对他们是一种身份的明确和肯定。”刘剑说,中国自古从不缺乏志愿的理念,“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个社会没有这些根基,仅靠一个奥运会动员全民族的热情也是很难的”。 尽管培训和选拔都是有组织的,但让志愿者感受到的最大动力不是来自组织号召,是奥运精神本身。在两年时间的选拔和培训阶段,申请人并非由统一的标准和严格的考试选拔,而是根据时间、专业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人才。赛会志愿者根据各竞赛项目要求专业化,因此志愿者部培训志愿者经理和骨干,场馆负责岗位培训,专业部门负责专业培训。城市志愿者,比如一个医生的年龄、经历、专业、家庭住址都被考虑在内。城市志愿者的培训侧重信息咨询、语言和应急,社会志愿者则为平安做贡献,每个志愿者都承担“平安奥运”的职责。志愿者部培训站点负责人,分管站点的负责人比如街道办主任,街道办主任再培训志愿者。 “我们派志愿者参加多哈亚运会等多个世界级比赛的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水准已经有了严格的标准,“在某情况下,以何种路线多长时间内到达都是有标准的,姚明摔倒后谁拿多大的一块毛巾上去擦地都是有数的”。这样的细节太多了,多到志愿者和观众都已经习惯了完美和先进性。志愿者培训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已经涵盖了所能想象的方方面面,这些细节的目标,使得“志愿者工作对于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观众和官员对奥运会的印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卫·布莱特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有的志愿者除了赛时餐饮和交通,其他一切费用自理。”这个务实的规定对人们参与的火爆程度毫无影响。包括近来反映的餐饮不理想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沟通的插曲,没有减弱志愿者的工作热情。志愿者们传颂的是,博尔特戴着志愿者送的彩色手环“微笑圈”冲过了100米和200米。“中国从参与奥运会到拿金牌,到成了金牌大户,到举办奥运会,这个过程激发了几乎所有人的情感。”志愿者是最明显表现——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又把中国人的情感向更深的层次引领了一步。 志愿者国度
“悉尼奥运会期间没有一个机会肯定志愿者的服务是否成功,直到闭幕时才得到了萨马兰奇肯定,才算是梦想成真。”大卫·布莱特说。北京志愿者从开幕式就开始不断得到激励和反馈。这次罗格在奥运会开幕致词上就说“没有他们,这一切将不可能实现”,联合国也第一次颁发“联合国卓越志愿服务组织奖”给北京志愿者协会。张巨明说这其中的理念变化值得一提,“过去讲雷锋,一个人好心眼,全是为别人,自己没有收获;现在自己的成长是重要的内在动力,哪怕一个很小的岗位,给他的舞台都很宽阔”。 志愿者组织内的自我评价和沟通也是“饱满热情”的一个保证。张巨明管着奥运志愿者心理热线,“我们还有层层反馈渠道,除了服务对象,志愿者自己可以评价,可以向管他的小经理向上反映”。这也是地震时的无组织的志愿者反映出的一大问题,信息渠道不畅。这就是志愿者组织的作用,“一个人想参加志愿服务,去哪里?服务谁?而需要服务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作为中间组织,我们完成志愿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规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在志愿者部的工作中,还有一项是梳理出了80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在网上公布,提供一个平台,市民可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这个组织就是国际社会说的第三组织,再强大的政府再发达的市场,还是有覆盖不了的地方,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志愿服务作用太大了。” 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会流传下来,还有百万奥运志愿者队伍,和初步的志愿组织体系的统计。在奥组委志愿者部消失后,“一个人怎么找到自己家附近,又配合休息时间的志愿服务来做?”而且志愿者的时间、体力、金钱还不是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技能和情感的奉献要求也在奥运志愿者中体现出来,特别是情感的奉献,也成为奥运志愿者的重要特点。张巨明说,以前的青年集体活动都是一些大活动,“组织化痕迹大,活动一完人也都散了”。“什么组织能够统领?怎么明确义务和权利?虽然国家还没有立法,但各地方已经在探索,把个人发自内心服务他人的愿望,和社会组织、政府引导结合起来。”2007年北京市人大颁布了《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是奥运志愿者工作的一个成果。“通过实施《条例》,我们将加强各级志愿者协会建设,逐步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吸引、动员更加广泛的人员参加志愿服务工作,推动北京志愿服务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的轨道,切实保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北京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工作的目标。”刘剑告诉本刊记者。 大地震和奥运会这两件大事中,除了体制制度的规范初步确立,志愿者的认同和普及也开始了。“咱们国家社会各方对于志愿服务的认识、理解还在发展阶段,还有过于超前或者接不了轨的地方。”但对于奥运结束后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信心显露无遗:“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志愿者内心的热情和快乐在更广大的范围产生了作用:“中国的志愿者开始将志愿服务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在世界将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