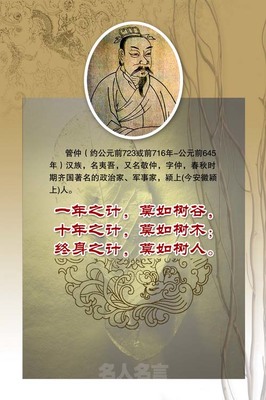“飘忽不定可能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家,我们今天也就找不到那么多的无家可归的感觉了。”
撰稿·乌力斯
一本冒犯“北大”的书 “我觉得北大的评论家太敏感了。”阎连科的眼睛血红,脸色蜡黄,看上去很疲倦。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便引发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弹,网络上先后出现北大学生《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等言辞激烈的帖子;报刊上也出现了几位北大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他们认为,阎连科借小说“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这一切,与阎连科《风雅颂》里提到“‘清燕大学’是皇城里最好的文科大学”有关。这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副教授杨科提着耗时5年完成的《风雅之颂》回到家时,迎接他的竟然是妻子与副校长通奸的场面。不久,因抗击沙尘暴给学校带来麻烦的杨科被清燕大学的领导们举手表决送到了学校附属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长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病人们反响无比强烈,掌声雷动。杨科逃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前寺村,他记忆中的桃源已发生巨变,他当年的初恋情人玲珍已经成为县城天堂街的地下妓院老板,那些坐台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学生、最热忱的知己。等他再回到清燕大学时,他的《风雅之颂》成了妻子赵茹萍的《家园之诗》,副校长已经成为校长,公然与妻子同居;老家的初恋情人因艾滋病身亡,留下一个长得与玲珍一样的女儿,在她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杨科因为妒忌掐死了新郎,领着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批专家、教授逃向“诗经古城”……但最后等待他们的是虚无与幻灭。 面对文学以外的猛烈批评,阎连科很意外。“之前,我的一个中篇小说《两程故里》故事背景发生在宋朝程颐、程颢的故乡,当地的村民说我不尊重他们的祖先,他们要到我老家的村庄打架,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村庄做好了迎击准备此事才作罢。这件事情发生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但是北大师生的反应那么剧烈,认为小说是诋毁北大,这样荒诞的反应超出我的想象。” 其实,如此激烈的反应并非没有预兆。《风雅颂》在今年第2期的《西部·华语文学》发表后,阎连科从各种渠道听到一些消息,“有人说这个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挖我们教育的祖坟”,这些话已经在圈内流传开来。这让《风雅颂》的出版异常艰难。“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以题材敏感为由给退了;接着作家出版社要出,提出20条意见,让我修改结尾,但后来给领导看又说小说太灰暗、没有正面人物;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出版”。 书出版后不久,《文学报》的批评专题也出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批评说:“作家对主人公置身的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入理解,夸张变形变成荒诞不经且龌龊不堪,致使对‘现代人精神家园失落’这一命题的探讨本身丧失家园基础,而对‘风雅颂’、‘清燕大学’等文化符号或浮泛牵强或扭曲粗暴的借用更有哗众取宠之嫌。” 另一位文学博士李云雷则尖锐批评说,“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但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得很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让人看了觉得有些可笑。小说还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不少人包括我对北大也很不满,但像他这样无中生有地搞‘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这应该是犯了写作的大忌,没有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反而将自己的臆想当作了批评的对象。” 阎连科并不同意邵燕君、李云雷等人的批评。“你可以从文本上来分析,批判《风雅颂》写得一点都不好,很粗俗,但作为一个批评家用真实和不真实来判断小说,说我是诋毁北大,我觉得是他们的艺术眼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他们的文学修养不如我想象的值得尊敬。阎连科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小说我一直说它是荒诞的。” 同样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陈晓明认为,阎连科是中国少有的有理想、有责任的作家之一,尽管阎连科的作品很多都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极端性批判,但是这些批判也确实击中了社会的一些软肋。对阎连科新作《风雅颂》的争议,陈晓明不以为然。他说小说只是作家的一个“白日梦”,所谓影射北大、清华,只是作家有意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或“噱头”,但作家本身对清华、北大并无歹意,只是对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一种广义性的评判,何况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讲,去追究名字的真实性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则表示:“大学精神的沦落是不争的事实,以为大学教授们还是过去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恐怕只是部分学者、教授们的一厢情愿。当然,杨科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并不代表中国教授的整体情况,据此认为阎连科在妖魔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言过其实。” 个人的精神自传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阎连科一再提及《风雅颂》是他个人的精神自传。“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精神内核和人生体验是我自己的。” 和莫言、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田湖镇。他是家里出生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阎连科的父母都是两眼不识字的农民。 该读高中时,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阎连科读书了,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在新乡水泥厂打工的叔叔,把18岁的他带去做工。那个时候,当泥瓦匠的阎连科一天要推许多车沙土、石料,还要学会搅拌、砌墙盖瓦。 在这段期间,天天从事繁重劳动的阎连科在文学刊物上看到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因为这篇小说,张抗抗从北大荒农场被调到了哈尔滨,从下乡知识青年变成了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这让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我白天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神奇。”阎连科回忆说,以往一到晚上八点钟,母亲就熄了灯的,怕费油。那时候,家里对他最大的支持,就是让他点灯写作到深夜。 1987年底,为逃离农村,改变命运,阎连科报名参军,他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到了新兵连,连长见他字写得不错,就让他去编黑板报宣传。部队教导员张英培是个文学青年,爱写古体诗,看到阎连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把他叫去聊天,看了他写的小说后,把阎连科调到营里当通讯员。 1988年,阎连科的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发表,他成了团里闻名遐迩的“秀才”。这让阎连科觉得,写作同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如果能够当上干部,他就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留在部队了。不巧的是,当阎连科符合提干条件的时候,正逢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提干的名额全部让给了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等到下一轮的时候,上级下发文件说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得通过考军事院校提干。“普通士兵考军校有个限制,年龄不能超过20岁。”当时阎连科已经24岁了。正当他万念俱灰准备复员回农村种地时,已经上了火车的阎连科被团长叫下车厢,因为他此前写的一个独幕剧在全军战士文艺汇演比赛中拿了第一名,上级给武汉军区分了20多个提干指标,阎连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
阎连科提干以后,上调到了师部当了图书管理员。心满意足的小干部,找了城里户口的随军媳妇,阎连科以为自己的日子可以安稳了。“我当时通过文学改变了命运,但究竟当一个拿笔的作家还是当一个带枪的高级军官,我还是有些摇摆不定。”而现实让阎连科彻底放弃了将军的梦想,一心一意走文学之路。1989年,凭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阎连科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看到同批学员中的莫言红得发紫,更加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这段时间阎连科逐渐受到文坛的瞩目。 2004年,长篇小说《受活》把阎连科顶到了风口浪尖,一方面小说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另一方面也让他备受争议。他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一次专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马上从军队转业。“一个领导看了《受活》说,如果将来还要打右派的话,阎连科肯定是一个。” 此前3年里,阎连科曾反复打转业报告,但上级以“爱惜人才”为名一直挽留,就是不批准他调离。如今一个电话就调到北京市作协,离开呆了这么多年的部队,“这让我有巨大的荒诞感。就像卡夫卡小说里一样,一夜之间也许我能够成为甲虫。”阎连科说。 无家可归的人 阎连科写《风雅颂》的念头产生于7年前。当时回老家的阎连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件事:河南一个高校的女副教授,因为学校名额限制,原本符合条件的她连续几年没有评上正教授。到了第三年,她的申报材料又送上去了,听说和自己专业相近的校长夫人也要参评的时候,因担心名额被抢走,她闯进校长的办公室,当众给校长跪下了,祈求校长给自己机会。 这个故事的结尾阎连科并不知晓。但几年里,这个事情一直在他脑海里盘绕,后来有一天阎连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没开多久,有几位教授就在会场上低头查看信封里的车马费。会议结束次日,阎连科又听说一位在会场上数钱的教授当夜去找“小姐”时,一边抚摸着小姐,又一边非常认真地教育人家从良读书。两个故事重叠以后,成为《风雅颂》的最初来源。 “河南的那个下跪的副教授让我想到我自己,我在那个环境里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知识分子软弱无奈的时候,他最大的力量就是下跪、求饶、求人。这些异化的经历和情节,确实来自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和所有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一样,从底层慢慢往上爬的阎连科知道权力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是多么重要。“今天我对我们老家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毕恭毕敬的,因为我的亲人还在老家生活,虽然我已经50岁了,职务也很高,但见到他们还是很恭敬的。” 身为知名的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侄男甥女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在亲人期盼的眼光面前,他经常觉得自己的无能为力。“我常常觉得我的人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有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在北京居住了20年,阎连科经常在梦里回到老家。“但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源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父母也不在了。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 都市和乡村的彷徨一直困扰着阎连科。作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阎连科却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这是一个权力中心,是文化的名利场中心,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你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你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愁无乡,有家无归。《风雅颂》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阎连科说,“这是所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的一个困境。我儿子这一代已经非常融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家就是北京,祖籍河南。但对我们来说,北京是人生的驿站,把家给丢掉了。但是,飘忽不定可能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家,我们今天也就找不到那么多的无家可归的感觉了。” 五十知天命。阎连科却盼望能够找到自己年轻时的激情和勇敢。他希望通过写《风雅颂》,恢复到写《受活》那样的状态和立场。他说:“对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最好的年龄可能只有15年,也就写两三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已经没有时间再供我去摇摆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像鲁迅那样,做个直面现实绝不妥协的人。对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还怕什么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