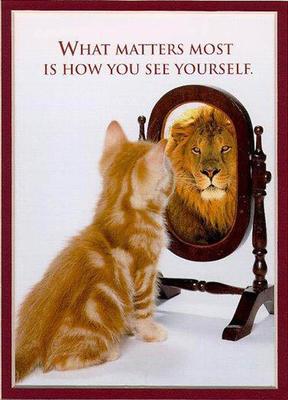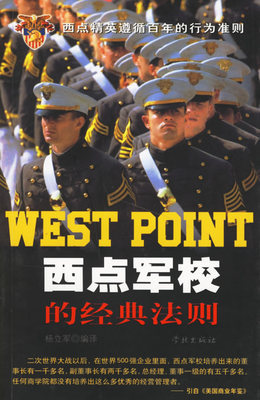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温;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重温。
撰稿/王晓渔
正在睡觉,收到朋友的短信:索尔仁尼琴去世。就像听到柏杨去世的消息,我有些意外,但没有太多悲痛,两人都得享天年,年近90而去,按照中国的说法,属于“喜丧”。更重要的是。他们死得其时。如果在20年前去世,索尔仁尼琴将无法看到“癌病房”的倒塌;如果在10年前去世,他又会对摧毁“癌病房”的休克疗法含恨终生。1990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授予《古拉格群岛》的国家奖;1998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的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奖;2007年,他欣然接受了普京颁发的文化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国家奖。
按照惯例,喜爱的作家去世,我总会把他的著作找出重读,以这种方式进行“告别”。“告别”是一种追思,不等于告别逝者的写作和思想。在中国,不乏对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艺术价值,属于“伤痕文学”;另一种认为他的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属于“冷战思维”。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恰恰是在以“见证写作”对抗“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对抗“冷战思维”。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的国家,“见证写作”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之为作家的承担,也是人之为人的承担。维护人性的底线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与冷战没有必然关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个体如何失去自由的过程,也呈现了高压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内伤,与其说他讨论的是政治,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性,人性之恶如何被政治之恶唤起。 不久前,我曾把索尔仁尼琴自传《牛犊顶橡树》找出,重温他笔下的“地下工作者”生活。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地下工作者”指那些拒绝按照既定程序写作的作家,他最初曾经坚信有几十个“秘密写作的兄弟”分散在各地,后来发现自己低估了契卡的能力,敬业的契卡可以将天才消灭于无形之中。索尔仁尼琴不是把地上和地下对立或者隔绝起来,而是写出了两者相互遭遇的情形,写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暧昧地带,这正是冷战思维无法触及的区域。他如此评价《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同时,他又指出编辑们除了迎合总编辑,没有其他目的,“有朝一日文学史将惊奇地研究和了解到苏联的这家热爱自由的、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杂志编辑部,在痛骂个人迷信的这些年代里,在自己的内部仍然奉行着个人迷信的原则。”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制造的,这是“癌病房”的传染病,但他也没有为刊发自己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总编辑作无罪辩护,而是指出:“特瓦尔多夫斯基缺乏朴素精神和幽默感来发现这些并给予制止。”这种贴身观察不太可能出自敌人,敌人很难理解敌人,只有可能出自地下工作者,这名“地下工作者”不是来自敌营,而是来自自己的阵营。 为索尔仁尼琴辩护,并不等于拒绝对他进行批评。我承认索尔仁尼琴的艺术价值要弱于另外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我也不否认索尔仁尼琴具有一定的冷战思维。索尔仁尼琴的冷战思维不是表现为他站在敌对势力(美国)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祖国(苏联),而是他依然无法摆脱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又对西方缺乏足够的了解。30年前,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演讲,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可惜这种批判有些隔膜,远不如他对“癌病房”的批判准确,此时他不再从“地下工作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是把西方当成假想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批判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出了问题,而是充分说明要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有多么困难。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没有成为李敖,从一个英雄演变为“小丑”。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重温他的古拉格群岛、他的“癌病房”。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温,让它们在我们的内心慢慢坍塌;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重温,让它们不再重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