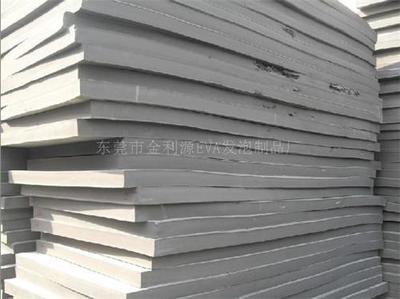福建土楼更像一座围城,作为“他者”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冲进去看一眼稀奇,而原住民拼了命要冲出去,与现代化的消费方式接上轨。
撰稿、摄影·沈嘉禄(主笔)
土楼的普遍价值体现在哪里 46座福建土楼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1个委员国专家们给出的理由是:“它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聚族而居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 是的,土楼以极富想象力的建筑形态,向世界显示了闽西南客家人的聚居方式,更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守衡的哲学思想和严谨的宗法制度体现在这种封闭的格局中。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客家人五次南下大迁徙的惨痛经历,不能不在每一根梁柱上烙下鲜明的印记,那就是在精神上的坚守和对外交流上的慎独。 土楼建造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唐朝,资料表明,唐朝陈元光开漳时建造的兵营可以被认作是最早的土楼,它不是为了防止外国入侵,而是为了提防南蛮之地的原住民。宋代,中原望族继续南迁福建等地,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财产和成员的性命,客家人开始修建如兵营般坚固的土楼。直至上世纪60年代,土楼才终止建造,因为建土楼浪费大量耕地。 目前,福建境内还有两万多座土楼星散在永定、南靖、平和、诏安、漳浦等地。除了典型的圆形和正方形,还有不常见的半圆形、长方形、椭圆形及多边形,正门一般以白粉画出一个方框,上面用楷书写着楼名,左右一副石刻对联,将楼名嵌在联中,寄寓了楼内人的操守和信念。在红尘翻滚的公路边,它们常常在空调大巴一掠而过时给外来者以无比的惊喜,而自己以阅尽人间沧桑的姿态保持肃穆。入选的46座土楼,应该是保存得最好的。不过记者以为“普遍价值”一说,很值得怀疑。 土楼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记者在土楼群落考察时看到,土楼里每间屋子都是紧密相联、相互依存的,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屋顶下生息,虽然分灶吃饭,但互通信息并不自觉地以对方为影像。土楼一般有四层楼,底层是厨房,并畜养牲口家禽,二楼存放粮食,三楼给小孩住,四楼才是家长居住的地方。大型土楼圈内有圈,多的甚至有四圈,但中央一般都设有祠堂,是大家议事、祭祖、裁决家族事务和举办红白喜事的场所。 土楼内自成循环系统,居民一两个月不出楼门,吃喝拉撒也不用愁。这种格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极端例证,当然也维系了一种长幼有序的秩序。一座土楼里的堂联为此作出基本评估:“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注重人伦”。但是进入新时期后,土楼里的人伦关系有所松动。一切也许从一口井开始,最初建造土楼时,土楼中心的空地上必定要由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用手杖往地上一指,大家便动手挖出一口井来。这是维系整个家族数百口人的生命之源,也是一个象征物。自从有了自来水后,水管接到家家户户,那口井就废弃了,心理上的井也形如止水。再则,祠堂早已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居民靠电视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靠电话与外界沟通。有一个新媳妇嫁入一座土楼,6年后在县城买菜时遇到一个同行妇女的帮助,一问才知道对方跟她同住一座土楼,而且是亲戚。 土楼最让人们称奇的是坚固性。土楼的外墙厚达1米多,以红壤土、瓦砾土、田岬泥加红糖、蛋清、糯米调和成三合土后层层夯实,中间插有密密的竹条,起到类似钢筋的牵拉作用。有一年地震,一座土楼的外墙被震开一道宽20厘米的裂缝,但后来的30年里,由于向心力的作用,土楼慢慢将裂缝弥合。这一神奇的案例给了客家人莫大的安慰。更多的时候,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土楼成功抵御了入侵者,乱民、强盗、倭寇以及他们的后代——侵华日军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土楼的门是木质的,但厚达20厘米,并包了铁皮。同样为了防御,土楼的窗子一般都很小,并开得很高,一二层是没有窗的。土楼是攻不破的特洛伊城。 风化中的土楼 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土楼开始非自然地风化了。在市场经济启动后,大部分土楼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既然作为景点,就要提供配套服务,比如挂个灯笼,摆个摊,开个店。这本无可厚非。只是为了做小本买卖,同姓亲戚发生了龃龉,姑嫂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转眼失和,陌路相见,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械斗,鲜血流进了供养几辈人的那口大井里。千百年来,维系着客家人和睦共聚的家族信念和制度,颤抖了。 记者曾在永定洪坑村旁边一座非开放的土楼考察,领记者进去并充当临时导游的一位农妇表示要收五元钱,记者答应了。但后面跟来的游客不知情,将钱交了横路里杀出来的一个妇女。她说这钱该由她收。于是在我们一拨人即将离开时,她们还在为谁该收这笔钱而相互争吵、辱骂。看得出,她们的积怨非一日之寒。
一座土楼一旦被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开发为景点后,里外粉饰了一下,挂了铜牌,就成了一个聚宝盆,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对象”,原居住者也转身为生意人,虽然他们的大多数依然纯朴如初。但外国的学者不愿意考察变形的样本,他们一头钻进了非开放的土楼,宁可领受那股刺鼻的臭味,踩着猪粪和烂菜皮在黑咕隆咚的回廊里穿行。记者考察时恰遇6个日本京都大学建筑系学生,在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土楼里测绘了6天,吃住在农民家里。而这座土楼至今还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里臭气熏天,蚊蝇抱团,还养着4头猪。 这样的生活条件,难免要遭到客家后人的抛弃。不少土楼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青年人冲出围城到外面捞世界去了,赚了钱就在土楼旁边盖起毫无特色的新楼房,装上铝合金门窗和空调,墙面贴上闪亮的瓷砖,过起城市人的生活。 还有不少土楼成了空城,野草萋萋,落英缤纷。祠堂内的神主牌位前,香炉的积灰越来越厚,也越来越冷。当年土楼盖瓦——当地叫“出水”——时放鞭炮的声响早已逝去,新婚夫妻打糍粑用的大石臼也落满了灰烬和鸡粪。 建于明代的环兴楼,曾被太平军烧掉了祠堂和几间屋子,幸遇暴雨大火才灭。今天环顾四周,依然满目焦痕。人去楼空,锅漏灶冷,窗户洞开,如瞽者深陷的眼眶,残存的楼板七零八落,恐怕风一吹就会掉下几块来。记者迟疑着走进去,意外地看到有一个老者佝偻着在书写红对联,并贴在每家每户的门框上。腥红的对联,炭黑的门窗,形成诡谲的反差。村里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退休教师,执意留守在这座楼里,赶也赶不走——他是疯子。 所以,“普遍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土楼并不是宜居空间,它不能提供现代人起码的卫生条件,个人的隐私也得不到保护,但原住民一旦脱离而去,空巢化便不可逆转,延续数百年的人文生态信息就会断裂,而这种信息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再从历史与哲学层面上考量,土楼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保守思维的产物,拔高它的文化含义很容易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不小误解。 成为遗产的土楼如何保护与开发,是一个机遇,更是一道难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