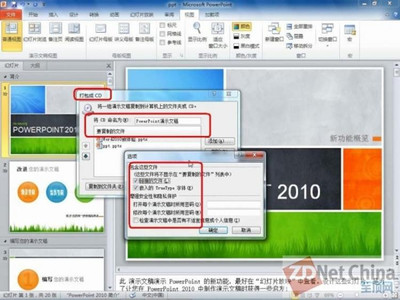令人失望的是,仅仅用420厂职工的感伤回忆为“二十四城”做一个大广告,就满足了贾樟柯拍摄严肃电影的愿望。

BY汪伟
《二十四城记》在戛纳取得了什么样的反响无关紧要。6月3日夜里,贾樟柯出现在上海影城,并且主持了《二十四城记》的慈善放映。制片方说,影片在法国引起了轰动。我无心去探究事实的真相。贾樟柯仅仅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电影,他之所以拍摄它,仅仅因为“现实如此严峻”,严肃电影仍然是我们的需要。我承认他的话异常直白,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中,我只看到一堆采访素材和几个表演片断,仅仅从剪辑的角度,仍可以说这是一部完整的电影。剪得的确漂亮,单薄零碎的材料甚至获得了逻辑的力量。但这力量属于剪辑师,不属于贾樟柯。 在过去的10年里,贾樟柯导演了5部故事长片,每一部电影都流露出他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个人解释。像他这个年纪的导演,没有谁像他那样执著于理解和表达80年代以来的历史,即或有同样的热情,也不具备他这样用隐喻来论政的雄心,以及与这雄心相匹配的影像才华。 除了大量采用移动镜头拍摄的《小武》,其他4部电影都充满了凝视般的长镜头。这些长镜头对准的空荡荡的空间里,每一个细节:从建筑到室内的布置,以及人的服装、动作和表情,即使是一个最小的道具,都携带着时间的信息,无限接近20年来的真实。它们具体而微地象征着时代。贾樟柯不怕麻烦地还原这些细节——其中许多已经让观者恍若隔世——不是出于怀旧的癖好,而是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这些长镜头有着一贯的清冷的色调,似乎在20年前,贾樟柯就不是亲历,而是旁观着他生活于其中的80年代。 自然主义的细节、长镜头和清冷的色调,后来成了贾樟柯电影重要的风格,但最终不过建造一座充满象征、隐喻和暗示的大厦的普通材料。贾氏的大厦既包含着时间,又包含着空间,和《世界》中那个虚构的世界相比,这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形形色色的男女栖身于大厦之中。20年来,这些男人和女人游走在中国社会的边缘,贾樟柯选中他们,让他们代表这20年来急速变化又为人遗忘的历史:这是大厦的主题,也是贾樟柯的历史观念:历史改变了人的命运,但人仅仅是旁观了这种改变。 《二十四城记》一如既往地谈论了大厦的主题。1958年,一家军工厂从东北迁往西南,40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随厂西迁,在成都郊区生产飞机发动机。50年后,工厂在经历裁员和改制之后迁往工业园区,房地产商买下了原来的厂址,计划开发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大型小区。有一些采访的素材最终作为成品放映出来,从中可以看到,贾樟柯关心的全都是可以纳入到大厦中去的那些人和事。《二十四城记》有机会让大厦更加完整,甚至深入到贾樟柯从来没有深入过的领域,把历史的视野从80年代推移到更远。但大厦意外地烂尾了。 寄身三线的军工企业420厂变身为“二十四城”(这个美丽而空洞的名称来自古诗对成都的描述),国家意志经历了从政治而商业的变迁,但这个过程决不仅是资本的凯旋。毕竟它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许多人的回忆都附着在空荡荡的厂房上面,这些厂房在挖掘机下发出空洞的回声,砖墙委地,记忆油然而生。即使痛苦难当,记忆也多少会夹杂些不复重来的甜蜜,而工厂一旦化作废墟,痛苦与甜蜜都难免埋进土里的命运。等到售价昂贵的“二十四城”里聚集起新的住户,从420厂动迁出去的职工将不知道散落何处,记忆即将消失。 历史改变了人的命运,最后又被人遗忘。这个吊诡的过程给了艺术家灵感,令人失望的是,仅仅用420厂职工的感伤回忆为“二十四城”做一个大广告,就满足了贾樟柯拍摄严肃电影的愿望。我不反对广告,只是没想到广告可以这么长、这么复杂。看上去它匠心独运,许久以后,我才警觉,它其实简单极了。复杂的是我对贾樟柯的想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