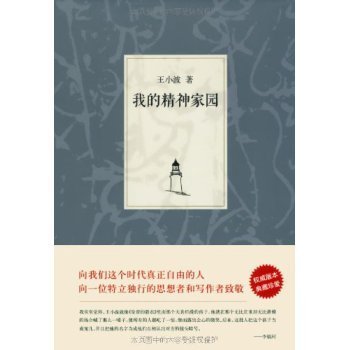不 到20年时间,全球化终于使新帝国的围墙搭建起来,以“新闻无疆界”、“人道无疆界”、“电影无疆界”这些帝国利器,围墙正在连接最后的缺口。
撰稿·边芹 旅法专栏作家
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能不能自许真实或历史真实?这是遍观今年戛纳的选片,在资本与政治结盟的现实面前,跃入人们脑海里的一个问题。 电影最早是为梦想而诞生的,一百年后,这门职业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逃开制造梦想的任务,日益钻进追逐真实的牛角尖。故事片纪录片化,或干脆直接拍纪录片,已成时髦。让很多两部大片之间找不到灵感、或江郎才尽的电影人,甚或一些政治投机者,纷纷“下海”。自戛纳几年前第一次接纳纪录片,并于2004年让美国人迈克·摩尔反伊战的纪录片得了“金棕榈”,纪录片风潮便一发不可收。今年在戛纳上映的各个单元的入围片,纪录片化的故事片的数目已经赶上传统故事片。也许是选片人的有意操控,现在只有很少的国度有送选传统故事片的运气,很多地方被挑来的几乎清一色是纪录片化的故事片或干脆是纪录片。让人看到戛纳电影节的一个明显意向:为导演安排了寻找真实的使命,并且只要他们完成这一使命:梦想由我们来做,你们去寻找你们的真实。 于是电影继分成商业与艺术两股道之后,艺术电影本身又分出了一支,并且自定义“历史记录者”。5月16日,贾樟柯就《二十四城记》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影评人波尔德采访时说:“当集体记忆消失的时候,个人记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想述说历史以留下证词……如今在中国,大家忘记了一切。谈历史是被禁止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讨论。而我,我要弄明白并且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段话我是转译自法文的,不排除波尔德的夸张。但这样的话却是法国人等待每一个被邀中国人为他们提供的证词!围绕《二十四城记》的法国评论,全是超出电影艺术的政治评判,总之贾的电影证明中国过去不好,现在更不好!我佩服国人自我批评的胸襟,但输出后若只为了取乐幸灾乐祸的人,我以为大可省省口舌。记得杜琪峰送选《黑社会》那一年,也接受波尔德的采访,谈话中就香港黑社会说了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凭此数字,西方人把香港想象成意大利那波里绰绰有余。当晚我与杜正好出席同一晚宴,便问他真这么可怕吗?他一笑置之:“嗨,他们就喜欢听这种话。” 4·19之后,我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寿司店用餐,有个女孩端上菜,我问她是不是大陆来的,她点头,站在桌边半晌不走,像是忽然抓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她说前一阵实在受不了了,只差一年就毕业了,但呆下去要发疯,行李都打好了,不要文凭也要争口气。这只是个课余在餐馆打工的女学生,似乎可以不承担任何东西,但那瘦弱的肩膀痴痴地要去分担一个民族的屈辱和尊严。每个人为他们只在瞬间可以把握的真实负责。
你不能阻止人为伟大的使命拍电影,尤其当伟大使命是为西方知识精英提供恒久不变的精神食粮。法国人有个“国病”,就是受不了幸福,尤其受不了他人的幸福。看到中国的高楼大厦,他们真有割肉之痛,一看到废墟就拍手,因为那才符合他们心理可以承受的中国。前不久经北京机场,在一处饮水机前喝水时,忽然听到法语,寻声望去,见几个法国人正朝饮水机走来,其中一男子边走边说:“不会是大粪水吧。”我原打算问他们要不要帮忙,听到这话,转身走人。饮水机是戴高乐机场都没有的服务,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酸臭话!别人穷、破、脏、乱的图景,对他们就像美餐一样不可或缺。于是就有一些中国友人心领神会,送来应有尽有的废墟。到后来连编故事都多余了,随便什么人从西方某个基金手里接一笔钱,找最穷最破的地方拍个纪录片,肯定被选来。证据由中国人自己提供,是最有说服力的。问题不在于画面真实与否,而在于它们的统一用途。 这恐怕是戛纳的一个明确走向,越来越政治化进而纪录片化,让一个艺术电影节行使“电影无疆界”组织的政治使命。不到20年时间,全球化终于使新帝国的围墙搭建起来,以“新闻无疆界”、“人道无疆界”、“电影无疆界”这些帝国利器,围墙正在连接最后的缺口。 一切都不在真实本身,而是为真实划界的权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