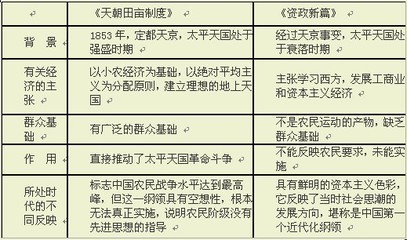知识人欣逢三千年乃至几十万年未有之变局,大约就像目击火星人入侵地球,在末日的绝望之中,隐隐约约又有一些绝处逢生的期待。
BY王晓渔
晚清时节,“天朝”遭遇“万国”,史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的考证,三千年是折中的说法,他考察了81位知识人的变局言论,有“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最夸张的甚至声称“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知识人欣逢三千年乃至几十万年未有之变局,大约就像目击火星人入侵地球,在末日的绝望之中,隐隐约约又有一些绝处逢生的期待。 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就呈现了士人在大变局里的绝望和期待,还有挣扎、思考、无奈和荒唐。从鸦片战争、“庚申之变”到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这些晚清民初之际的关节点,《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均有涉及。只有《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和《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两篇文章与全书主题有些出入,放在里面略显突兀。 据不完全统计,书中两次讲到裕谦剥取“白黑夷匪”人皮的光辉事迹,这名文官还曾剥取俘虏“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留作马缰,直逼“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气概。然而,如此主战甚至好战,裕谦非但没能收拾旧山河,反而以投水而告终。琦善的奏折更是充满科学浪漫主义,这位重臣认为老外以牛羊肉为食,一定要用大黄茶叶,否则会便秘而死,而大黄茶叶是中国特产,老外必然受制于我。这个观点在当时一度成为共识,林则徐先生也曾致力于断绝老外和大黄茶叶的关系。 相似的细节我曾在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里领略过,但是从写作时间来看,很难断定孰先孰后。两位学者同出陈旭麓先生门下,知识产权难解难分,也在情理之中。茅海建最近的研究日益学院化,作为他的忠实读者,我逐渐有力不从心之感,无力继续跟踪阅读。作为杨国强的非忠实读者,我对他的早期著作少有关注,对他的近作却颇感兴趣。 书中最长的文章是《晚清的清流与名士》,以庙堂之内的清流和庙堂之外的名士为主角,几乎就是一部光绪年间的士人简史。文章指出庙堂里的清流的前身是热爱清议的士大夫,习惯道德评判。但是清流毕竟身为人臣,常常在在君权和法度的冲突之间左右为难。文章讲述了一个太监引发的公案。按照惯例,太监只能由旁门出入,可是慈禧派遣的太监一定要从午门出入,被值日护军阻挡,太监回去后向慈禧告状,慈禧要求严惩护军,后来在清流的压力下从轻发落。对此,杨国强的评述不时地变化,他一方面说:“即使言路与政府常常相水火的年代,也能有政府对言路尊严的钦敬与亲近”,紧接着他又说:“就当日的总体而言,这种结局圆满的事其实并不常有。”这与其说是他的矛盾,不如说是历史自身呈现的内在冲突。杨国强还指出名士曾以清流为源头,所以身居江湖之远的名士常常仰望庙堂之高。尽管名士对体制的向往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体制还是不可能完全收编他们。报纸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当名士的报纸压过清流的奏折,天下士议的重心也从庙堂之内移到庙堂之外,名士时代取代清流时代,19世纪的士人倡言尊王攘夷,20世纪的士人倡言全变速变。当然,两者也有相似之处:清流喜作侃侃高论,名士爱发炎炎大言。最为吊诡的是,当“天朝”慢慢熟悉“万国”,它也走向了末日,士人变身为智识阶级,重新开始自己的绝望、期待、挣扎、思考、无奈和荒唐。 遥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谁也不能保证生逢其时,做得就比他们更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拒绝反思的理由。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杨国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4月出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