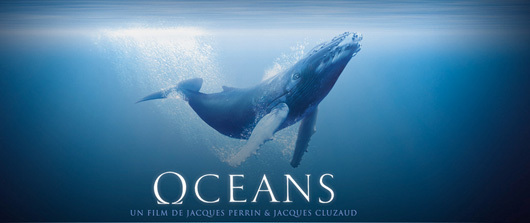我觉得电影节更像个聚会,中国电影、成都都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奖项来肯定。
撰稿·董铭(特约记者)

作为唯一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贾樟柯执导的新作《二十四城记》被业内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特别是该片表现的内容是关于成都和成都人的,在中国四川省遭受了特大地震灾害后,影片更被关注。贾樟柯导演于5月20日下午在法国戛纳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拍摄成都这座城市? 贾樟柯:我最早构思这个剧本是在1999年,与《站台》同时,当时名字叫“工厂的大门”,想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工业的记忆。我们曾找过山西太原等很多城市,最后确定在成都,是因为这个工厂最多时候有3万职工10万家属,那么大的一个群落立刻就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个特别能体现我想要拍的那种城市化过程的感觉。工厂在搬迁到一个新建的工业园区之后,这块土地就被开发成一个楼盘叫二十四城,我便以此作为片名。我觉得成都给我一种非常平和地观看世界、观看历史的态度。各方面的快速变化是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事,这里面带出了一个广阔的中国的背景,拍中国人现实的处境是我一直关心的,以往我的电影都是拍当下,但这部电影会跨越50年,我觉得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换一种态度去看历史,对历史变得轻松一点,宽容一点。 记者:为什么会选用三代“厂花”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呢? 贾樟柯:在对工人进行采访的过程中,那些女性讲述者们感情的充沛让我很有感触,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立足在一个女性的角度,然后才想到“厂花”这样一种人物。为了丰富叙事视角,我加入了陈建斌这个上世纪60年代工人的角色,也是一种男性视角的补充。这样正好粗线条地勾勒出50年的历史,也是三代女性她们感情的线索。比较好玩的是时间跨度虽然有50年,但整部电影是一个现在的时态,过去存在于讲述和追忆之中,不是一种真实再现,而是她们的生活与回忆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 记者:影片为何选择了虚实结合(一半虚构一半纪实)的手法,并选择明星来出演? 贾樟柯:这次我将故事性和记录性糅合在一起,并且特意让观众分辨出这两种手法的差异,记录性的内容会占到全片的百分之三四十。我之前的长片都是纯粹虚构的故事,虽然看上去像纪录片,但都是在严格剧情的规定下表演出自然生动的人的状态。这次我也不会像《三峡好人》那样,再拍出一个纪录片《东》来了。这次的记录部分主要是五组真实工人的讲述和访谈,我觉得现在已经糅合得相当完整和完美,所以不必再单独剪出一部纪录片。这部作品对演员的台词功底要求很高,其中讲述和回忆有些像舞台上大量的对白,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找职业演员来演。在想象这三个女主角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现在这三个演员,吕丽萍出道以来出演的作品那种真挚感特别强;陈冲的细腻能丰富人物的内心,她对生活感受的表达能力也是无可挑剔的;赵涛很直爽,完全不把私心带入角色的能力让她胜任每一个角色,有时她还会临场发挥加入对白,除了她们我还真想不出谁更适合这部电影。 记者:能说说这次的地震吗?它与你拍摄的故事一样,正好也发生在四川。 贾樟柯:我虽然没有去过汶川,但曾经为《二十四城记》的拍摄到都江堰的学校里选景。当地的人民生活都很安逸,地震这个概念对他们相对遥远,没想到意外来袭。我这两年一直在西南拍戏,开始在重庆,后来又来到成都。地震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很震惊也很担心,因为我们剧组一半的工作人员都是成都人,我们的投资方华润置地,我们拍摄和采访过的420厂都在成都。后来我们得知所有人平安的消息后,才得以放心。因为《二十四城记》,我们在成都采访一百多个工人,拍摄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我对成都怀有深切的感情。 记者:拍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您觉得这次有机会获得金棕榈吗? 贾樟柯:这是一部非常豁达的电影,它也让我对很多东西开始变得豁达。如同我在故事梗概里写的一样,有很多往事都变成追忆,虽然物转星移,但很多东西依然温暖存在。我觉得电影节更像个聚会,中国电影、成都都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奖项来肯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