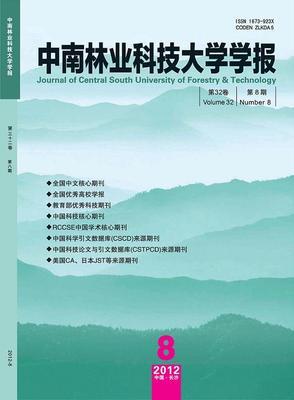“哈英”中的“英”对于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本来是多么沉重的象征符号,然而因为某些真正了解英国文化的文化人的介入,有时这个“英”字的负担减轻了,它的内涵变得朴实了,使得我们很多人又能重新爱它了。
撰稿·沈双 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
我以前有个很聪明的同事,斯里兰卡裔美国人,十分激进,还有一个“毛病”,听到英国人讲英文就腿软。她自称是“哈英”一族。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哈英”相对普遍地存在于殖民地/后殖民地国家与地区的某些人群中。“哈英”并不等于认同殖民主义。有制度性的和属个人行为类之分。制度上的“哈英”大概多少和殖民体制有关,然而个人行为、脾性、爱好,却更多与文化教育或者文化记忆有关。很多反殖反得厉害的人反而是“哈英”一族,其原因是太了解英国人的逻辑,太知道他们的弱点了,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的朋友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种“哈英”情结在内地很少找到载体。年轻一代里有人哈日哈韩,但是那个“哈”法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里的,既不需要懂得外语,也不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前殖民地的“哈英”要比这更深入,更彻底。它是建立在某种对其语言文字的深刻认识之上的。
“哈英”的一个便利之处在于用在文化交流上,它占绝对的优势。看看今年香港艺术节的话剧节目,就知道英国的剧目是挑得精而又精的。英国国家话剧院是我非常喜欢的剧团,几年前在伦敦为看后来一举成名的话剧《历史课的男孩子们》,我在国家话剧团里的大厅里等了两个半小时。果然不负我望。今年又来了两个关于男孩子的戏,《聊天室》和《国民身份》。其中也有女生,但是好的对白都留给男生了。看得出男孩子的成长是剧作者更为关注的问题。 《聊天室》讲的是六个十几岁的孩子深夜里上网聊天,一个男孩儿患有深度忧郁症,想自杀,另外两个一男一女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千方百计地鼓励他去死。另外三个谨慎些,一个甚至曾经自杀未遂过,努力要劝他不要走绝路。这个男孩子被两边炒得烦死了,约大家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到拐角的肯德基,让大家看着他一了百了。 结果他没有死。网上的聊天大概还是起了一点发泄的作用吧。混在顾客中的聊友也松了一口气。观众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青少年的世界就像凌晨三四点钟的网络空间一样,让我们偷窥一下,把我们吓一大跳。这个话剧是英国国家剧团组织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是邀请英国的几位知名剧作家,为中学生量身定做几个话剧,之后由中学生自己挑选,挑中了的剧目由国家剧团负责排演制作。 《国民身份》也同样是讲中学生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糊里糊涂地和同班女生睡了,结果女生怀了孕,男生也因此知道了自己是同性恋。然而结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惨。两个人都继续过各自的生活,几年后重逢也好像老同学一样照常打招呼。年轻人自有对付困难的办法。 这两个话剧都很朴实。我想挑选节目的负责人也没有因为它们来自英国而要求他们必须是“前卫”或者“经典”的。我看的其他艺术节的节目也具有同样踏实认真的态度。没有太多的喧嚣和炒作。而且票价也并不很贵,起码与国内大城市演出的价格不相上下。然而票早早都订光了。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文化市场无论从组织者还是观众来看,都还有待培养。文化是否一定要和某种象征意义连在一起呢?不是说它一定不能有象征意义,而是说不宜过于沉重。 今年香港艺术节的一个特点是再现经典,无论是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斯导演的贝克特的短剧,还是英国交响乐团唱诗班的表演,都围绕着一些众所皆知的经典展开。这些表演对于经典的态度都不能称得上前卫,没有试图重释经典。其实我也认为有时重释是一件坏事。经典成为经典之后,很多人反而不了解它的真正的内容了。“哈英”中的“英”对于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本来是多么沉重的象征符号,然而因为某些真正了解英国文化的文化人的介入,有时这个“英”字的负担减轻了,它的内涵变得朴实了,使得我们很多人又能重新爱它了。这整个过程是需要有识人士的参与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