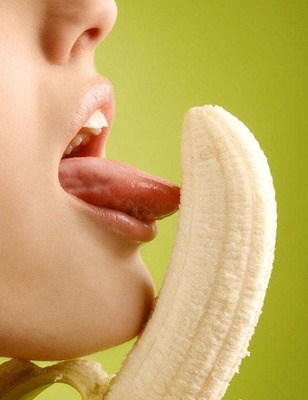王军 备受瞩目的许霆案(许霆个人账户只有100多元,却从“失灵”的银行ATM机取出17.5万元,后被判无期徒刑)日前重审。在电子商务日趋普及的今天,该案的标志性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 交易人的权利义务在人机对话的电子商务活动中究竟如何界定?这是许霆案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一项基本的原则和共识是,机器的一切意思表示都应该推定为(设置该机器的)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机器交易的当事人信赖机器的表示等同于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是每天无数次人机对话交易得以成立和日渐普及的基本前提。ATM机被金融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称为“自动柜员机”,实际上就是银行的“机器人营业员”,其意思表示应为“职务行为”,都应推定为银行的意思表示(参见《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各商业银行的银行卡章程大多复制了这条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声称它的柜员机在许霆取款时因系统紊乱而“失灵”了:在这期间,许霆每取款1000元,柜员机只显示取款1元。许霆的取款行为究竟是盗窃、诈骗还是侵占?或者仅仅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或无效民事行为? 既然柜员机在营业时间的一切意思表示均应推定为银行的意思表示,那么,在银行通过法律程序撤销交易之前,许霆与该银行的交易就应该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假如银行在法庭上证明柜员机的确“失灵”,那么,该银行对许霆的支付行为就构成民法上的“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是:“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银行因此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或者变更其与许霆的交易行为,要求许霆返还多得的款额。 既然柜员机的意思表示均应推定为银行的意思表示,而且在银行通过法律程序请求撤销或者变更之前该意思表示一直是有效的,那么,许霆提取和保有多出其银行卡全额的现金就应该推定为已经银行同意,至少未违背银行的意思。经人同意而公然取人财物,当然不是盗窃。许霆也未虚构事实欺骗柜员机,当然也不构成诈骗。如果柜员机失灵的事实已经法律程序证明,银行已向许霆主张返还,而许霆拒不返还多余金额,则其可能构成侵权。 即便许霆在取款当时认识到柜员机“失灵”了,企图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拿白不拿”,是不是就具有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目的”?关键要看许霆当时的主观状态是否具有“非法性”,换言之,是否违反了某种法定或者约定的注意义务。 在使用柜员机时,如果柜员机的失灵侵害了用户的利益,用户有权要求银行纠正柜员机的错误。这是用户的权利,而非义务。同样,柜员机失灵给用户带来意外利益时,没有法规或者合同规定用户有义务通知银行。如果说,凭常识或常理,任何正常人都应知道柜员机“少扣多给”是反常现象,这是不是就给用户施加了某种注意和通知义务呢?反常或者罕见未必就是不合理、不可能的。当今社会无奇不有,匪夷所思之事时有发生。用户为什么不能认为这是银行在搞某种“馈赠活动”呢? 反常交易导致意外利益,的确应该引起一位诚实信用的当事人的注意,进而采取针对交易对方的必要的通知、保护和照顾行为。但是,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受领意外利益而不通知、不保护对方,是不是就构成恶意或者就具有了犯罪故意呢?在我看来,这只是不诚信的表现,而不是犯罪故意。许多论者都把许霆的“恶意”或“非法占有目的”当成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事实。恰是这一点误导了人们的思考。 此外,围绕“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律解释,也产生了认知误区。如何界定“盗窃金融机构”?人们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8条: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这条解释的重点,与其说是给出完整定义,不如说只是强调盗窃物的范围应限于资金和有价证券,而不包括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等财物。所以,该条解释并未提供完整的犯罪构成。审理法院有机会也有权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的具体含义。 公诉人在庭上指出:“生活中难免有诱惑,以不变应万变的是我们内心的善和对法律的敬畏,不义之财不可取。”是的,作为道德戒律,“以不变应万变”是人之性灵的最高境界。对刑事司法而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刑适应等“不变”的信条也是法律应对“万变”的现实而不离其宗旨——公平正义——的法门。“变”与“不变”,的确深有隐喻,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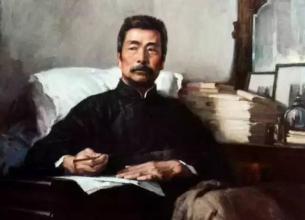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