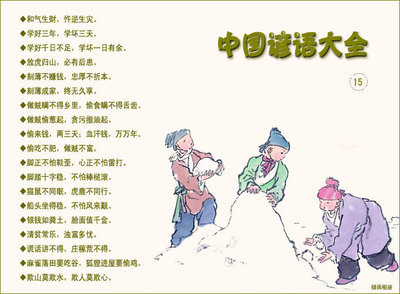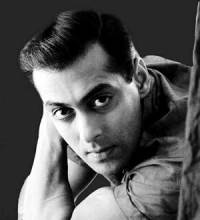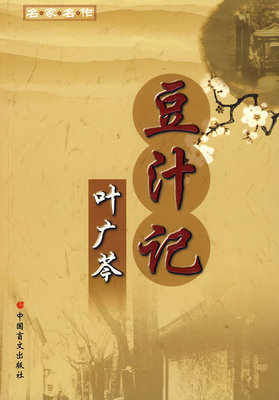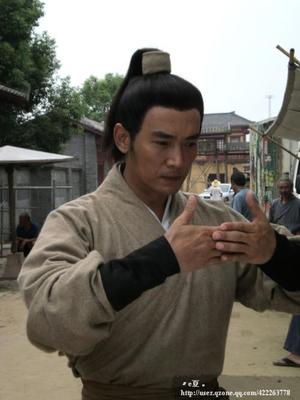文/王军

2007年10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政府发布《嘉兴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住房抵押借款、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依照该《办法》,嘉兴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农村住房设定抵押,从嘉兴市农村合作银行获得贷款。《办法》自11月1日正式实施,但实施了一个月后,没有发放一笔贷款。实际上,浙江湖州早在2001年就尝试过农房抵押贷款,但至今还没有农民通过农房抵押获得贷款。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久前,我在本专栏发表了《穷人的“另类担保”》一文,以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为例,试图说明,贫困人群缺乏可担保财产,而一般的商业银行又不发放无担保贷款,因此,法律有必要放松限制,鼓励银行家们探索和发掘贫困人群的非物质的“另类担保”,以使穷人有权享用现代社会的金融资源。 但当前更为急迫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大量财产,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尚不能物尽其用。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如果说,对于缺乏财产的贫困人群需要发掘“另类担保”的话,那么,中国农民现在正“捧着金碗讨饭”:他们已经拥有的物质财产——土地“用益物权”——还无法成为合法的担保财产。 我国房地产法律遵循“房随地走、地随房走”原则,农房建于宅基地之上,以农房抵押,就意味着债权人行使抵押权时可能发生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而依现行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主要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如荒地、荒沟、荒丘、荒滩)。农用地、宅基地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组织,而使用权通常归属于农民个人或其家庭。在“物权法”上,这类土地使用权被分别定义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两种物权衍生自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用益物权”中的两种法定类型。从概念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法定类型的物权,以之设定抵押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1995年《担保法》和2007年《物权法》均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在宅基地使用权禁止抵押和转让的前提下,农房就成了一种不可转让的财产。农房抵押也就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和可操作性,金融机构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抵押物。于是,对农民而言,农房及其宅基地使用权仅具有居住的价值,不能转化为投资性资产。 然而,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和转让(从而限制农民融资)的理由竟然是保护农民生存权和社会稳定。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尚未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宅基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农民一旦失去住房及宅基地就将“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影响社会稳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解》,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 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住房和宅基地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吗?或者尽管知道,但他们缺乏足够的智力去判断住房抵押是否可能危及“安身立命之本”,因而需要立法者事先为其做主放弃处分权?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民法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了未成年人和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外,还应该包括农民。因为,只有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自主决定个人事务,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恐怕没有人会公开赞同这样的论调。但实际上,许多以保护农民的名义限制乃至剥夺农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当然,保护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也许仅仅是为了防止流离失所的农民“影响社会稳定”。这个理由可能更拿不上台面仔细推敲。言说者应扪心自问,他们所说的“社会”究竟是“城市社会”还是全民的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是不是必须以压制农民的发展为手段?农民固守在一亩三分地上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为什么生为农民就应该一辈子以农业为生? 对于嘉兴尝试农房抵押的做法,有人认为违反了《担保法》,甚至有违宪之嫌。不错,这里的确发生了“违宪之嫌”,但“嫌疑人”不是农房抵押政策,而是“担保法”和“物权法”中的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条款。因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城市居民的房产可以依法抵押或转让,而农民的房产却不可以,这种不平等法律的合宪性的确是可疑的。 “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列为“物权”之一,但又禁止其设定抵押。这样的法律是否有助于防止农民丧失“安身立命之本”不得而知,但它的确大大限缩了农民分享金融资源的机会,浙江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点。禁止农民自由处置土地,实际上锁定了农民的自主选择,从而将农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转化为一项义务。以保护的名义施加控制,用家长主义的“呵护”取代法律的平等对待,这都是与宪法和法治背道而驰的做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