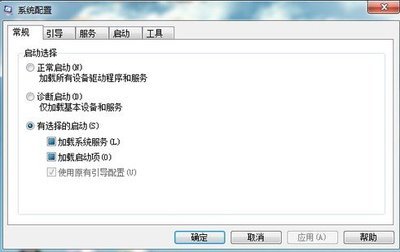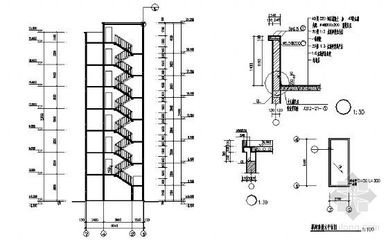谁都看得出来,有资格说“让一步”的,那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有余裕的。而整部作品的叙事技巧和情感机关,也全在这“让一步”。
撰稿·毛尖 专栏作家
表弟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上同班的女孩,不知道怎么表达,走过女孩身边,扯掉了她的辫子。那时我们都笑话他,自觉自己是长大了,长大当然知道如何表达。 可是也不一定。活了半辈子,茫茫人海中走走,我自以为早练就了声色不动的功夫,但是,去年在香港见到张大春,还是慌张得不行,虽然没上去扯他辫子,但一桌吃饭,听到有人叫大头春,还是哗啦打翻了葡萄酒,血红哒嘀地坐在餐桌上,心中的懊恼简直可以溺死自己。 热菜没上,我就溜了。第二天和张大春一起当评委,我在散文组,他在小说组,当时觉得是有生以来最体面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敢找他说话,不知道怎么开头,“张老师,我一直很喜欢读您的作品”,那得穿中学生校服才合适;“大春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年轻英俊”,那是把自己当范冰冰了;心中千军万马,后来索性躲着他走,草草地当了评委,草草地回了上海。 回上海路上一直听宝爷赞美张大春,连带着加深了对宝爷的好感,宝爷还告诉我,一直想把张大春全盘引入大陆,但大头春眼界高,至今没看上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出版社。正遗憾着,世纪文景推出了《聆听父亲》。 《聆听父亲》其实在坊间已经流传很久,除了被冠以很多最高级,还被爆了很多第一次。比如,朱天文说,“第一次,他如此之老实;第一次,他收起玩心;第一次,他暴露了弱点”;而用张大春自己的说法,“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甚至,“第一次,他边写边哭”。
打开书前,腰封上的推荐,媒体的欢呼,已经把我们的情绪铺垫得非常饱满,甚至,我找了一个静悄悄的夜晚,黄道吉日似的,手边还放了一包纸巾,自觉凭自己的控制力做不到眼睫毛抖抖就能过昭关。我看得很认真,很投入,一直到东方鱼肚白,我沉浸在张大春的前世今生里,既希望做他的祖宗,又希望当他的儿子,当然最好能当张大春。但是合上书,回过神,我发觉,自己竟然没流过一次眼泪,倒是有几次,还笑过,比如他替他爹抱不平,因为爷爷对爹不好,他冲口说出:“爷爷是个老混蛋!”然后父亲一巴掌就拍了上来。谁小时候没这样的经验,帮着妈妈骂爸爸,结果两边不讨好,凭空两记麻栗子! 作者边写边哭的作品,又是平素真相莫辨的张大春第一次示弱之作,读者没有跟着哭一场,是我们的智商出了问题,还是情商有了欠缺?《聆听父亲》再看一遍,我这样为自己说情:家族记忆也好,国人乡愁也罢,在我们读者这里,还是传奇啊!清朝的算命先生我们没见过,三百亩良田没见过,甚至,大姑二奶三爷这些称呼,于我们,也都是章回小说里的称谓,没贴身碰到,在书里又是东出西没,刚有模糊印象转个身已经下场。不过,张大春说他自己边哭边写大概不假,因为书中的曾祖母、大大爷、五大爷、六大爷,对于大头春,那是圣经和超我,面对身家性命,除了软弱,还能玩出什么花招?而且,让我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来揣摩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在我看来,示弱,就是这部作品的最大花招,或者说,最大技巧。 书中几次强调,“让一步”是他们张家门儿的德行,但是,谁都看得出来,有资格说“让一步”的,那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有余裕的。而整部作品的叙事技巧和情感机关,也全在这“让一步”。他讲故事前让一步,说是讲给尚未出生的儿子听;大大爷在“筱云班”的故事没有兜全,他让出一步,让六大爷的《家史漫谈》出场;他开头是让,结尾也是让,逃难路上的母亲,本来可以展开最煽情的片段,他让给了下一部曲。 嘴上让一步,笔下千万亩,他哪里是掏空了,写完《聆听父亲》,才是天下无难事。家族故事里能拉扯进奥德修斯,装下李逵鲁达,张大春第一次踏入了鬼斧神工的境地,嘿嘿,大头春索性抖落一身繁花,三分丰子恺,三分周作人,三分泰戈尔,再加一分“让一步”,写出《认得几个字》,表面娱子教女,其实标语口号:普天之下,莫非春土,率土之滨,莫非春臣! 这个时候,让我们使个坏心眼,对大头春说,你哭的时候,我们没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