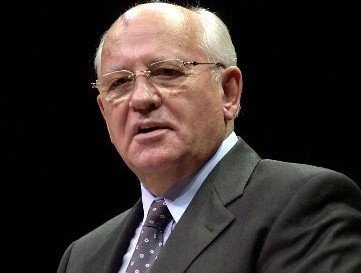我真的很困惑,索罗维奇们的选择,到底能不能被称作是选择?
董铭
《伪钞制造者》比起另一部二战片《卡廷惨案》来说,要显得“轻”得多了。然而这种轻,却是导演斯蒂芬·罗泽维奇刻意处理的结果。 轻微的手持和长焦镜头,让《伪钞制造者》在影像上有种真实的记录感,很容易把观众带入到集中营的阴暗氛围中。但是配乐的大量穿插,丰富到溢出的渲染,又使得影片蒙上了某种脱离历史的浪漫感,把其间的讽刺意味,带到更加广阔的主题上。罗泽维奇早年一直从事纪录片拍摄,并不缺乏沉重的表现手法,而这次他却避开了战争影片惯用的角度,从另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阐释集中营里的那些犯人,或者说,那些“工人”。 在这座濒临死亡的集中营里,特别分出的封闭区域,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特别工厂。它对外被冠以“伯恩哈德公司”的名号,甚至算是座“国营企业”,只不过生产的产品,却是反国家的“伪币”。在这家企业里,曾经的艺术家,当年的造假天才索罗维奇成了中层管理者,他不再是罪犯,也不算是囚犯,而是扮演一个介乎工人与商人之间的角色。“制版车间主任”不容易做——既要和凶残的屠杀者做交易,又要保护同伴们都能活下去;既要委曲求全替纳粹做事,又要不昧良心从中作梗。当战争的杀戮被隐藏时,观众只看到了一群忙碌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是继续战争,他们的工资是自己的生命。 口琴、钢琴、西班牙吉他,歌剧唱段的反复出现,冲淡了二战集中营里的苦难和沉重。《伪钞制造者》并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惨烈,仅仅是通过某些侧面线索来交代“伯恩哈德公司”的员工们与战争的联系。在所有的同伴中,唯一牺牲的只有男孩科尔亚。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出现其他集中营电影中常有的大屠杀场面。在影片的开始和结尾处,导演甚至处理得很商业,只留下淡淡的忧伤和自责。甚至完全可以把中间段落,看成是家公司在运作:从组织建立,到完成指标,打开销路,中途研发受阻,错失商机,最终倒闭走人。一场战争史,在导演的手中,变成了一家企业的兴衰史。德国人伪造英镑美元,本就是战争中的一步“妙着”,在革命者博格看来,自己被迫所做的事情,已经犯下了为虎作伥的罪行;而在造假者索罗维奇的眼中,这仅仅是另一种工作,能够活下去的工作罢了。 我们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的苦难,无从责备他们,虽然从普世道德来看,博格无疑是正直而伟大的战士,但影片却并没有否定索罗维奇。博格、索罗维奇和赫尔佐格三人构成的冲突,足以撑起整部电影狭小的格局。索罗维奇的复杂则在于,他曾经是名罪犯,被预先剥离了道德和正义的约束,而同时他又是犹太人,身具保护同胞的侠义,以及讨价还价的民族本性。也正由于如此复杂的性格,才能让他在纳粹的屠刀下,得以保全了自己乃至同事们的最大利益。这个利益,也是他们身为集中营囚犯仅剩的一点点东西:生命。 伪钞与死亡,仅仅隔了一堵木墙。墙那边的囚犯在被肆意屠杀;墙这边的囚犯却在快乐地打乒乓球。当印刷工人重新见到印刷机时,他们激动得流泪,这或许只在二战集中营里才能见到。“这样做就是在帮助德国人,改变战争的进程。”索罗维奇们心里其实很明白,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卡廷惨案》要重得多,黑白分明得多。1940年前后,苏联与德国瓜分波兰后,苏军先后杀死2万多波兰降军,讲述这个故事,不会面临《伪钞制造者》带来的困惑。我真的很困惑,索罗维奇们的选择,到底能不能称作选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