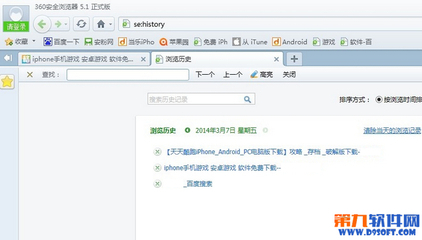◎朱文轶 国祭史 对孔子常规性国祭的可靠记载,最早是在公元37年。东汉建立者光武皇帝于公元29年幸山东,祭孔子陵,公元37年又封孔子的两个所谓直系后裔为侯,命其中一人代表朝廷向孔子献祭。从公元72年到124年东汉有3位皇帝先后谒孔子故里,祭祀圣人。以后历代王朝的帝王继续提倡对孔子的崇拜,这为曲阜的孔家人带来了无上的光荣,为这个特殊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直到对孔子的国祭成为常规之时,曲阜的孔家才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公元8年,儒生梅福上书朝廷,指出只有曲阜有孔庙,但孔子的后裔仍然是平民,没有免除赋税的特权。梅福指出:“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或其福……” 从公元37年开始,因为国家开始祭祀孔子,曲阜孔家的一些人逐渐发达,但到了189年,他们因战乱而背井离乡。公元221年,社会秩序暂时恢复,魏文帝组织人马寻访圣裔,从别处找到了一个孔子后裔,让他主持曲阜圣人的祭祀仪式。以后的王朝更迭总是充满了杀戮,使得孔家人逃离曲阜,而每当新王朝建立,朝廷就会下令寻访孔子后裔。 这样看,虽然尊孔的传统从汉开始,但曲阜作为孔子故里被广泛认知,和“孔庙”这个建筑符号被不断强化不无相关。“汉王朝仍然缺少修建孔庙的热情。”中国社科院古代建筑专家傅崇兰说,“只是到了唐宋时期,扩建孔庙的热情才逐渐高涨。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嫡孙为‘文宣公’之后,开始增扩庙制。” 不过,北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孔子45代孙孔道辅上书朝廷时还是称“曲阜祖庙,卑陋不称”,足见开元年间的“广大其庙”变化仍然有限。傅崇兰说,直到宋真宗在泰山封禅(公元1008年)大兴土木建造行宫,孔道辅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0年后,请用宋真宗建造行殿的剩余木料进一步扩大庙制。 这一次耗时多年的大规模扩建,突破了之前“因宅立庙”的布局框框,形成了殿、堂、廊、庑的建筑群,房屋总数达到316间。“由大成殿、寝殿、杏坛、藏书楼构成的孔庙庙制的基础框架。”傅崇兰说,“正殿的规模达到了大型殿宇的水平,七间重檐、歇山和同时期的遗构太原晋祠圣母殿基本相同。按照宋代礼制规定,孔子祀仪等级属于‘中祀’,和‘大祀’一级的九间重檐庑殿顶大殿相比规制稍低一等。孔家的住宅区就在孔庙的北面。” 宋仁宗也将孔子第46代孙孔宗愿由“文宣公”改封为“衍圣公”,世代承袭,这次加封和孔庙扩建同时完成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开始。官方首次从仪式上承认了曲阜孔氏对孔庙以及对于这个特殊家族的管理权——只有他才具有全国性孔子祭祀的主持资格,也只有他才是确认孔子后裔的唯一人选。

人们神话般地相信,从神圣的祖先以降,代代长子连成的血系之线至今没有中断过,“中断然后寻访”的模式是基于这种观念核心的。后唐时期孔仁玉和孔末的传奇性故事尤其体现了这个观念。在孔氏的直系谱系中,孔仁玉是第43代的独子;孔末是孔家的仆人,原来叫刘末,进了孔家后改姓孔。那时候,家中所有仆役都要姓孔,直到明朝结束时这个规矩才被改变,那之后任何仆役都不准姓孔了。据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野心勃勃的孔末想篡夺孔家的财产和地位,他杀害了孔家的家长,还想杀掉年轻的继承人孔仁玉。孔仁玉找到一个机会去找奶妈张妈。后来孔末来找这孩子,张妈给自己的儿子穿上孔仁玉的衣服,让他代替孔仁玉被杀害了。然后孔末自称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几年之后,孔仁玉在张妈家里长大成人,向政府报告了孔末的罪行。朝廷重新将孔仁玉立为孔家的家长,于是他就成为“中兴祖”。 在过去藏于衍圣公府上的族谱中,这个故事更为详细,它还导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习俗的形成,就是区分出内院孔和外院孔——前者指孔仁玉的后代,后者指孔末的后代,又被称为“伪孔”。曲阜1937年出版的一本族谱中有一篇题为“伪孔辨”的短文,其中有些图式,告诉人们如何区分篡位者孔末和中兴祖孔仁玉的后代。实际上,这个故事更核心的价值观在于,它给曲阜的主人被官方赋予的权力提供了让人信服的族权依据。 不过即使毫无争议的继承人早已出现,新王朝的皇帝也未必会认可他,但新皇帝仍然会认可曲阜。例如公元1128年,女真人入侵中原,汉人朝廷确立的衍圣公带着家眷逃往浙江,在衢州安家。这就是说,官方认可的孔家直系后裔全家离开了曲阜,逃往了南方。但是,蒙古人后来灭了女真朝廷,既而向南宋政权问鼎轻重,并于1282年将其消灭。蒙古人的朝廷逼迫衢州的衍圣公孔朱让出封号,铁腕的忽必烈汗将衍圣公的封号转给了曲阜的一个人,表彰他能够负责任地留在了家乡,看护孔子的陵墓。 社会学者景军在他的研究中认为,“衍圣公及其近亲对自己是孔子直系后裔的宣称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这种宣称之所以能在千百年中不断被明确地重复,这需要两类历史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国家权威乐于寻找自己信任的人物来组织曲阜的祭孔仪式;另一方面,有相当一批野心勃勃的孔氏子孙希望自称为一位辉煌祖先的后裔,尤其是当这位祖先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的时候。换句话说,衍圣公和衍圣公的曲阜都是在两套制度结合的时候,成为政治性的被指定者,而这两套制度就是:祖先崇拜的私人行为和国家对孔子的尊崇”。 “三孔”的确立 对一些观察者而言,曲阜的意义并不只是它本身,它的确隐含着儒家学说所规定的一些秩序。曲阜的孔府、孔庙和孔林统称“三孔”,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年青的建筑师丁在2002年第一次近距离对孔庙进行研究和测绘时,就注意到在2000多年的延续中,曲阜的中心建筑群表现出了超强的稳固性。丁和他的导师、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王其亨因为6年前一场“水洗三孔”危机被曲阜文物局邀请参与对“三孔”的勘验。他说,比如孔庙外围的“廊屋”,这种在汉唐非常流行的方式在后来的民间建筑和官方建筑中基本上已经不被采用了,因为连成一片的建筑,使得火灾成为致命的隐患。 “尤其木架构建筑,一处着火,整个建筑群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丁说,“这种围合式建筑是建筑高规制的体现,后来官方的建筑师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它在实用性上的问题,就广泛使用‘配殿’结构取代了它。‘配殿’环绕主殿,但它是独立的建筑个体。”事实也证明,曲阜孔庙历史上数次被毁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雷灾引起的大火。尽管如此,孔庙的历代重修和扩建依然选择了“遵从古制”——这让这个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是明清时代建筑的建筑群在外观和整体结构上仍然延续着浓厚的“汉风”。 到宋代,建筑木材的供应已经出现短缺了,京城建造宫殿因为大料木的缺少,甚至不得不采取拼合梁柱的办法来解决,而为了保证“先王之道”的延续,曲阜大修的建筑用木一直要求被优先保障。“到明代,因为北方原始森林的减少,北京建造宫殿的大料都是从四川、湖广、江西、云南置官采运木料供应,从这些地方沿运河运到北京大木厂库存,这个传统从朱棣造北京城一直延续到清朝。”丁说,“而雍正时期,以大成殿核心院落为主的重修工程非常大,为了保证曲阜的大料供应,动工前雍正就下令从那时候开始,所有北上的木料,到济宁都停下来,存放在济宁,确保重修所需。”“一些特别大的料,运输很困难。工程停工待料,一直等到天冷之后,沿途掘井泼水结冰,用上百头牛从济宁拉到曲阜。康熙朝时康熙给曲阜题过一个碑,沉重的碑身和龟符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北京运到济宁,再转运曲阜的。”“1911年以前,有记载可查的对三孔的重大维修活动超过60次,孔庙、孔府的总平面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但从总平面的布置手法来说,仍然沿袭着早年流行的院落组合,这种延续性可以说是惊人的。”研究孔子和曲阜的建筑学专家许详林说,“但另一方面,曲阜的确是一个奇怪的样本。它由孔子故里到一个‘圣城’的变化中充满着矛盾感。” 许详林所说的“矛盾感”,是指曲阜建筑“在延续性之外,又无处不在的断裂感”。这种“断裂感”,无论是年轻的丁,还是1935年受南京国民政府之邀到曲阜进行修复孔庙工程勘估和设计的梁思成都感受到了。“皇帝往往是在用他的想象来恢复前代的遗址,创新多于继承。为什么孔庙孔府那么清晰的官式建筑样貌?就因为从明清开始,曲阜的重大工程的施工方都是‘内务府加工部’——修造北京城皇家建筑的全套系统都搬到这个小城里来了。”丁说,“除了整体框架不得不遵循‘旧制’,每一个朝代都把当时最好的材料最流行的建筑细节用在孔庙。” 梁思成在1935年撰写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曾提醒当局也告诫建设者们警惕在重修孔庙的问题上重蹈旧辙的危险:“在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两千年以来每一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经破弊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无不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今天,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 掌权者的视角和建筑师的视角是不同的:重修曲阜孔庙无疑是一次彰显皇权、树立信仰的机会。 许详林说,金代开国70多年后,金章宗拨巨款兴修因为战事被毁的曲阜孔庙,从《孔氏祖庭广记》所录的“金阙里庙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完全超越北宋的华丽。“南面,在原大门这儿加了一道‘大中之门’,大中门前设棂星门;北面,扩展了孔氏族人居住区——‘东位’、‘西位’;东面,扩建衍圣公府和庙学区;西面,拓宽了齐国公殿与观德门之间的距离。在建筑细节上,完全是‘弃旧建新’的做法,正殿和两庑屋顶用绿琉璃作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槛帘拢。”他说,最突出的就是外柱使用雕龙石柱,这开创了曲阜圣庙使用龙柱的先例。 而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超过历代工程规模的一次大修,则更是一次皇家威仪和大国气魄的集中展示。引起这次大兴土木的原因正是雷电导致的火灾: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从家庙开始的火势迅速蔓延至斋厅、东庑、寝殿、西庑、大成门、大成殿、洪武与永乐两座碑亭,烧毁123间房屋,一直烧完西路的启圣殿后,大火才止息。“朝廷调集了京畿和各个王府的工匠汇集曲阜。这次完全不只是针对‘天灾’而采取的恢复性建设,明朝廷实施了一整套以修建孔庙为中心建设曲阜的全盘计划。”傅崇兰说,“仅大成殿和其他庑房修建就历经4年,耗银15.26万两。敕调徽州工匠刻制了大成殿四周28根雕龙石柱,比金代规模更为宏伟。重修并再一次扩建孔府和孔林,由当时著名文学家、大学士李东阳监工,建造了占地巨大的孔府花园。此外,在孔府门前留下了很大一片空地,在空地之东第一次兴建鼓楼,鼓楼门东西正对孔庙的东门,直通西门,形成了东西轴线。”“洪武十年到成化二十三年间,诏修孔庙的记录共有6次,其中永乐十三年到十五年和成化十九年到二十三年两次规模最大,到弘治十七年修成的孔庙总平面已经极为宏大了,大成殿的华丽程度比起北京宫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此,曲阜的“三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清朝做过多次修葺,在规模上一直未有逾越,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只是在雍正朝的重修中将正殿正门的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两庑改为黄瓦剪边,又一次提升了孔庙的规制级别。光绪三十二年,经慈禧授意,把孔庙祀典由中祀升为大祀,孔庙所有门坊亭阁均改为黄色琉璃瓦顶。 明弘治时期,曲阜和“三孔”仍不是一个绝对统一的概念,曲阜县中心离“三孔”相隔10里。“三孔”被无限强化的同时,曲阜县相反倒显得像是一个陪衬物了。这个以祀事功能为主的城市,一旦战争来临,它有点显得不堪一击。 移县就庙 曲阜城市功能的单一化,决定了这个城市经济来源的单一化。曲阜,作为城市的防御和贸易功能的退化,在这个城市后来历史中都显示出来。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一次农民起义的攻击几乎给这个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场爆发于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给曲阜造成的破坏能从按察使兖州道佥事潘珍的奏折里看到,在这份不长的文字里,潘珍向正德皇帝诉苦陈述守卫曲阜的困难:“曲阜县去庙仅满十里,城防不足以御寇,今该县官衙并城中居民房屋皆被焚毁十无一二。”如果是一个一般城市,这场灾难就足以使这个城市一蹶不振了,烧毁房屋和走散的人丁,以当时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相当长时间可能都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潘珍这份奏折的后一部分才是他想说的重点所在:“请趁此县治残毁之余,庙貌犹存之际,将曲阜县治移徙庙傍;量筑城池以备防守。庶庙貌县治,皆可以永保无忧……得旨报可。” “筑城卫庙”——孔庙救了这个城市。当时日照、蒲台、武城、阳信这些地方尽管受损程度不及曲阜,但也无一不是满目疮痍,曲阜率先得以恢复,则完全得益于地方官员以孔庙之名迅速申请到了重建资金。潘珍的上奏获准后,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七月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六月,明朝用了前后10年时间,3.58万两白银修筑了新城,将孔庙和孔府环入城内,县治由古鲁国心东的旧县治迁往阙里,治所安排在孔庙围墙之外。对曲阜来说,这场重建意义非凡:嘉靖以前,孔庙离曲阜县城有10里远,而且没有城墙围护,这次后,一个以孔庙为核心并有城墙保护的城市诞生了——孔庙从一个城市的附属建筑,第一次成为城市的中心了。 梁思成在1953年考察孔庙时,对这次历史事件在曲阜历史上的重要性也一再提及。他说,“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现在曲阜的雏形”。 “曲阜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迁。”傅崇兰说,“这个城市以孔庙为中心祭祀功能,和孔府的府第功能与县城的行政功能结合在一起了。”这座全新的庙城,以西门大街路北建县衙署为其政治功能区,以常平仓(内有24间仓房)为其贸易区,以重修县学和迁建到孔庙西观德门外的四氏学为其教育区——整座城市仍然没有任何生产功能和自主经济收入的来源。 “庙城”曲阜从另一角度无疑宣告了这座城市的符号意义,它完全由中央财政供给,成为一个“文化飞地”。事实上,除去官方的认可和贵族的徽号外,历来的帝国政府还赐给了衍圣公及其近亲丰厚的地产、可观的薪俸、昂贵的赏赐、世袭的佣工,并免去他们的赋税。1956年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孔府保管地契册籍的地方发现了起于明代中期(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的“孔府档案”,这批公开档案里,孔府管家孔令隽在回青岛天主教神父鲍润生的信中的一段细节透露了这份府产巨大的程度:“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孔府档案》8115卷)以此计算,供养孔氏家族的田地多达108万亩,这些土地广泛分布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和安徽五个省。 “单纯从历史演变的立场上看,以一座私人住宅,两千多年间从未间断地在政府的崇拜和保护之下,无论朝代如何替易,这庙庭的尊严却从未受过损害,即使偶有破坏,不久即修复,由三间居堂至宋代已长到三百余间……其规模制度与帝王相埒……由建筑史看来,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梁思成考察完三孔建筑后在他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感叹说。而长期主持中国古建筑测绘研究的王其亨认为,这种保存方式的经济基础,极为奢侈的财政供养当然不容忽视。 当然,从城市完整性来说,问题也很明显。曲阜对于国家形式和政府财政的依赖几乎成了这座城市生存延续的唯一条件,以至一直到民国,曲阜连像样的农业生产都没有形成,更不用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育了。根据曲阜县志提供的信息,“到建国前,曲阜仅有的几家作坊式的私人工厂全部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871万元”。但这种落后从另一方面,又恰恰保护了曲阜城和孔庙的完整,“如果曲阜成为一个充满行政机构的城市,或者成为一个生产性城市,绝不可能有保存到现在都如此完好的孔庙和几乎接近历史城市的城市格局”。 前提是,曲阜和主管它的孔氏家族必须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崇,一旦供给中断,这座城市的命运就岌岌可危。魏晋南北朝,一个漫长的强大中央集权时代刚刚结束,玄学流行,佛教道教备受推崇,尽管孔子的嫡长孙仍保持侯爵封号,但往往是“有封爵而无胙土”(清乾隆继汾《阙里文献考》26卷),仅有食邑一二百户,曲阜城景况十分萧条,“庙貌荒残”,“庭宇倾颓”。 1912年民国建立,曲阜的灾难和孔氏家族的灾难再一次到来。衍圣公及其族人所享有的特权和徽号并没有取消,但地方官员和军阀可以不受帝国政策的限制了。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他们越来越多地向曲阜的孔家征收财产税和徭役,同时,衍圣公作为中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也遭到了威胁。多年战乱后,孔家分布在5个富裕省份30多个县的丰厚祭田到民国初年已经大为缩水,根据1919年的数字,山东的祭田总共有323802亩上等农田。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将孔氏家族的祭田国有化,1929年10月这个计划被公布后,曲阜极为震动,孔氏的家族长老恐慌之中联合各阶层商量对策。他们为了不失去这些祭田,以衍圣公孔德成(现居台湾)的名义提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宣言,这项宣言在报纸上发表,它攻击这项动议侵害了私人财产,也威胁到国家的尊孔政策。 最后,财政部长孔祥熙介入,由他出面支持曲阜的孔氏家族,结果这项没收孔家祭田的动议在内阁会议上被否决了。但对此事的宣传却焉知非祸,因为它导致人们开始公开讨论,帝国时衍圣公的封号在民国时期是否还应保有。1935年,孔德成屈服于官方与民众的压力,终于放弃了这个头衔。 特权与它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了曲阜和孔氏家族的特权,谁要成为这个家族的成员,要拥有在曲阜这座城市的居住权,他必须是“内院孔”,而且属于曲阜的“六十宗户”之一。这些宗户又被分为“大宗户”和“小宗户”,大宗户是指住在曲阜中心的12座府第中的人们,最大的宗户中住着衍圣公及其妻妾子女,其他府中住着衍圣公最近的族人,他们多是富裕而有学识的;小宗户中住着衍圣公的远房族人,其中大多住在曲阜郊区,是农民。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佃农,耕种帝国赐给衍圣公的“祭田”,这些佃农要向衍圣公交租,但被政府免除徭役和兵役。 由于清代实行编审人丁制度,“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在“城中称坊”和“近城称厢”的双重范围内,孔庙和孔府处在曲阜城设点上心区位得以进一步加强。这种以孔子嫡支裔孙为核心,近支次之的族权分布,也同时形成了阶层分布——这给曲阜城的格局留下了烙印,三大建筑“三孔”既是曲阜的标志,也是曲阜的一切。明朝嘉靖年间那次重修后,不断扩建的孔府、孔庙和孔林几乎填满了整个城市的中心,而这个城市的整体面积又如此之小,“如果仅从一个城市形态的角度看,这个城市看上去多少有些奇怪了”。许祥林说,说它完全是孔氏家族的城池也不为过分。 许祥林说,曲阜城内所有街道无法直通东西或者南北,它们都要绕开孔家,孔府和孔庙处于曲阜县城严格的中轴线上,这使得街道相交处多呈“T”字形。1930年,全城有64条街道,全长19494米,其中东西走向的33条,南北走向的29条。同样因为孔府官邸之庞大,曲阜街道的长短宽窄参差不齐,最长的北马道街1425米,最短的文昌祠后街只有63米。由于这个城市公共权力和家族权力的边界一直模糊不清,因此除了孔府和一些通往孔家店铺的街道较为整洁外,“郊区”的道路条件相当恶劣。这个家族式城市的格局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打破,1951年,当地政府辟建了穿过孔府菜园的鼓楼大街北段,10年后,又拆除了东城墙南段,并在曲阜的护城河上建了平桥让五马祠街和东关市场直接相通。 曲阜和孔庙的每一次扩建,都伴随着衍圣公地位的不断抬高。衍圣公的品秩并不是一开始就袭封和所谓的“文官之首”,宋代始封孔宗愿为衍圣公时,孔宗愿只是兼了个仙源知县的小官。金元时期,衍圣公才逐渐由从四品成为四品,而到明洪武元年,孔子56代孙衍圣公孔希学已经被官秩二品,晋阶资善大夫了。 “大宗户”在曲阜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因为“衍圣公”在曲阜的胞弟支系越来越庞大,这些孔氏的“十二府第”也是一再扩充自家地盘。根据1985年出版由孔令志口述的《孔子后裔府弟》,“曲阜孔氏府第的最后一个府虽称之为‘十二府’,但实际上却只有九个府第,其中除七府在城南张曲村外,其他八个府第都在城内,占有大片土地”。在学生时代就到这些府第看过的傅崇兰说,“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宗户府第,都是在康乾盛世修建,并成规模地分布在城内东门大街,五马祠街、棋盘街、三皇庙街,北门大街、宫园街、陋巷街,只有‘一贯堂’在‘衍圣公府内’。它们集中在孔庙、孔府以东的东门大街南北城区,曲阜唯一一块商业集市气息最浓厚的区域也成为以大宗户为主的‘富人区’”。 许祥林强调,曲阜的特权逐渐形成了族权和行政权相结合的一种特殊权力。在孔家的族谱中,“户”这个汉字的含义并不总是一致的。1685年,著名的剧作家孔尚任编辑了一本族谱,从中尤其可以看到这个字的模糊含义。族谱中说,大宗户有670个男丁,根据社会学家景军的研究,由于这些“户”指的是住在曲阜十二府中的人,如果670这个数字基本正确,那么这就表明,每个府中究竟是否只住着一户或一对夫妻就很成问题了。对于“小宗户”一词的运用我们应该同样小心,其中一户有668人,涵盖了曲阜附近的整个一村。另外一个即所谓“文献户”,其家庭单位就小得多了,只包括那些被世代雇佣来保管衍圣公府文件的父母和孩子。 孔尚任记录下的全部“六十宗户”中共有近1万人在世,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龄修研究孔府和曲阜的统计,这些人中列下名字的男丁共有8993人。1764年,曲阜的孔氏家族共有超过2万的男子,到19世纪中期,这个数字超过了4万,其中还不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迁居外地的人们。曲阜以外的孔家有自己的族谱,其中只有少数被衍圣公认为是合法的。 曲阜类似一个宗教中心的地位,它所拥有的行政权除了皇权所赋予的那些,还包括特权的衍生部分,就是它能决定曲阜以外孔氏身份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权力使用相当克制,一旦孔氏权利扩大化,本身就会危及曲阜孔氏甚至城市地位的权威性。 衍圣公清楚地知道这些特权的重要性。曲阜以外的孔氏相当多被排除在外,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衍圣公对待皇恩的谨慎态度。从15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依赖衍圣公来决定谁可以作为孔氏家族的成员,从而享有减轻赋税和免除徭役的特权,如果把这些特权扩展到更多的孔姓人中,朝廷就会觉得它们过于繁重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衍圣公在曲阜以外的孔姓社区中只挑选了一小部分,允许他们享受这些天恩。“这些社区要将他们的族谱寄到曲阜,以便获得合法性。”何龄修就特别注意到这些现象,“这些族谱上要盖有衍圣公的私人印章和宗族会的印章,然后政府才会认可它们的主人可以免除徭役和减轻赋税。” 对整个孔氏家族来说,衍圣公是最高统治者,拥有中央特许的超经济统治权,而按照一品官宅第形制建造的孔府基本上就是曲阜的统治机构。府中除住宅以外还有官衙:有审理用的公堂,有行使催收田租、管理奴户及掌管印信文书、礼仪制度的综合机构(合称为“六厅”)。 族权和行政权在曲阜的高度统一有时也会让中央政府和一些言官们担心,但在清朝,中央政府对曲阜的孔家表现得相当宽容和器重。“雍正时期,孔庙主要门殿的绿色琉璃瓦被替换为黄色琉璃瓦,这意味着孔庙建筑规制的整体提升。”许祥林说。明代曲阜的地方官员改为世职知县,曾一度由孔府掌门人保举一人送部充授,领敕赴任。乾隆年间山东巡抚白钟山曾就这个问题上奏说,“曲阜知县向由衍圣公保举,每多瞻顾营私。若其人懦弱,即听挟制;若其人才干,则诸事阻挠”。白钟山还举了衍圣公孔昭焕因为派庙户当差事同邹县知县发生争执一事为他的观点作为佐证。此后,朝廷将曲阜知县改由流官充任,第一任由拣选调补的知县叫张若本,但不久,孔家和曲阜知县为争利而激烈争执最终相互控告时,皇帝“对孔勿问,而把知县调走了”(《曲阜县志》)。 岌岌可危的孔家店 1935年,孔德成被迫放弃“衍圣公”封号前,这个正处于危机重重之中的大家族本来将有可能获得一次全面复兴的机会。民国政府试图再一次在全社会树立儒家信仰,但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个尊孔和刚刚被推翻的王朝的尊孔有着本质的区别? 民国创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一个民国官员的代表团会聚曲阜。他们带着新政策来祭献孔子诞辰的周年,明显是有意要突出自己的身份。1914年,政府下令把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性的节日来庆祝,在曲阜由政府出资举行庆典,这是曲阜近代史上又一次辉煌时刻。这种新创造的仪式称为国祭,在解放前,国祭的参加者包括国家的代表、省级官员和县长。 景军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这个细节格外重视:“曲阜孔家保存的仪式材料也强调岁时祭祀。事实上,对孔子的这种岁时祭祀是由国家政令规定的。明清朝廷的钦差大臣按时到孔子故里祭献供品,他们留下了无数的祭文。他们在献祭时候就高诵这些祭文。我考察了30篇祭文,其中最早的是1331年的,最晚的是1909年的。没有任何一篇是纪念圣人诞辰的,献上的供品是岁时祭享,其中1/3以上是春天祭献的,这表明春祭比其他的岁时祭祀都更重要。”景军说:“这些都表明,曲阜的‘孔子诞辰庆典’是相当晚近的文化发明,特别是它来自于民国政权试图将自己同以前的帝国统治区分开的努力。” 但这个全新的国祭仪式并没有重新点燃尊孔的热潮,曲阜反而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陷入危机。当激进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把孔子的教导和主张当成国家落后的罪魁祸首时,孔子的公众地位急剧下跌。1928年,在攻击儒家的热潮当中,曲阜一所高校的学生编排了一个叫《子见南子》的剧本讽刺孔子,这引发了一个大案,通过新闻媒体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这桩案件里,自由派学者和著名作家纷纷发表意见,争论孔子是否应该被讽刺,鲁迅也站在学生一边,写了一组文章来贬斥孔氏宗族会。曲阜强大的宗族会打赢了官司,但这个案件却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受损,他们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这场浩大的信仰危机最终还使得解放前曲阜最后一次大修计划因缺乏财政资助而流产。1935年1月,时任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的梁思成受邀到曲阜进行修复孔庙工程的勘估和设计。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被晋军炮火损毁的曲阜孔庙孔府建筑一直无人问津,直到5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拟采取中央与各省分担经费的办法,决定由内政、教育两部与山东省政府各派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中国古建筑专家对其修复。 “当时国民政府很多人反对中央这一修葺计划,中央财政能拿出的经费也很有限,所以想了由各省分担的办法,但是地方上愿意拿钱的也很少。修庙是国民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法,资金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孔祥林说,“在几周的详细测绘各殿宇廊庑损坏的位置和情形后,根据测绘和摄影资料,梁思成着手拟定曲阜孔庙修葺计划,并预估工料价,于7月份完成了《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由于当时黄河决口造成鲁苏两省严重水灾,赈济灾民和黄河堵口复堤工程需要巨额款项,本来就争议重重的大修计划最终无限期搁置下来了。“直到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拨款20万元,修缮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准备‘三孔’的重新对外开放,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曲阜这个一度没落的城市才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