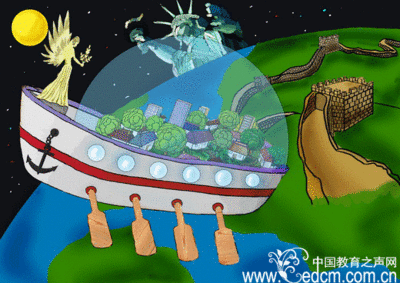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是为出口换取外汇。第二次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一天能收三卡车。收购员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时交账,多退少补,一般情况下200元可支付一天的收购。
◎舒可文
收藏权取消 1950年,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文物保护的法令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各地都逐渐颁布了地方法规,并成立了文物管理部门。法令针对的现实是,40年代末连年内乱,古董文物的价格一落千丈。那时候,在长春街头文物以麻袋论价,国宝级珍品混杂其中,在当时古玩行被称为东北货,各地古董商都到东北去进货。多年后,还有东北货不断出现,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曾讲过一个故事:1963年一个东北小伙子到琉璃厂,用粗布包裹送来一堆破纸片,后经行家拼接,其中居然有赵孟等人的真迹37件。一年后他又送来一堆,又拼接出20多幅书画残卷,但他没敢留下姓名、住址。那时候,做国际交易的古董商收进文物,往往卖给欧洲以及日本、美国的古董商,除了外商高价收购,中国人之间的交易由于乱世已经大量减少。1952年北京的大古董商岳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镇压,就是根据相关文物的法令被判罪,他的罪行之一,就是把石雕《帝后礼佛图》卖给了美国商人。 这个法令所依据的观念是,珍贵文物归国家所有,只能在中国境内交易,不能外流。这其实不是新中国的新观念,不少收藏大家从几十年中国屡遭外辱的经验中,已经建立起了这个观念。1936年,张伯驹想收藏唐朝韩的《照夜白图》,就起于阻挡其外流的动机,当他听说溥心畲所藏的《照夜白图》出让给了专做国际文物生意的上海画商叶叔重,就试图请官方阻拦出境。但晚了一步,这幅名画已经通过另一个文物商,转手给了英国人。第二年,在一个书画展览会上,他看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时,深怕《平复帖》再被古董商卖给外国,才几经周折,以4万元买得。1946年抗战之后,张伯驹在琉璃厂墨宝斋看到展子虔的《游春图》出售,曾请求故宫收下,但因当时故宫经费困难,他只好卖掉自家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凑足220两黄金,“代故宫周转”。1976年,故宫专家朱家老先生捐给承德避暑山庄一批国宝级文物时有一个主要背景,他听说外贸单位跟文物局商议,要收购这批东西。尽管是有价收购,老先生也不愿意让这批国宝外流,他就抢先一步把这批文物捐出,运往承德。 如果说“文物不能外流”在那时候还只是一种民族意识,那么岳彬的被镇压在古董生意人中间则形成了具体的压力。1945年进琉璃厂韵古斋当学徒的王广义老师傅回忆说:“当时外贸部、公安部、文化部三部联合发布指令,规定了三类文物不许买卖出口——180年前的文物;180年以后的官窑、家藏款;新出土文物。除此之外,都是可以买卖的。但是这时候,已经少有人买了,很多古玩行都开始买卖些其他东西糊口,像韵古斋,因为老板兼做茶叶生意,就干脆在韵古斋摆出了茶叶摊子,韵玉斋卖起了粮食,宝华斋卖起了炒货。韵古斋那时候是琉璃厂最大的店,解放前有10个人,这时也只剩下了6个,宝古斋也就六七个人,通古斋除了掌柜的外,就一个伙计,其他就都是连家户了。”这种萧条使以后的公私合营变得相对顺利。以北京琉璃厂为例,1956年琉璃厂十几家老字号完成了公私合营,成为属于外贸系统领导的“工艺品公司文物部门”,由私方人员和国家职工组成,古董商人成为店员,他们有工资,也有分红。不久,有一个说法在琉璃厂传播,说改造后的资本家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还有半只脚没踏进来。没有参与合营的,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便把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了国家。王广义说:“把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馆,掌柜的也就跟着去了故宫博物馆,像耿宝昌、孙瀛周。” 文物部门的上属机构一直是外贸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所属结构。80年代文物商店的负责人景严解释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机构组织形式:因为当时的宣传是“文物属于废品,鼓励以旧换新,文物出口到外国可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但换取外汇只是一部分,外贸部管理不恰当,因为文物业务包含旧书业,1960年的时候就划归新华书店,成为新华书店文物科,对外称文物商店。之后不久,因为它的更多业务与图书业无关,就独立出来,成为一直延续下来的文物商店,这个总店管理着各地的文物商店。 文物商店归属的不稳定,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主要功能几乎完全改变,以收集流散文物、向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提供文物为第一要务。有收购文物权力的只有文物部门和出口公司。 北京市文物商店在北京设立了三个收购站,分处西单、琉璃厂和地安门,除了北京三个坐店收购的,文物商店的师傅被分为东北、南方、西南三个小组,常年在外收集。收购部基本上是由私方人员构成的,因为他们是行家,眼力好,门路熟,他们去看东西,藏家才拿出来给看,新人去了藏家不敢拿出好东西。1960年以前,收购的同时也有买卖,因为老师傅带有老作风,价格合适的时候就会转卖;1960年之后,买和卖就分工了。同时,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也都设有收购点,因为有“文物属于废品,鼓励以旧换新”的宣传,很多人把文物古玩送到收购点,换取一些生活贴补。 文物商店收购上来的东西,经鉴别后,把文物价值高的送交总店,统一调配给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景严说:“其余的分为三等,由文物商店出售。第一等放在商店的‘内柜’,通常在楼上,专供国家高级官员和知名的文化人。第二等在‘中柜’,面向民众。第三等就是可以出口的大路货,放在店面,所谓‘外柜’。商店门口挂上了外宾供应处的牌子。由出口公司收购的古玩经鉴别后,按法令规定不能出口的交给文物局,由文物局转交给文物商店,其余的出口。” 文物公司收购时给的价格都很低。文物商店因为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公私合营时,国家给一些补贴,像韵古斋这种大店的补贴不过7000元,这在文物商店算是最多的补贴。而有些不能出口的文物收上来,放在内柜也不能卖高价,利润非常低,所以收购价格尽量压低。清朝的盘、碗只有3元至5元,一对同治粉彩的大瓶子收购价只有10元。出口公司收购时则是不分朝代,价格一律按尺寸给,一尺二的永乐花口盘子,7块钱收上来。 在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有老师傅回忆说,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的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就是为了出口换取外汇,这也是当时文物部门的主要利润来源。当时的文物商店是工艺品公司的一个部门,从1956年开始,工艺品公司和首饰公司每年创汇几个亿,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古董中也有一些是有文物价值的,20多年后才重新调整了可出口的文物界限。第二次是在1978年之后,“文命”结束后,文物收购点恢复,北京在大葆台、十三陵、法源寺等处建了几个临时库房。现在翰海拍卖公司的赵师傅在这一年从商店调到了收购部,她说,那时候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候一天能收三卡车。这时收购的价格仍然很低。他们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的时候到财务科交账,多退少补,但一般情况下200元可以支付一天的收购。 公私合营后,整个琉璃厂冷清了。1960年文物商店成立后,上面指示要让琉璃厂恢复热闹,整条街被油漆了一遍。之后,每年春节都开一个展览会,在把有收藏价值的文物送交博物馆之前,先让领导、行家们浏览。展览会在宝古斋、韵古斋、庆云堂等店里举办,景严记得经常来看展览的人包括康生、陈伯达、邓拓、吴晗、田家英、吴作人、李可染等。此外,一般市民和老收藏家因为展览会不卖展品,也就不来看了。如张伯驹这种大藏家,出让的多,几乎不再收新的了,一是没钱,二也是害怕。内柜、外柜就是在这个时期区分出来的。1938年参加革命的辛老先生,解放后在国务院外办任职,他说,那时候在高官中有一个古董沙龙,康生是班长。他们经常一起到各店的内柜去选购,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邓拓在宝古斋买画最多,有时候下班晚了,夜里零点他还是要来,宝古斋有专人陪他。他也曾在店里换货,因为出让的画比他买的时候高,在“文革”打倒他时,有一个罪名就是投机倒把。景严说,他们在内柜出售的文物一般定价是高出收购价的20%,5元收购的,6元出售。康生曾在悦雅堂买一件宋代拓本,标价只十几元。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标价100元。 但显然中柜的生意冷清至极,处于全民所有制中的普通公职人员,少有剩余财力购买基本消费以外的物品,以至于在文物商店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傅现在根本回忆不起曾经有中柜的存在,这与内柜的大交易量形成了一种意味非常的对比。 几乎与内柜兴旺的同时期,1961年,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第十五条规定,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明确了文物的国有归属,私人不再拥有收藏文物的法律权利。由于文物不在合法的交易范围内,所以无论是收购还是内柜,实际上都不再具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也不再有市场交易。 心理改造过程 文物价格归零的制度完成建立在一个相对有序的法规指令中,相比之下,心理完成的方式更具侵蚀性。 文物属于国有的概念在制度完成前就植入了社会,大藏家们由于种种缘由把藏品捐献给国家。故宫专家朱家从1953年捐出了700多种碑帖后,几次捐献,直到1994年朱氏兄弟将家中最后一批文物捐给浙江省博物馆。“从此我家与收藏无缘”是大藏家朱家对藏品的告别。1956年,张伯驹向文化部捐献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当时文化部奖励他3万元,不叫收购,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有“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劝说,才惶然收下。章乃器是新中国有名的大藏家,1954年他捐出了第一批1193件个人收藏,种类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收藏不同于张伯驹、朱家那样的世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1948年被电召到东北,参与筹备政协。当时正是东北货四处流散的时候,他在东北期间开始收藏,到解放后的1953年,收藏的文物已经占满了三个大屋子。 张伯驹、章乃器都曾是实业家或银行家,他们从来贾行士风,本不为在收藏上牟利,捐献之举不仅顺应形势,还有轻身卸载的超然。真正能说明文物不可交易的概念之深入社会的是琉璃厂的文物从业者。一位姓宋的师傅说,当时在内柜服务中,偶尔在藏家和文物商店之间发生争执,文物商店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即先上交政府部门,后供内柜选购,而有时一件文物是先在内柜被人选中,后才被挑选上交,这时内柜的客人就要求遵守“先来后到”的通则。 而没有官职的市民在十几年中,已经完全远离了关于文物的任何信息和知识,新的生活冲击着也许还残存的些许印象,这些渐渐模糊的文物印象,突然在1966年更新为否定性的鲜明形象。 这一次的心理改造更为激烈。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命”初期,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工作之一就是这“破四旧”,古董、古迹、字画、书籍,是最明显的“四旧”代表。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物、古籍被砸烂、烧毁。梁漱溟先生晚年描述过被抄家的一幕:“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这时距新中国成立只有17年,许多市民家中都沿用着17年前就购置的老式家具、器具,服饰,即使在17年内也有老式的用物生产供应,没有被抄家的普通市民把家里的旧物挑拣出来,自行了断。甚至有极度惊恐者,把旧瓷器包裹在棉被里砸碎,避免弄出动静,招致红卫兵的注意。 琉璃厂自然是在红卫兵要破除“四旧”的重点地带,文物商店的员工用报纸把整个商店的货架封起来,货物收进库房,内柜和收购部的业务全部停止。整个琉璃厂街彻底沉寂了。一直到1969年重新开门营业,但不仅没有生意,根本就无人光顾,每个店里只需留个老头儿看门,其他人都去开会搞运动了。 打砸抢的狂潮大约持续了3个月后,中央发出指示制止乱砸,改为查抄。红卫兵查抄后集中到一个指定地点,文物商店被派去检查,不是文物的可以砸,属于文物的抄走,运到几个临时集中点。琉璃厂的宋师傅回忆当时看到那些文物时无比震惊,说北京的法源寺、白云观、天宁寺、先农坛体育馆这几个集中点都堆满了查抄的文物,文物商店成立了一个清理小组,大部分员工都被派去清理这批文物。宋师傅在先农坛的清理小组工作了好几年,可以想见数量之大。 被清理出来的文物精品存放在府学胡同的文物局保管,宋师傅说,那时候一到周末,府学胡同里小汽车排成队,堵满胡同。康生窃取文物的罪名所指,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政策规定如何处置,不属于文物商店的经营范围,所以康生看中的,只能“借”。后来的清理工作逐渐正规了,所有文物都有清单记账,宋师傅说:“他们借去了,长时间不还,我们的账对不上,很为难,又不敢催人家。只能跟他们的秘书说,看好了吗,再换一件看?”后来,在查抄文物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特供小组,专供“文革”领导小组“选购”,只是选购的价钱比“文革”前更低了。 1962年分配到文物商店的陈岩,是文物商店公私合营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徒,他描述的齐白石寿桃册页上的印章,昭示着书画被阉割的畸形命运,册页上一共四个印章,有齐白石两方印章,一个红卫兵的红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查抄专用章”,还有一个“康生珍藏金石书画图书之章”。
除了极少的文物占有者之外,整个社会的文物概念被完全倒置。1976年朱家先生捐给承德避暑山庄的那批文物,躲过了流散海外的命运,没有躲过运往承德旅途中的轻蔑。运货的司机在途中接到一笔小生意——运煤,他就把这些文物卸下车,堆在一个院子里,运煤回来后再装车去承德。这一卸一装,文物严重受损。在后来的清理检查中发现,诸如完整的秀墩缺了牙板,多宝格丢了两个抽屉,如此种种。 朱家先生生前把所藏文物全数捐出,也有不得不捐的具体原因,他90岁那年接受采访时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这是他们那一代藏家的自觉意识。另外,也“怕招来灾祸,这个顾虑相当严重”。朱家是朱熹的25代世孙,家传有祖宗像,“这祖宗像不能捐掉,干脆就委托博物馆保管了”。 即使是故宫博物院,从1939到2005年,接受了582人次向故宫捐献的文物3.34万件,直到“故宫80年”的时候,才在景仁宫设立了景仁榜,向捐献者致敬。 收藏权回来的时候 经历了自毁家传和多年的过度出口,本不可再生的文物存量问题出现了,不加以控制,就可能造成近200年来某些文物的历史空白。1981年国家文物局递交上级一个请示报告,报告文物处境:根据过去规定,1795年(乾隆60年)以后的部分存量较多的一般文物可以出口,但是近几年来每年出口较多,有些文物在国内存量已日益减少。如不少博物馆收藏文物,由于库房和设备严重不足,长期露置在院中或棚下,风吹雨淋,造成严重的自然损坏。有的名贵书画,由于存放条件太差,也发生潮霉。而文物专业人员一直不被当做科研人员对待,不少地方的文物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30年间,文化记忆在双重的改造中被割断。“文革”劫后余存的一些器具,难有人识得,即使是琉璃厂的员工也欠缺培训。宋师傅记得在地安门一个老太太家收了一个雪花蓝大碗,当时定价5元,拿回店里后经多位专家辨识鉴定为国宝,有记载说这种碗中国曾有两只,一只在台湾,第二只一直不知下落,老太太家的正是这只。连老太太本人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在那样一种文物认识的畸形环境里,没人再愿意向家人讲解可能招灾的故事。文物中所有的辉煌已经褪色为重重疑虑。 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必要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4年,琉璃厂完成翻建扩大,但是与预期不符的是,由于街面扩大,非文物部门的“三产”进入琉璃厂,经营旅游纪念品。琉璃厂看似恢复了生气,而作为当年最大的古董市场,其盛不在新或旧,而是一股寻古访宝的悠悠雅风。经营旅游纪念品在某种程度上冲撞了文物生意,文物本来已不被人识,与旅游商店相比,经营文物的氛围淡而沉静,少有人光顾,翻建之后反而有些衰败。 为了扩大内柜,这一年,各门市的内柜从各门市分出来,集中到虹光阁,面向更大范围的国内客人。虹光阁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文物可以重新交易了,但是原有的规矩还保留,买东西要拿户口本,填表。并且只可以买,不许转卖。虹光阁开张那天,一件康熙官窑标价只有400元。虹光阁的法律依据是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物的专门法。在这部法律中有专门针对私人收藏文物的条文,条文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其实来到虹光阁的人还是原来内柜服务的高层官员、知名文化人。渐渐多了两种人。一种是倒爷,他们是来送货的,倒爷的货源一部分来自查抄退赔的,一部分是“喝街”收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民往城里带的。与虹光阁同时出现的文物贩子,其实也是惊魂未定,他们买卖文物急于变现,为的是摆脱贫困。变现的最快渠道是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而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对比1950年的相关法令,1982年的保护法等于在法律上归还了私人收藏的权利,但购买文物的权利并不清晰。所以收藏文物依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合法权利,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接受虹光阁的这个信号。即使有人有收藏愿望,但没人知道虹光阁。赵师傅说:一直到90年代初,一年的交易额只有几十万元。“东方朔偷桃”的一个竹雕,在虹光阁标价3000元,放了3年,没人过问。1994年翰海拍卖公司的首场拍卖会上,这件竹雕卖了30万元。 1992年,由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场文物拍卖会,才真正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相关的法律要滞后到2002年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规定,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享有自主处理权,可以通过继承、赠与、买卖、交换等合法手段进行处置而不受干预。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允许建立规范的、除国家专营外的文物市场,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个人对文物的收藏权利才得到确认。文物的身价从1992年开始飞升。 但在文物低谷中受益的马未都知道,他们与老一代收藏人比,现实是严重的先天不足。过去的收藏人都有系统的国学、美学教育,老一代以品鉴文物为雅,相互沟通,交换知识和心得,而80年代交易文物的人是文化断裂中浑然长大的一代,因此也不会有良性的收藏环境。不少拜访者曾追问过朱家先生捐献家藏的真实原因,他说当他看到先祖朱凤标写的联文“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时,才算明确了多次解释未尽的意思。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财力增加着文物中延续的文化精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