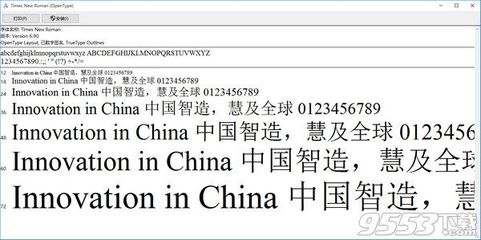文/查尔斯.汉迪,伊丽莎白.汉迪
慷慨再度流行 2004年末东南亚发生海啸灾难后,英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捐赠了大量财物。这次公开大规模的捐赠事件,仅仅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近些年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风尚——同情和慷慨的事例之一。2005年,《时代》杂志顺应时代风潮,把比尔·盖茨夫妇和U2乐队主唱博诺评选为年度人物。《经济学家》杂志紧步其后尘,在2006年2月刊开展了一项关于慈善事业的特别调查,之后还创造了“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这一字眼。 正如《经济学家》有关慈善事业一文的作者马修·比肖普所说:“在富豪和名流界,慈善从未如此流行”。他指出,新的慈善风尚并不局限于北美。在印度,Infosys,Wipro和Dr.Reddy等公司的富翁老板们正在加入包括塔塔、比尔拉和巴贾家族在内的老牌慈善家之列。在拉丁美洲,比肖普援引了瑞银集团马丁·李西提的话:“所有的富翁都有一个慈善计划”。在俄国,石油巨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捐赠了数百万英磅来提高他担任行政首长的所在地——楚科奇自治区的生活条件。欧洲当然也在潮流之列。例如,德国的慈善基金会在10年之内增加了3倍。最引人注目的是,世界第二大富翁沃伦·巴菲特于2006年6月宣布他将捐赠310亿美元给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使该基金会的规模整整扩大了一倍。 美国社会很早就有“回馈”的传统,尤其是成功人士应当回报曾使之受益的机构,并帮助后来人。因此,以往的大部分捐赠方向都是宗教组织、自己的母校,或设立奖学金、资助医院的新楼、博物馆收藏品或歌剧。罗伯特·赖希在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创新评论》期刊中写到:“我们不应该再蒙骗自己,认为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做了很多事情”。 根据《时代》杂志文章的观点,2005年,慈善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年“慈善和慷慨得到了重新定义,美国从它对待世界穷人的一贯迷蒙冷淡态度中回醒过来”。凯瑟琳·富尔顿最近写了一份慈善行业的调查报告,她对此也很乐观:“只要5%~10%的新晋亿万富翁慷慨于慈善事业,他们在未来20年内将改变慈善事业。” 英国在公共捐款方面一向落于人后,每年每人仅捐赠226英镑,大大落后于美国的600英镑。2003年,英国个人捐给慈善事业的数字是72亿英镑,与花费在赌博上的数字相当,而且一半以上的捐赠都来自5%的人。遗产和慈善托管金捐赠了另外30亿英镑。英国人吝于捐款的原因是多重的。例如,在过去的100年里,巨富的数目减少了,而且对于慈善捐赠,英国的税法向来没有像美国税法那样给予诸多优惠措施。因此,大多数美国人是有计划地捐款,而英国人通常是在大街上捐赠小额数目。另外,欧洲的福利社会制度或许也鼓励人们把市场照顾不到的事情留给政府去处理。有人问一个企业巨头为什么不更慷慨一些,他回答道:“我交税了,不是吗?” 与大多数欧洲人一样,英国人更习惯献出自己的时间,而不是金钱。在英国,大约2600万英国人(一半的国民)都做志愿者服务。有些人做得更认真一些。丹尼尔·麦克罗斯基博士是这类时间慈善家的代表。他协助成立了医疗慈善机构Afrimed,并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寻找英国医院认为已过时,但苏丹却急需的英国过剩医疗设备。他指导这些医疗设备的运输和安装,从自己的假期里抽时间每年拜访苏丹医院三次。英国有许多这样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但是,要使慈善真正起作用,需要时间,也需要善款。现在,英国有了改变的迹象,慈善事业正在变得流行起来。《观察家》杂志的克里斯丁·奥登评论道,现在帮助别人比努力赚钱更时髦。菲利普·贝雷斯福德在他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财富排行榜”上添加了一个“慈善排行榜”。他还注意到,在1989年,75%的捐赠来自世袭财产,只有25%来自捐赠者自己赚的钱。现在,情况正好反过来,75%的捐赠来自自己赚钱的捐赠者。特蕾莎·劳埃德为英国慈善总会所做的调查文章《富翁为什么做慈善》证实了这一点。她的受访者中,70%都是白手起家的人,其中一半是企业家,另一半是专业人士。一个企业化的英国获得了重生,正在变得慷慨。但是,这些慈善家与过去不同,他们想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而不仅仅是捐赠。“高度参与”是一个时髦词语。
在这些新的慈善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名流。例如博诺和比尔·盖茨夫妇。拥有390亿美元资产的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是历史上最大的基金会,而且资产额即将翻番。还有谷歌创始人塞吉·布林和拉里·佩奇,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慈善事业将超越谷歌公司的辉煌,在全世界范围内“雄心勃勃地、创新性地利用大量资源来解决世界上的最大难题”。在英国,摇滚明星鲍勃·格尔多夫和大城小厨的杰米·奥利佛因慈善事业而备受瞩目。凭借使之成名的才华,他们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 比尔·盖茨以其建立微软帝国的策略性远见来运营他的基金会项目。正如博诺所说:“如果比尔·盖茨说可以在十年内根除疟疾,那么你知道他已经详细地调查计算过了”。作为音乐家,博诺和格尔多夫都深谙同大众的沟通交流之道。极少人像他们那样,能够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的关注点上。他们也积极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来接近世界最重量级的人物,获取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年轻、超级自信的电视厨艺明星和畅销书作者,杰米·奥利弗并没有满足和沉浸于自己的成功。他想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财富为社会做点事情。他在电视节目上唤起了英国公众和政府对于学校午餐健康的关注,证实了不必花很多钱,就可以提供既健康又受学童喜欢的营养午餐。他的“十五”餐厅(Fifteen)证明了完全有可能把无业青年转变为专业厨师。值得强调的是,他有这个自信把这些转变过程搬到电视节目上,并自己出资130万英镑,为项目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 英国的慈善家 我和妻子决定研究一下,这些名流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是否代表着一股更大的社会潮流。是否有很多这样的人,只是他们并未受到媒体的关注?这种现象只出现在美国还是已渐及全球?现在的英国,有许多人年纪轻轻或在中年就凭借自己的努力变成巨富,我们想知道这些人怎样处理他们的财富。 我们知道英国已经有一些活跃的、引人瞩目的慈善人士。大卫·斯伯利勋爵是最慷慨的人士之一。1967年,他用继承来的财产建立了“盖茨比慈善基金会”,他家族内的其他成员还成立了另外18家信托基金会。他最近宣布,自己打算成为第一个在有生之年捐赠10亿英镑的英国人,并委托盖茨比基金会在自己去世之前把全部资产和收入都花在慈善用途上。利乐包装公司的罗辛家族也因其常有创新之举的慈善行为而闻名。 这样的慈善人士还有很多。理查德·布兰森爵士最近成立了维珍基金会,并宣布他计划以后一半时间用来打理自己的维珍企业,所得悉数捐赠给维珍基金会,另一半时间用来从事社会公益活动。1994年,时装零售商季风公司(Monsoon)的老板彼得·西蒙在企业成立25周年之际,在其服装制造基地印度成立了印度妇女儿童教育基金会。越来越多的财富新贵们都成立了自己的信托会或基金会,部分出于税务原因,但同时也是掌控捐赠去向的一个方法。汤姆·法默爵士、迈克尔·格尔斯比、罗伯特·奥登爵士都把财产捐赠给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特蕾莎·劳埃德在《富翁为什么做慈善》一文中采访过的76位“高资本净值人士”中,有一半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虽然这些信托基金的许多捐赠对象都是新的慈善项目,他们还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创新慈善家。 不管是不是创新慈善家,近年来人们变得勇于展示自己的慷慨。纽约卡耐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瓦坦·格雷戈里恩会很高兴看到这一变化。她曾说道:“我喜欢人们公开宣扬自己的慷慨行为;如果我们看到谁在做慈善,大家就会更加踊跃”。另外,公开自己的慈善行为还会鼓励他人加入慈善行列。例如,美体小铺公司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在BBC上宣布了向她积极参与的国际特赦组织捐赠100万英镑的决定,并打算陆续捐赠5000万英镑。她说公开宣传自己捐赠的目的就是鼓励别人也来做慈善。艾尔顿·约翰爵士通过自己的艾滋病基金会资助了900多个艾滋病防治项目,仅在2004年就捐赠了1900多万英镑。摇滚组合平克·弗洛伊德的大卫·吉尔摩也公开宣布,把售房所得的360万英镑捐赠给“危机”慈善机构(Crisis),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住所。 体育明星也一直有慷慨之名,而且从来持公开态度。桑德兰足球队的爱尔兰足球明星尼尔·奎因把球赛奖金捐赠给数个儿童基金会;英格兰橄榄球队队长马丁·约翰逊把奖金捐赠给了癌症慈善基金会。尽管如此,慈善资助基金会(CharitiesAidFoundation)的凯茜·法拉奥估计《星期日泰晤士报》慈善榜上的前30名仅仅捐赠了他们年收入的1.2%,而美国的数字是13%。英国的慈善事业仍有待大力发展。 著名的私营银行顾资(Coutts)认识到了这一点,成立了家族企业与慈善事业部,协助私人客户创立有效的慈善策略。顾资银行的这一举动旨在帮助客户了解捐赠的不同方式,让善款物尽其能,使客户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满足感。顾资银行在全国组织了一系列慈善论坛,供慈善人士交流经验和观点,并有专业顾问提供指导。2005年,因其在慈善业开展的创新服务,顾资银行被《欧元》杂志评为“最佳慈善业服务银行”。一些私营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也推出类似服务,为有资金但缺少主意的人提供慈善规划服务。 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不是唯一的慈善服务机构。我们发现,英国新出现了一批名称里带有“慈善”一字的组织。一些组织致力于慈善业的研究和信息收集,例如英国慈善总会(PhilanthropyUK)和英国慈善学会(InstituteforPhilanthropy);其他组织积极地推广有效的慈善投资策略。这些都表明有组织有计划的慈善行为和服务正在日益升温。英国财政部也不甘落后,最近成立了慈善处(OfficeofCharity)和第三部门财政专署(ThirdSectorFinance),协助慈善捐赠的相关政策事务。几位退休银行家成立了新慈善基金会,利用自己的专业才能来研究最需要慈善捐助的领域,向有意捐赠的人提供捐赠方向和捐赠规划的建议。 “慈善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或者更准确地说,“捐赠创投”(venturegrant-making)是另一个从私人资本市场借来的做法,但投资者获得的不是资金收益,而是社会收益。捐赠创投与某个慈善团体保持长期关系,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人力支援。英国现在有6个捐赠创投机构,资金来源为私人投资者或基金会,它们向投资人选定的领域提供长期贷款或资金。Venturesome是这6个机构中的一个,它由慈善资助基金会于2002年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向90多个慈善团体投资了大约600万英镑。Venturesome与慈善团体合作,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还有,富翁俱乐部的富翁们在慈善上联手行动,以使捐赠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激励他人进行捐赠。社会变革协会(NetworkforSocialChange)和拥有40名成员的私人宴会俱乐部——蛇纹岩理事会(SerpentineCouncil)是其中的典范。另一个典范是本·戈德史密斯的马努卡俱乐部,其成员们联合起来支援环保事业。这些俱乐部实际上是投资信托基金会的一种。 在捐赠创投机构中,很少有几家能像ARK(AbsoluteReturnforKids)在筹集善款方面做得这么成功。它由几位退休银行家发起,宗旨是改变英国和其他国家,例如南非那些受虐待、残疾、疾病和贫困儿童的命运。在2005年的年度晚宴上,ARK一晚上就筹集了1100万英镑,每一英镑都代表一个匿名的捐赠小组。有一些ARK的会员还以个人名义捐赠200万英镑,在伦敦或伦敦附近建立政府倡议的城市学院。四所已经处于可行性阶段,另四所还在筹划当中。ARK教育分会协助建立学院的相关事宜,但几位会员自己也积极参与到其中。 另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捐赠创投人是斯蒂芬妮·雪莉女士。她是较早从事商业科技的企业家,于1962年创办了FI,即现在的Xansa。她为自己患孤独症的儿子和其他孤独症患者成立了Kingswood信托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为30个IT(她所在的行业)和孤独症慈善项目投入了5000万英镑。她说,她在慈善投资方面都非常讲求创新性和策略。 在这里,我们不想详细地探究英国的慈善现状。这方面英国已经有详尽的研究报告,比如马修·比肖普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全面调查,特蕾莎·劳埃德受英国慈善总会委托而做的报告《富翁为什么做慈善》,由顾资银行资助、英国慈善总会出版的《慈善指南》等等。从以上诸文,我们可以了解如今在英国富翁中新兴起的慈善潮流。但是,我们对于创新性慈善的调查和了解还不够多,我们需要寻找更多像比尔·盖茨和杰米·奥利佛这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慈善人士,他们创新性地进行慈善活动,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利用自己的才能和金钱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发起新的慈善项目,而不仅仅是向已有的基金会捐赠金钱。他们是理想中的“催化剂慈善家”,促使其他人改变了慈善的方式。我们试图寻找这样的慈善家,找到的比预想中的要多得多。 新慈善家“新”在何处?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宣扬这些“新慈善家”的工作和成就,另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其他成功人士向他们学习。我们相信社会变革的开端往往是新的行为榜样们开创了一种新的风尚。要做到这一点,这些新榜样们必须能够激起他人的共鸣,他们的个人故事必须精彩,他们也必须愿意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们很感谢书中这些同意接受采访和拍摄的慈善家。尽管有些人不太情愿,但是为了有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最终答应下来。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这些新慈善家是谁?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新”慈善家?他们做了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发现这些答案的最好方法是阅读他们的故事,但不妨先看一下有关他们的总结介绍。 他们是正当盛年的企业界或成功职业人士,已经赚够了自己需要的钱,现在想利用自己的财富、才能和技能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他们想改变和回馈社会,但不满足于仅仅给慈善团体写支票。他们想积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创新精神和商业才能,他们喜欢去填补空白,做别人忽略的事情。在英国,大家感觉到有一些领域政府没有或不能够照顾到,如果你有才能、精力和金钱,你应该挺身而出。一个受访者说道:“这样的慈善机会使赚钱变得有意义”。 我们需要新词。“慈善”(philanthropy)这个词让一些人感到不愉快,因为它还带有维多利亚时期“贵族的美德”、家长作风和不合实际的改良主义的意味。 一个受访者说:“请别说我是个慈善家,我只是想做个有用的人”。汤姆·亨特这些人则喜欢称自己是创投慈善家。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企业家”,但他们不必像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家那样去筹集启动资金,征求外界的捐助,他们可以给自己写张支票。 慈善几乎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新象征。拥有自己的基金会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楼是一种成功的耀眼标志。我们不应该嘲讽这种现象。如果社会地位是用慈善程度来衡量的话,这个社会将变得更好。但是,新慈善家们的慈善动力不是追求社会地位。他们在经过很多劝说之后才同意出现在本书中,免得有人误解,认为他们是在炫耀财富和善行。传统上,最受称道的慈善都是匿名的。本书的新慈善家们之所以不选择匿名,是因为他们关注慈善,因为他们知道做事情的成功之道,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基石。 他们是“新”慈善家,因为他们远远超越了以往慈善家写支票的老模式。他们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选择并亲身参与自己的慈善项目。他们是“新”慈善家,因为他们正当盛年,还有目标、激情和梦想,还有精力去开拓一番新事业。他们不想在身故之后才把遗产用作慈善用途,他们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慈善基金发挥作用。他们是“新”慈善家,因为自从维多利亚末期以来,除了极少几个例外(例如斯伯利家族),英国没有一个能够催生巨大财富的企业家阶层。英国社会在上个世纪的主体成分是公营和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即使有心慈善,因为积蓄有限也无法进行大额捐赠。只有最近以来,一些高薪高奖金的专业人士才有了大笔捐赠的能力。 这些新慈善家起了很重要的典范作用。他们的创新才能、敏锐的商业头脑不仅给社会企业带来了财富;通过帮助他人,他们还填补了自由企业制度所缺少的社会公正性。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他怎样赚钱,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怎样花钱。这些新慈善家们花钱有道,也乐在其中。正如艺术商人和资助网(FundingNetwork)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穆尔德博士所说:“用自己赚的钱去资助我认为值得做的事情,是一大乐事”。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些新慈善家们或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人指责他们未做充分调查或不了解慈善项目的更长期需求就仓促上马。他们可能会闯入一些老资格的慈善团体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的领域,遭到忌恨。为了尽快实施慈善项目,新慈善家们可能会忽略办事程序、抄捷径、惹恼当地官员,或大肆批评政府制度的缺陷。扬氏基金会的理事长杰夫·穆尔甘指出,深层的社会变革不是几个鼓舞人心的项目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它通常需要社会心态、社会运动和市场的联动转变,以及政府的参与。但是,星星之火的出现不可避免。我们的受访者说,他们很清楚这些问题,会尽力与领域内的其他人和相关官员合作。他们认识到,要使他们的慈善事业产生久远的影响,他们必须最终融入到大环境中,要积极利用所有资源。 激情、持久力和合作 书中23人的性格及其他们的慈善项目都差别很大。有人内向,有人外向。有些人的慈善动力是信仰或宗教感情,有些人是社会责任感或仅仅希望帮助别人。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激情、持久力和合作。
不奉献大量的精力,任何项目都不会成功。好点子,甚至精心研究的商业计划书都远远不够。但是,如果有了激情,就可以面对所有问题,可以忍受全部困难。如果尼尔·梅隆不是那么醉心于他的居住计划,他不会一月两次往返于都柏林和南非。如果杰夫·甘比诺对他的慈善事业没有激情,他不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每天为400人做晚餐。如果彼得·兰普尔没有下定决心结束他眼中的英国教育隔离,他不会把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他的教育基金会。他们都对自己的慈善事业充满激情。他们奉献,不是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更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奉献,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信奉的理念充满激情。 通常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引发了他们的激情。彼得·兰普尔回想起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因一项慈善举动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从此认识到一个人能够改变做事情的方式。大卫·查特斯在一个周末醒悟到由于他太沉浸于工作,以致于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天晚上,克里斯托夫·普威斯在一个信封背面计算出他已经赚够了整个家庭需要的钱,从此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保姆可怕的乳腺癌治疗经历促使莎拉·达文波特着手成立基金会,虽然这意味着她必须卖掉自己心爱的画廊。拉姆·吉多摩尔在孟买的经历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安排。 一天上午,有人打电话给汤姆·亨特,提出用一笔足可以使他消除后顾之忧的金钱购买他的公司。他开始考虑如何安排自己以后的生活,因为他当年只有37岁。其他人,像杰夫·斯克尔、迈克尔·德·乔吉奥和克里斯·马提亚斯在卖掉自己的企业后,都思考过相同的问题。他们很幸运,都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慈善项目,意外的机会或问题促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如果这些事没有发生,他们或许会满足于成立一个家庭信托会或基金会,只向申请者提出资助。这样做本来也无可非议,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但这样,就没有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创新慈善项目了。要做慈善事业的催化剂,必须有激情和源自激情的奉献精神。 新慈善家都是成功人士,大多数来自商界,有很多人仍然保留着些许对商业的兴趣。他们用商业眼光看待自己的慈善项目,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投入资金、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很清楚,这些慈善项目到最后必须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独立、持续地运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持续向项目提供资金,被这个项目绊住,不能发起其它的慈善项目。要使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则这个影响力必须是永久性的,能够一直延续到他们去世之后的很多年。 有些新慈善家考虑周全,建立了另外的资金来源渠道。杰夫·甘比诺在悉尼新成立了一家盈利性企业,专门为自己的慈善项目积累足够的资金,以防自己的钱用完或自己身后资金不继。莫·易卜拉欣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乳腺癌诊所大楼有7层楼,其中6-7层将出租为豪华办公室,租金收入用来维持诊所将来的运转。戈登·罗迪克规定他投资参与的几个社会福利事业必须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达到收支平衡,他密切关注这些事业,确保它们达到他的目标。 但是,慈善项目的持续性发展最终要依靠某种合作。其他人必须对项目真正感兴趣,否则在原主办人和投资人离开之后,项目常常难以为继。要使慈善项目永继发展,必须在合作方面更上一层楼。这往往需要跳蚤与大象进行合作。跳蚤虽然是个人或小团体,但远比大象们具有创造力和实验精神。然而跳蚤需要大象来协助运转项目。在所有领域内,大象都鲜有创新之举;另一方面,跳蚤人少力量也小。英国在商业的创新和发展方面表现不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创造力丰富的跳蚤和高效、资源丰富的大象之间缺乏合作。做的最好的新慈善家知道这一点。 彼得·兰普尔在剑桥大学组织并资助了第一个暑期学校。他不仅与剑桥合作,还特意邀请了当时的教育大臣大卫·布兰基特参与到项目之中。现在,教育部和英国的60所大学合作开办了60所暑期学校。他曾说:“项目在一个地方试点成功之后,我们即与政府紧密合作,在政府的协助下在全国推广,并获取政府的资金支持。”汤姆·亨特很高兴他在苏格兰投资3500万英镑的教育实验项目获得了政府1.75亿英镑的资金支持,把他的教育实验推向了全国。 如果没有南非当地及中央政府的帮助和参与,尼尔·梅隆的项目将远远小于现在的规模。南非政府提供了基础设施、把租金合法化、为房屋提供津贴。他招募的爱尔兰志愿者也纷纷为项目筹募资金,负担自己的往返住宿费用,所以这些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作者。合作带来的是积极的参与、奉献和长久永续发展。 彼得·赖安最初在马拉维推行小额贷款项目时,邀请了英国当地的宗教团体一起监督项目的进行;在项目有所起色后,英国政府也应彼得·赖安的请求,成为项目的投资者之一。托尼·福根斯坦在教育方面的实验项目自然需要与学校和大学合作,但是他还争取使这些项目获得政府的资助。调动资源从来都是关键的一环。 我们希望这些新慈善家能起到间接的带动作用;希望他们的故事能给别人带来启发和鼓舞。我们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一定在思考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希望这本书能给他们提供些许启示和鼓励。 (本文是查尔斯·汉迪和伊丽莎白·汉迪夫妇合著的《新慈善家》一书的序言,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