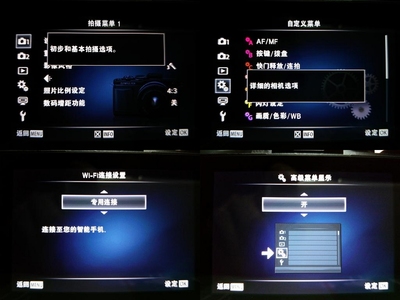如果说诗歌是阿巴斯电影的延续与再创造,那么摄影就是阿巴斯电影的源头与母体。
撰稿/春秋
2008年1月26日,伊朗籍国际电影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Kiarostami)来到中国北京,其摄影作品会在北京皇城艺术馆展出。至此,为期1年3个月的阿巴斯综合艺术成就中国巡回展将画上完美句号。之后,阿巴斯的作品将离开中国前往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继续展出。 电影:“看似不可能的里面有时又有着一定的可能性” 作为仍然健在的世界级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成就世人共睹。1997年,凭借电影《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获得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导演戈达尔说:“电影始于格利菲斯,止于基阿鲁斯达米!” 在伊朗,电影是件“危险”的事情。一如阿巴斯本人当年获得了金棕榈奖时遭遇的情形——颁奖时与凯特琳娜·德诺芙的一个拥吻使他不得不在外国“避一避”。因为公共场合向异性表露情感以及身体接触在伊朗是大忌。 银幕上,伊朗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遮住头发,穿宽松的袍子遮盖住身体的曲线,男女间亲密的行为只允许发生在夫妻间。银幕上的女性永远不能看到暴露的头发,即使在其私人的房间内,而扮演夫妻的演员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真实的夫妻,那么他们违法了……诸多类似的限制使得伊朗的电影导演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出路——象征、隐喻、以儿童故事为素材折射成人世界…… “但是看似不可能的里面有时又有着一定的可能性。”阿巴斯说。 一如阿巴斯在他的电影中熟练运用的技法:在《橄榄树下的情人》结尾处那个著名的全景镜头里,阿巴斯将“做爱”处理为两个瞬间接触的黑点,消失在广袤的自然间,勾联于想象与象征。这是阿巴斯的技艺,他以“最微小的总和展示了情色”。出人意料的是,在某些场合,阿巴斯竟然捍卫伊朗苛刻的电影审查制度!他说道:“真理有很多纬度,所有的谎言都拥有真理的成分。” 当某些影像在阿巴斯的电影中被遮蔽掉时,另一些可见的影像却奇妙地开始演变为一种权力——所有的电影人都必须服从限制来拍摄,此后产生的图像成为激发人们产生无限想象的工具。那是“使全部假象进行增生的电影,它所追寻的,就是朝理想化进行永无休止的奔跑”。 少量的几个人物、线性叙事、作为背景的日常事物,阿巴斯的电影画面甚至可以用“简单”一词形容,但阿巴斯的简单之中孕育着深刻的内涵以及众多的阐释路径。在他看来,简单蕴涵着丰富。正如阿巴斯最欣赏的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一样,小津的电影正是简单而深藏哲理的,而他开放式的拍摄让观众体会到了观看的自由。 阿巴斯以自己的方式向他崇敬的电影先辈致敬,于是,就有了长达74分钟、只有5个长镜头的《五》。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阿巴斯说:“这5个章节是在我脑海里自然而逐渐地产生的,我没有剧本,每一段拍摄都花了些时间。尤其最后一段,为它我去了五六次外景地,因为一个月里只有两天是满月。” “我的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创作。我也从未受过什么特别的影响,一切故事都来自我的生活。” 诗歌:“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都需要诗意” 对于阿巴斯来说,任何人类创造性的劳动都可能成为他的兴趣爱好,比如:写诗歌、做一名木匠。这位不论白天或是黑夜都戴着深色墨镜的伊朗人谦虚地说这一切不过因为电影也是他的“副业”之一。 在那册并不厚的阿巴斯诗集《随风而行》中,我们感受到阿巴斯远离尘嚣的心灵。一首首俳句式的简短句子勾勒出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在他直接而具体的书写里,一切具象化的事物焕发出厚重的意义——阿巴斯电影式的人生思考与困惑。其诗歌衍生出的连带意义辐射出阿巴斯的生存背景以及他植根的文化土壤。 “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不见/回到雾里”——世事无常不断变换,幻象与实象交替更迭;“火车嘶鸣着/停住/蝴蝶在铁轨上酣睡”——大反差的不和谐美;“春风不识字/却翻作业本/孩子趴在小手上/睡得香”——日常事物,真实美景;“土路尽头/融进阴霾天际/几个雨点/掉落尘埃”——不受干扰的孤寂自然…… “我必须要说的是,很多人在表达艺术的时候是没有诗意的。但我认为诗意对艺术表达非常重要。而且,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都需要诗意。” 阿巴斯的“诗意”是东方式的。在他的贴着骨子里生长的东方情怀里,东方人的隐忍与顽强显得更为重要。 在诗歌《越想越不明白》中,从最初问“雪为何如此的白”到“为何一无所获者手上,尽是老茧”,它直接延续了阿巴斯电影中直抵现实生活的真实。雪、蜘蛛、狗、母亲、一无所获者是真实世界里的坚忍;洁白、秩序、威严、忠诚、爱、老茧是真实世界里的顽强。但阿巴斯却采用了一连串的疑问句式呈现种种真实,直接导致这种引入的怀疑如同病毒一般蔓延在严谨的真实程序里。以致真实的意义被彻底颠覆! “我对世界有诸多的疑惑,这些疑惑刺激着我的创作。虽然我拍过不少电影,但电影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为电影也有局限。我澎湃的内心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平静,比如,诗歌、艺术、哲学。 “对我来说,诗歌是暗室里的光亮,它照亮我的内心;诗歌是抑制痛苦的止痛药,它让我重获内心的平静。我相信,无论是电影,抑或是诗歌,那份能打动我的深刻的情感也流淌在你们的心间,因为那是你我共同的部分。” 摄影:“影像是万物之源” 如果说诗歌是阿巴斯电影的延续与再创造,那么摄影就是阿巴斯电影的源头与母体。“我认为影像是所有艺术之母。我之所以被电影吸引,应该说是因为影像总是让我着迷,并不是因为电影是一种更完整的艺术。每种艺术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摄影也是如此,它有自身的特殊功能和地位。” 在阿巴斯看来,摄影是一种基本需要。通过摄影,他学会如何观察世界,使得“自己内心积累影像”,懂得取舍,并且“理解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意义”。 “影像是万物之源。我经常从一幅内心影像开始写作剧本,也就是从存在于脑子的一幅影像开始建构和完善剧本的。” 零星的一两个人点缀在天空与路的尽头,又或者是一条在大山身体上凿出的蜿蜒曲折的路,再不然是大片云朵仿佛匍匐着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前行……这些是阿巴斯带来的题为“路”的系列摄影作品。 现场银幕上不断回放着阿巴斯的《基阿鲁斯塔米的道路》。在影片的旁白里,阿巴斯说道:“我也说不清,‘道路’这个主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可以说:是从我开始摄影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是‘道路’。我只知道,有一天我发现,过去25年来零散拍摄的照片里,竟已有上千张是道路、车辙、曲径。我想这些照片的根源要回溯到童年时代,我对路的迷恋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的电影里,也总是下意识地出现很多大道或小径的镜头。一个很确定的事情就是这些道路承载着从过往而来的记忆。它们象征人类未经记载的寻觅,对生命的寻觅。也许是感伤的,也许只为一口食粮,道路上就画下杂乱的线条……” 展厅四壁挂着的“路”系列作品采用了阿巴斯最爱的黑白两色极简主义摄影风格拍摄完成。阿巴斯认为:“黑白摄影在某种程度上比彩色摄影更接近艺术。在一个更大的艺术发挥空间里,所有人能同时面对真实与虚幻。” “人类的眼睛不是只识黑白——彩色摄影里黑白也被其它颜色覆盖或者转化,尤其是在拍摄雪景的时候,彩色摄影里的雪都变成浅蓝色,我不喜欢。”
除了忙碌的巡展活动,阿巴斯最近还在执导一部歌剧。“这比做电影轻松多了。”阿巴斯开玩笑地建议所有电影导演,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尝试做一次话剧,“因为这实在太好玩了”。(本文图片选自阿巴斯诗集《随风而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