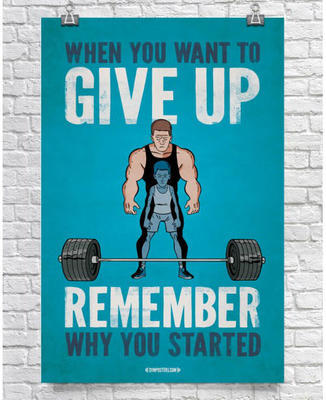西方近、现代史没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虚拟的布景和舞台上选好、安排妥定的演员。
撰稿/边芹 旅法作家

有一些作家就像时代面汤上的油花,经不起死亡的搅拌。一次都经不起,不要说作品一旦越过生死界,便只有一个命运:在一代一代的死亡漏勺上逃生,像赌博一样看谁能在牌桌上多坚持一分钟。 时隔三星期,文坛出了两件事: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欲死而复生。于连·格拉克,小说家、随笔作家,97岁,老死;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的情侣,诞辰100周年。观察两个死去的人透过传媒的词语再度显现,我惊叹存在过的那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后来人怎么看他们。而怎么看他们,有百分之八十取决于他们活着的时候“炮制”的故事,只有百分之二十来自他们的文学才华。这样一来,格拉克就大大吃亏了。他一生没有“故事”,主张人生尽可能消失在文字后面,所以一辈子躲在法国外省小城,拒绝与传媒打交道,唯一足以让后世嚼舌头的举动,是1951年拒绝了“贡古尔奖”。但这么一件“壮举”,加上寿终正寝式的死亡,报纸、电视两天就没有话题了。再看波伏娃,与萨特的情人关系是不尽的话题,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抖出的“谎言”越来越多,但重要的显然是“占领空间”,成为话题。在广告比文字本身重要的时代,文人已经自动缩短了寿命。这一次百年诞辰,除了“神话”和“神话破裂”这些传统的炒卖手段外,又多了一招——现代传媒的最后一招:脱衣服。《新观察家》登了她一张露出整个后身的裸照。我看了,得出结论:肉身和文字可以完全脱离,没有把它们连在一起的理由。肉身之不再神秘,是人类思想死亡的前兆。她有着匀称的身材,从肩背到臀部以上的线条,完全是亚洲女人的。忽然问自己她扛在肩头的“女权运动”在多大程度掩饰了这脆弱的线条?那呈现给世人的潇洒浸透了多少心酸? 关于这个女人,我写过不少东西,越是不知究底的时候,越敢下笔。到了今天,当我穿过层层封锁——文字的、历史的、阶级的、种族的、禁忌的,真正游进这个文化的酱汤,我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仿佛被邀去看人家一手导演的戏剧,只看见人家想让你看到的东西,而且居然毫无异议地相信了。西方近、现代史没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虚拟的布景和舞台上选好、安排妥定的演员。两百多年,真正的统治者始终都在台上,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的版本,你可以想象。篡改文明的轨道,居然把新版本变成一种宗教,让被改造者都坚信不疑,真是天大的手笔!这样看来,波伏娃不过是被挑中的演员,只在某一历史时期起领头羊的作用,她的女权榜样,是旧文明消亡之长跑的起跑线之一。她在文学史上究竟有没有价值,还要等一百年,甚至更长,才有可能测量。因为19世纪以来,连文学史也未逃脱利益集团的棋盘。 我那天在电视上看着她身穿粉色羊毛小套服面对镜头走过来,几秒钟的时间,一切都变得清晰,她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我自以为了解她,将已经不是事实而是文字构成的“事实”,一层层揭开翻下去,但我慢慢看出,如果每一个细节都跟出版商的利益、某一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宣传、某个族群攫取权力的需要密而不分,你已经永远无法知道完整的真相。因为现今以“真相”的名义要打碎“圣像”的运作,与当年要竖起“圣像”的炒作,目的如出一辙。这一对文坛“情侣”为他们的“不真诚”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又为他们的真诚将丢失很多。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新征服者投向旧体制的两枚铅球。我曾经拎出的那些“真相”,构筑了我作为“卒子”的命运。而卒子的命运是个接力棒,两百年来就在中国文人的手上一代代传递,直到本文明完全褪色,我们也就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我也是到了西方多年以后才发现,“文化投机”到了掩盖真相的程度,电影、文学的质量标准,被商业利益、族群利益甚至意识形态取代,而这一切又是以市场规律操作的,外表天衣无缝。当制片商、电影节、影评人、电影奖、发行商、电影资料馆全部控制在一个族群手里,同样当从出版商到文学奖乃至书店老板、公共图书馆,也在一小撮人手里,平衡和真实就消亡了。 波伏娃在她的小说《女客》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她自己的生活更真实。”我要加一句:但那是说不出口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