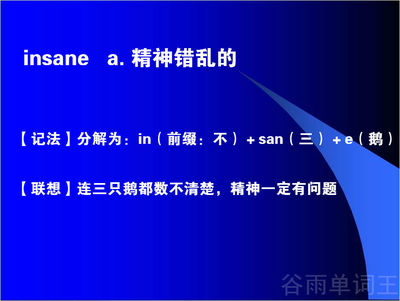我只对错误的地方感兴趣,我把那些错误的地方记录下来,然后把各种各样的错误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片段,因为我觉得那些错误的地方,是更真实的反应。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创作是主题先行,还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阿库·汉姆:到了我和演员们合作的4周后,我才想到了身份问题。剧组成立时,我只是在考虑,如何把这9个陌生个体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第一天,我和9个演员一块儿到排练厅开始合作。他们有的是当代舞演员,有的是芭蕾舞演员,有的是印度古典舞演员,下意识带着警惕的姿态,很容易就显现出“你这些东西我熟悉,那些东西不熟悉”。我不想让他们感觉别扭,于是就让他们把自己当做是普通话剧演员,处理一些剧情上的关系。合作进行两周后,我渐渐开始了解他们的心思,我发现,中国演员有些忧愁,他们好像特别想家,这让我联想起自己的情况。所以问题来了:我的家在哪儿?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地理上的故乡,还是代表着身份认知?这些都通过舞蹈提了出来。还有就是作为舞蹈演员,我们经常去各地旅行,我们在心灵上是否可以有一个家?我又问我的舞者,如何和家联系。他们有的是通过手机,看到他们对电话那么当心的样子,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在当代生活中,是手机控制你呢,还是你控制手机。于是在这段舞蹈中就加进了中国台湾女舞蹈演员对手机的独白。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编舞的? 阿库·汉姆:说老实话,你们看到的动作,实际上不是我,是演员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只是给他们一些引导。我还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单纯模仿我给的动作,就是二手货无疑。我跟他们谈了很多,每个人对家的概念都不一样,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人发生联系。我开始是创作一个片段,然后慢慢地发展内容,到最后再合起来。我会用一些即兴发挥,教舞蹈演员一些基本技巧,然后我走开,给他们两小时的自由发挥,我再从头看录像,从中寻找感兴趣的动作。有时我让他们必须照某种方式跳,我把速度加快,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犯错。基本上,我只对错误的地方感兴趣。 排练时,我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演员,然后让他们的特点在舞蹈中发挥出来。比如中国台湾的女演员,她曾经是“云门舞集”的舞者,后来离开了,我马上问她,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剧团?因为她表演时的爆发力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很吸引我。在来到我们团几周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平时总爱躲在钢琴后面。直到我了解到她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阴暗的童年,所以她表现那种紧张、激烈的情绪很到位。孟宁宁和人说话怯生生的,但后来发现她其实很自信,所以她那个角色是渐渐飞扬起来的。王艺潼人很阳光,但经常迷迷糊糊的,这使得她的那张脸很可爱。我就给她设计了那段双人舞,从始至终她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和恋爱的主题蛮符合的。 三联生活周刊:与你合作的很多艺术家都很有名,你与他们合作的原则是什么? 阿库·汉姆:我最长期的音乐合作伙伴是尼丁·索尼,我们合作已经有7年了,刚开始时他还寂寂无闻,现在他也是个明星了。我们的合作,一般都是我先到他的工作室,我们会有很多交流,我给他我的想法,还有排练的录像片段,他的反应总是特别棒,因为他对什么都有反应,色彩、灯光,还会给我对剧本的建议。我也被他的世界音乐所吸引,这次创作《相聚》,我们兼收并蓄了南非、西班牙,还有中国的音乐元素。 但不同代的人对合作的要求不一样,我和一位60多岁的当代作曲家第一次合作,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你的音乐请允许我给些建议,我也希望他能对我的舞蹈给出建议。”结果他在酒店大堂把我骂了15分钟,说,“我给你音乐你就去编,我信任你,但是我不允许你踏入我的领域半步!”也不是所有上年纪的人都这样,我和约翰·凯奇(JohnCage)的合作就非常好。2009年,我和谭盾还有个合作计划,我去看他的排练,他非常谦虚地问我,你觉得这个背景怎么样,那个服装怎么样。他是那么开放,那么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我很期待和他合作。 我最近合作的一个人,是法国电影明星朱丽叶·比诺什。她到我的排练厅来,我们先讨论谁说了算,我先教会她一些动作,这一天排练完了,她脸色就很难看。她说:“你老告诉我干什么,还要我来干什么?”她说,“我们明天从头开始,我们互相不许教东西。”第二天,我们的排练就什么接触也没有,我按照自己的方法活动,我问她干什么呢,她也问我干什么呢,我问她你是在模仿我么?她也说你是在模仿我么?我做什么她就模仿什么,我就很崩溃,后来我说回家吧,她也说回家吧。不过对我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我一直在探测别人的边界在哪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