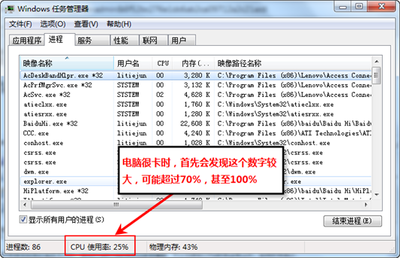孙甘露专访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撰稿/河西(特约记者)
孙甘露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80年代,带着澎湃的诗情和忧悒的哲人气质,他以先锋派的姿态进入文坛。自那之后,20年,他坚持着独特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毛尖说她最怕她的学生写研究孙甘露的论文。毫无疑问,孙甘露的作品是先锋的,他质疑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动摇了根深蒂固的文学接受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不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是,他的身影似乎有些孤单。他的写作是绝对的,不同凡俗的,同时,90年代之后的巨变让他对写作产生了一些怀疑。孙甘露,8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零星发表的小说、随笔和诗歌中维持着人们对他的期待。直到近年,随着长篇小说《少女群像》片断和作品系列的出版,孙甘露才给人以春蛰之后冬眠初醒的感觉。 12月16日,由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作协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孙甘露和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孙甘露作品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在同济大学见到他,一身黑色,显得很精神。他很健谈,但是并不张扬,他说他只赞美他认为好的事物,很少去批评他人。更多的时候,他选择静静地聆听,直到和你面对面地谈起文学,他才会敞开心扉,与你坦诚相见。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北岛说,他的作品给人感觉很冷是因为童年,孙甘露的情况是否相似?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童年谈起。 早年记忆 新民周刊:您的少年时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当时是否也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绘的那样,过着一种非常态的幸福生活? 孙甘露:没错,王朔比我大一岁,基本上那个年代背景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我父亲是军人,隶属于空四军地勤部队,我们家也没有随军,就在地方上,住在部队的院子里。后来我父亲去援越抗美,小孩就是放羊式地生活着。很巧,我1966年进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好我都在上学。小学6年,中学4年,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文革”结束那年我毕业,学工学农,各三个月。学农在崇明,睡在猪圈改建的宿舍里,我记得天很冷,就在这时中央粉碎“四人帮”,我们还在学农的地方刷标语,一个时代结束,我的学生时代也结束了。 新民周刊:北岛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食指的诗歌,接触到一些地下文学,当时您在上海有没有这种情况? 孙甘露:那时候我看的主要是家里或朋友留下的书籍,四大名著、苏联小说与《红与黑》等等。我母亲和外公都是老师,所以还留了一些书,虽然我们都比较害怕。我记得我母亲还被游过街,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然更多的是革命小说,《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诸如此类。也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比如雪莱、海涅的诗集,繁体字,有横排有竖排。还有很多没头没尾的书,看得人太多,给翻烂了。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时真的是如饥似渴,拿到一本书就看。写作的兴趣都是从阅读来的。 新民周刊:这应该算是您最初的文学记忆,您真正喜欢上写作是什么时候? 孙甘露:真正喜欢上文学,那应该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出版,包括翻译小说和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另外坦率地说,其实“文革”时的样板戏、《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丛刊、“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飞雪迎春》、《沸腾的群山》和“文革”前出版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阅读体验,培养了我对叙事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毕竟年龄小,并不能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苏俄文学,什么是法国文学,什么是“文革”文学,没有那种概念,就觉得它是小说。特别是英雄故事对于男孩子来说,会让他产生一种幻想。当时它们影响你的方式,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而是建立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上,它是混合的经验,你知道的只是:它是一个读物。 新民周刊:您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主要做些什么?和后来发表的小说《信使之函》有关系吗? 孙甘露:我中学毕业后分配到邮政局,在原来的人民公园附近。那时我19岁。邮政局当时很难进。当时的情况是多子女的家庭,最大的孩子要下乡,所谓的“一工一农”。但是由于我父亲刚从越南回来,出于照顾,把我留在上海,但不能进工厂。我先进了邮政局的技校,读了两年,毕业后正式去邮政局上班。如果我下乡了,我大概就成了一个知青作家。 《信使之函》是一个幻想性的作品,从文学意义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附会。但是如果你说完全和我的经历没有关系,好像也有点。我在邮政局什么都做过,送信、送电报、送报纸、卖邮票,凡是邮政局里有的活我差不多都干过,从1979年至1989年,前后十年,直到我开始写作进入作协工作为止。 踏入文坛 新民周刊:您早期的作品中诗歌的痕迹很重,但您却说您一开始就写小说。 孙甘露: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诗歌和小说我都写,交叉着写,小说方面我一开始写作是写小的故事。除了《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中国古典诗词,最初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涅的《歌谣集》、查良铮译的雪莱的诗集以及一本莫洛亚写的《雪莱传》,它们对我的文风有一定影响。这些译本文字非常漂亮,近乎华丽,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的句子:“我的飞翔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要往那金星落处的天空求那灿烂的死”,太漂亮了,特别我当时那么小,马上就把我征服了。 然后再接触到歌德、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文革”之后再要阅读小说就变得很容易。 新民周刊:您刚刚提到的都是古典主义的作家,现代主义的作品对您产生影响是在什么时候? 孙甘露:其实当时绘画对我的影响更大。我还去学过素描,在中学的后期还和一个美术老师学画画,可是我画具象的形体是永远都画不准的。8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绘画大展在上海展览馆举办,来了很多原作,那次对我影响很深。 我最早看到的美术作品是哈定的水彩画,他是上海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彩画家,古典画风,画街景,从此开始对风景画感兴趣。当然当时看的大部分都是画册,然后渐渐地接触到印象派。再后来就像阅读一样,完全开放了。 这些绘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我观察事物的态度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都发生了变化,以前接受的都是非常形象化的、古典意义上的叙事。对于艺术史的理解也是如此。你理解的艺术史是从圣像这样一个宗教题材一直到民间世俗的绘画,从皇室到平民,从风景到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发展脉络。但是当你看到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的时候会非常震惊,以前对绘画的概念是风景和人物,是具象,现代主义绘画将既有的观念完全颠覆了。 其实当时我对音乐、绘画、诗歌的兴趣要超过我对小说的兴趣,这也很正常,因为一方面是青年的求知欲,另一方面则是官能冲击的直接性,它们都要比小说更为有效。是它们铺平了我之后接触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道路。 新民周刊: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议题是“孙甘露与85新潮”,我不知道您和先锋美术之间还有什么关联? 孙甘露:从今天来看,我是这个大范畴中的一分子。当时有许多前卫艺术作品在文学艺术界传播,白洋淀和今天派的诗歌也已经能够看得到,整个氛围是现代主义当道,文学、绘画、电影、建筑,都开始深刻地变革,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我和85新潮之间存在着一种纽带式的关系。 我最初写《访问梦境》是在1986年3月,发表在同年9月,但写作的准备肯定在1986年之前。其实我一直在写一些诗歌和很短的故事,但很难在杂志发表。1980至1985年这6年时间,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潜在的准备,不断地学习和写作,只是不被社会和公众认同。 任何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每一部作品都会遇到一个准备期。一个作家并不在他发表作品的时刻诞生,他早就存在。
新民周刊:当时在上海,您是孤独的写作者,还是有一个朋友的圈子在互相激励? 孙甘露:也有一些朋友一起讨论文学和艺术,但能坚持到现在的凤毛麟角。我有一个邮政局技校的同学,现在完全是一个官员了,当时他也是很热心的文艺青年。有的出国,有的做生意,有的去研究物理,他们多多少少都写过一些。我觉得每个人在青春期都是诗人,但要将其作为一生的职业,面对你小时候不曾考虑过的生活的压力,要将你的兴趣、志向和梦结合在一起,那太困难了。 新民周刊:马原老是说他最初十年小说没办法发表,我不知道您最初的小说发表是否也非常困难?1986年您的《访问梦境》是怎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 孙甘露:《访问梦境》之前我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一共二十多篇,但很可惜,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把它们全部烧掉了。我的一个技校同学认识作家薛海强,将我的作品拿给他看,他就将这些作品推荐给《上海文学》的编辑杨晓敏,他就觉得这些作品很特别,但是这边发不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挫折,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和写作前景都比较悲观,就觉得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不必再持续下去了。 1985年底1986年初,忽然有一天,杨晓敏把我叫去,说上海作协要办一个青年作家讲习班,问我愿意来吗?1986年3月我就去了。一共3个月,大多数时间是讨论和讲座,请了许多作家,我记得其中就有李陀和韩少功。结束时要交一篇作品,文学样式、篇幅不限,我就交了这篇《访问梦境》作为作业。据我后来所知,杨晓敏将这篇作品交给李陀看,李陀看了觉得不错。当时丁玲复刊《中国作家》杂志,李陀给了《中国作家》,都下厂准备印了。这时周介人把这篇小说重新拿回《上海文学》,说这是上海的作者,还是应该在上海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争议,有人就觉得看不懂,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完全不同,但是周介人坚持要发。如果他不坚持,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新民周刊:当时有没有想过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响? 孙甘露:这绝对是我始料未及的。而且我听说周介人在发表这篇小说后也受到一些压力,他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一封致我的信,信的名字叫《走向明智》,对我的创作提出一些建议。现在看来,这封信也是解释给其他人看的。 我和上海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想过自己拍电影,有没有想过将自己的小说搬上银幕? 孙甘露: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但那是很可怕的记忆。年轻时候有幻想,想自己拍,后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年龄越大越不可能。电影是个体力活。当然,看电影的兴趣一直都在。 如果有导演能看中我的小说,将它改编成电影,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但那要靠机缘。你看张爱玲5000字的《色,戒》给李安拍成了这样一部电影,你不可想象,换了一个导演就会变成另一部电影。如果说看电影是幻想,那么拍电影现在已经超出了我的幻想。 2003年,央视给我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上海:孙甘露此地是他乡》,我写了脚本,是关于我对上海看法的纪录片。我看了以后很震惊,我觉得导演韦大军他很了解我,这个作品最终获得了该年度最佳纪录片奖的最佳导演奖。地域当然有差别,但它是相通的。如果有一个导演能理解作家,他就能将作家的文本作品拍成影像。 新民周刊:您一直住在上海,您写过《上海流水》、《上海:时间玩偶》,上海这座城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除了旅行和参加活动,我没离开过上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我说过这样的话:上海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结果被记者写成“上海是我的世界”,意思就不准确了。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我接触到的世界就是上海。我的经验、我的感受、我的感官,从日常角度来说,它们所面对的首先是上海。 新民周刊:说到上海,不能回避现在已贴上上海标签的张爱玲。但张爱玲的小说和您的小说是完全不同的阅读经验。您觉得张爱玲的女性都会叙事和您的形式实验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还是个人写作的趣味所致? 孙甘露:张爱玲的小说我读过一些,但和那些张迷不同,我对她不是那么着迷。我对她写作的故事有兴趣,但对她的文体我不是太喜欢。我对她的印象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的印象其实相差无几,从鲁迅开始,那个时代讲话的方式和现在是有距离的,我不太能接受。我欣赏不了它的妙处。当然,现代文学史上也有我很喜欢的作品。所以我说地域对作家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比如翻译作品就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现代和当代的翻译家,对当代汉语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敢说他不受翻译文学影响。懂原文当然最好,但涉及到的语种太多了,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语言都学会。 有人提出翻译的作品不能成为写作的直接资源,我不太同意。举一个例子。叶芝的诗歌写作深受希腊民间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不懂希腊文,他看的也是翻译。叶芝认为各种语言的诗歌是相通的,不必一定去学习原文。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中的人物原型阿兰·布鲁姆,也就是《开放的美国精神》的作者,他研究柏拉图、莎士比亚和卢梭,他在考证另外一个译本时举了个例子,一个从拉丁文译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作品本子,甚至成为希腊文手抄本的错误的订正的范本。译文成为原文的范本。正是根据这些译本,阿奎那建立起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典范。 另外,我们之所以会喜欢翻译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它提供的现代都会经验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验方式和态度也以农业社会为主。他们的时间观念、叙事方式都受到农业社会的限制。 地域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巴黎很远,但似乎并不比北京更远。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学被边缘化了。翻译文学被大量引进,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阅读厄普代克、菲力普·罗斯、库切、奈保尔、艾柯、拉什迪?他们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事。杜拉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新小说派那么多作家,其他的作家有多少人在阅读?这也是一个传播的问题,传播的渠道和阅读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