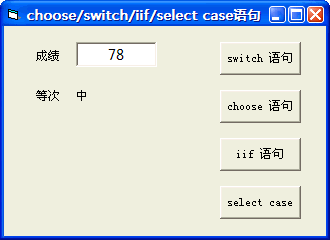历史是一面镜子,但万物都是镜子,如果我们把它举起来并透过表面凝视它。我们从事于研究、阅读、思考,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更好地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联。
文/江素云
卜正民(Timothy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鸦片政权》、《民族行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等著作。 卜正民从印着“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布袋子里拣出一张卡片,报出一串英语单词,跟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核对完词义:神操、原罪、伊斯兰教法……走进复旦人文讲堂。底下,历史系、哲学系和法学院的学生已坐满,窗台上靠着几个白T恤。这天,讲的是“近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凌迟”。 前一天,他向复旦学生展示的是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一周前,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展示的30多张中世纪以降的世界地图,也多少透露了这位明清史研究者的视角。而在他已译成中文的三部著作中,可以进一步发现他对县志和学者笔记的偏爱。 卜正民讲完“千刀万剐”,朱维铮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有阐发。当他用上海方言发出“杀千刀”三个字时,卜正民眉眼一动,立时记在卡片上。跟那些已经和正在翻译他英文著作的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一样:语言,是深入另一种文化与思想的布满荆棘的小径。 在来中国之前,卜正民有过两年的汉语准备,其中包括一年的文言文学习,然后就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早在中国恢复高考的1977年之前,他先后走进了北京和上海的大学。 70年代留学生 1973年,疲惫的中国正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那一年,中国足球队频繁出访比赛,人们认识了一匹从中场杀出的黑马容志行;那一年,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那一年,跟随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玛格南图片社会员布鲁诺·巴比拍下了王府井和苏州街道上的色彩:大红、军绿、灰、蓝……也是那一年,周恩来与加拿大总理克鲁多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加学者交换项目协议。 “我想,当时中国非常需要把好的大学生送到国外学习。”第二年,卜正民从多伦多来到北京。“我是第二批,一起来的加拿大学生有三四个。先到北京语言学院强化了6个星期的中文,然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历史,10个月。我觉得一年时间不够,申请再待一年,1975年秋就到了复旦,跟随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走在复旦校园里,除了几栋标志性的小红楼可供辨认,卜正民已不识其余。当年与两位中国同学共住的宿舍和常吃白菜土豆的食堂分别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30多年,他的兴趣一直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他的东方兴趣有迹可循:最早可能是铃木大拙《碧严录》之类的禅学著作,然后是日本佛学;因为多伦多大学当时只开了中国佛教史这门课,他便选作辅修。毕业前,他决定改专业,从英国文学系转入东亚学系。那里的训练,为他后来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打下基础。 李庆甲教授给卜正民的印象是“学问很深”,他帮助卜正民打开通向晚明世界的那扇门。“选读的是李贽的《焚书》、《续焚书》以及《藏书》、《续藏书》中的一些篇章,也读王夫之。我对王夫之有特别的兴趣,他是17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我记得当年在福州路上的一家旧书店买到王夫之的全集,是线装书,好高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卜正民对《金瓶梅》感觉一般。 新民周刊:还记得1974年北京和上海的样子吗? 卜正民:北京给我的印象是一座古城,那些建筑充满了历史感,但政治气氛很浓。我更喜欢上海,上海人很能够接受新鲜事物,待人也比较开放。所以这十多年,我跟上海学界的交往更多一些。它有一种旧时代的味道,不单是殖民地味道,而是那时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的味道。站在外滩,你能够感受到。 我的留学生活到第二年感觉好起来,大概是因为到了上海,虽然当时物质上北京上海都比多伦多艰苦。我记得食堂里常常吃白菜、土豆,偶尔有一点肉,但我们都做好了来吃苦的准备,进入这样一个历史上古老神秘的、今天的人民共和国。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当年您的工农兵同学的文化素质?当时学校里气氛怎么样? 卜正民:相比之下,工人的文化水平最高,而且他们很聪明。解放军当中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高,一部分人逊色一些。农村来的最弱。不过总体上,我没有觉得工农兵大学生的素质不如我们。我当时跟两个中国同学一起住,隔壁宿舍有个同学每天早晨跟我、还有另一个留学生一块儿跑步,天天如此。他本来是上海发电厂的工人,复旦毕业后回到电厂管理图书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我明天就要去找他玩。 八年一本书 瘦高个的卜正民若穿上魏晋士大夫的宽袖袍服,定能展示那种翩翩风度,他有一种天生的温文尔雅。现在,他坐在主席台上笑了,大概听到什么有趣的提问,眼睛、嘴唇运动起来,脸上绽放几朵小菊花;有时,他沉吟片刻,谦和地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考虑过,不能马上回答你。” 不久就要去牛津大学任教的卜正民给华师大一位同学留下特别的印象:“来讲座的大牌教授,就是问到专业以外的问题,多少总能答两句,但他居然说自己不知道,很少见。”相识多年的李天纲教授则说:“他已经不需要用那些东西来吓唬人了。” 新民周刊:听说您在哈佛师从孔飞力(PhilipKuhn)先生,能说说那段经历吗? 卜正民:我1976年去哈佛念书时,导师是史华慈教授。当时孔飞力教授还在芝加哥大学,1978年他来哈佛。但1979年我就去了日本,在东京呆了两年,查资料。 孔先生对19世纪感兴趣,而我对明朝感兴趣,我没有直接受教于孔先生,他影响我更多的可能是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与人的联系、人与人的关系、人际网络、政治与社会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等等。1984年临近毕业时,孔先生邀我一起编过闵斗基(韩国汉学家、首尔大学教授)的英文版文集。孔先生70岁寿辰时,我跟威廉姆·施坚雅一起为他举办了一个比较盛大的庆生宴会。孔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在我看来是西方最好的汉学著作之一。 新民周刊:我在《剑桥中国史》明代卷里找到了您写的章节。 卜正民:《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有两卷,第七卷是编年史,当时牟复礼(FrederickMote)和崔瑞德(DenisTwitchett)邀请我写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一章,收在第八卷。我写得很快,但修改时间挺长,前后花了一年工夫。我很感谢他们给了我相当大的自由,用我喜欢的方式完成那一章。而我发现无法将想写的全部内容放进那一章,就有了《纵乐的困惑》这本书。 明代的交通与商业本来是我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从论文到成书,花了8年时间。90年代初我又来上海,在当时还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图书馆,我看到了1609年的《歙县志》。歙县是南京南面一个风景如画的内陆山区县,它的贫困落后与当时富有的商人之乡比起来,有天壤之别。知县张涛是个小人物,在篇幅庞大的《明史》中,他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他中过进士,当过县官,也调查过官员腐败,晚年远离政治,在家乡从事写作。他花了两年时间撰写县志,抨击商业,批评时代,但他也属于那个时代。我觉得他说得很有意思,说出了困扰同时代中有改革意识却比较保守的那部分人的共同的忧虑,所以,我选他作为回到那个年代的导游,有点倔强,有点古怪。 这部将叙述、轶事和严谨分析巧妙结合的书1998年出版,2000年获列文森图书奖。耶鲁大学历史系史特林讲座教授史景迁评价说,“赏心悦目,充满了动感和细节。”张隆溪先生对其行文间巴洛克式的音韵美也表示过赞赏。卜正民笑说:“我原先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史。”英式英语的严密、周到、曲折、有礼,记者在翻译其书面补答时再一次感受到。 “深思熟虑对我的治学很重要。慷慨陈词很容易,但更困难、更有价值的是缓缓道来,意识到你现在正思考的一切将来都有被修正的可能。思想总是向着暂时的结论走去。” 更好的镜子是世界历史 新民周刊: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像极了那个“财富带来快乐,快乐触发困惑”的明朝,您对此怎么看? 卜正民: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如果我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走过这30多年,我不会去写这本书。处在如何调和追求利润和保持道德水准的欲望的两难之间,一些中国人发觉他们再次生活在类似晚明的矛盾环境中。对于希望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位置,而原有道德体系面临解体的国家来说,一个快速的回顾显得很有必要。 新民周刊:明朝276年的历史,在知县张涛看来,是一部从前期稳定的有道德秩序的农业社会蜕变为后期道德堕落的商业社会的痛史。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卜正民: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不认为晚明是一段衰落的历史。一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必须为明朝的覆灭承担一些责任,但又不愿担负所有的责任。他们试图表明因为所处的时代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也不想让清统治者自以为,如果没有明朝内部的腐败,满人就能征服中原。明代当然是一个发生了伟大变革的时期,只不过在最后十年分崩离析。 新民周刊:我读了《纵乐的困惑》,它最后落在批驳“西方中心论”,而没有分析这个国家内部经济巨大发展和生活失去平衡之间的矛盾成因,您对此有感觉吗? 卜正民:我承认这一点。这正是我在下一部书中想解决的问题。明年哈佛大学将出版我主编的一套书,将元、明连在一起分析,我试图探索这个矛盾的来由。 新民周刊:那天您谈到今天中国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环境代价。就您接触的范围,“人心(失衡)”的代价是否同样值得注意? 卜正民:中国人今天面临的心理问题相对于物质问题是第二位的,虽然它们常常也能反映物质问题,但那不是根本。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造成资源的紧张,而资源开发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基。就像我在《纵乐的困惑》中所说的,就像我暗示的晚明的真相——物质的改变总是令人沮丧,要理解这种沮丧,就需要考虑人们生存状况。 新民周刊:《纵乐的困惑》中,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文人的轶事、观察和抱怨引人注目。您为什么比较看重这些“书生言论”? 卜正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喜欢去找过去那些让人们陷入困苦、哀怨的东西。明代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发表了各种见解,记下了许多事情,而恰恰是他们的抱怨让我感兴趣。这些怨言帮助我看清他们生活表象底下的紧张关系,接着帮助作为历史学家的我去理解他们如何经历那个时代的矛盾。那不仅仅是困惑他们的东西,而且是他们无法找到一个简单答案的问题所在。 新民周刊:如果从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算起,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已有400多年历史。在您看来,汉学研究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您对哪些人的研究比较关注?卜正民:这个问题挺难回答。从利马窦生活的时代到现在,汉学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学家们的水平也提高了,他们能够去分析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事务。事实上,汉学研究的巨大力量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是中国之外。提出“中国中心论”是重要的,但远离“中国中心论”也是有益的。中国人自然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特殊的、单独的案例来考察,但这样想也许是有帮助的:中国就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汉学家们努力用中国的资料研究中国,但局外人的身份也许会让他们得出国内研究者不以为然的结论。
如果说关于汉学有什么不公平的话,就是中国人没有一个叫做“欧学”的研究领域。去年11月我在澳门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我认为如果中国学者早发展这项研究的话,他们一定能够从中受益;中国人可以更完整地理解1840年以前的西方,并对后来发生的事有所准备。 新民周刊:您如何看中国古人所说的“以史为鉴”? 卜正民:历史是一面镜子,但万物都是镜子,如果我们把它举起来并透过表面凝视它。我们从事于研究、阅读、思考,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更好地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联。从历史这面镜子看进去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当两种状态(人与世界)都变了(意味着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但人们依然会基于可以预见的一套需求来做事(这说明人活在一种持续的规范里)。 只看区域性历史的危险在于,它会诱导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只需要向自己的过去提出所有的问题,并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对于中国人来说,一面更好的镜子是世界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愿意活在万历年间松江府 卜正民偏爱爵士钢琴。当他听着KeithJarrett科隆演奏会现场的音碟,眺望休伦湖蓝色的湖水,遥想法国探险家杰恩·尼克雷在1643年夏天那次想当然的中国之旅时,他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之外的人。他在历史中静观文化与社会风景,想寻找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但他也知道,“我们都是陌生人。” 新民周刊: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和地方是您最愿意去居住的?为什么? 卜正民:我大概最想生活在万历时代的江南松江府。比起经济发达的苏州府、贸易发达的泉州府,松江府是一个市民文化昌盛繁荣的地点,那里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书画家董其昌是上海县人,他后来就搬到松江府去了。 新民周刊:研究中国历史对您个人产生过哪些影响? 卜正民:研究中国曾经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我能额外地去体会人们是如何在困难的文化中求得生存,而不仅仅限于我成长的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也帮助我在家庭中确立更宽广的信仰和道德准则。我也许愿意坚持那些信仰,但我也明白生活在另一套持不同信仰的家庭是多么容易(出身多么偶然),那样我会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