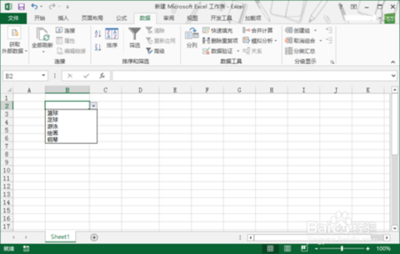文/刘丹亭

纪德文集》里有这样一篇文章极有意思,有人发动全球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记录自己的同一天。总的说,纪德不过是写了一篇流水账。但这个创意的确非常有趣,就像不同人用手中的拼图,努力拼出一个圆,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一段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时间。有一段日子,网上亦有人组织此类活动。试想如果像必须申请户口那样,每个人都得写出哪怕是随便一天,之后编辑成册,卷帙浩繁。多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终其一生翻读它,但永远读不完(因为新篇章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书必有一种关于人类生存意义的真理,每个活过的人借此永远存在着,永不消逝。全世界的一流图书馆分册保存这部书,再写下去,二流、三流的图书馆、书店,一切公共场所,所有人家里,都有无人翻阅的几大册,于是这部书又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真理价值。没有人能读完它们,于是也就没人读它们。 这是个悲剧,又一座巴别塔轰然倒塌。我小时候,隔不了多久就会为世界上一切可担忧的担忧。后来这些命题都担忧过了,我便开始担忧天堂。总有一天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口增长过快问题会被转嫁到天堂上。试想永不停止的人口增长,只有进而没有出,只有生而没有死,就算天堂无限大,人口永不停息地增长也会大过无限的承载能力。最后,天堂的人口密度会有我们教室那么大,这以后就更热闹了,人们背着,抱着,一个踩在一个身上,永远保持这个姿势。或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向天堂上的天空祈祷,梦想着凌驾在天堂上的天堂,能解决一部分人口负担。死去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反复讨论其可能性,直到永远。 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我以为人死后都得上天堂),为这事愁得都不敢死了。于是有人教育我说,不要把天堂想成有形的,天堂是人灵魂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而上的善。因此每人都有每人的天堂,各不相交,各不相撞。这样好。我们的灵魂就像孤独的星球在无限当中旋转,被凝滞的存在裹得紧紧的。我还以为很多人正是不堪这种折磨,才以死解脱的。没想到死去还是这一套,这才是虽死犹生哩! 纳博科夫有一句诗,大概是说如果人死去而不能将留在人间的爱物带走,天堂的永生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也正是我想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常悲剧性地幻想,待我死去,我要让我的后人把我的布狗、芭比娃娃及其各式衣服、“珠宝盒”,平素搜集的小纸片、小布头,一起摆在我的祭坛上。我也明白,尽管死后可以永生,但带不走它们,也就是告别了我记忆的真实,走向忘却——忘却真正意义上的生。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愿借死亡来回穿梭于各个世界,我不愿借死亡永生,但愿我能神形俱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