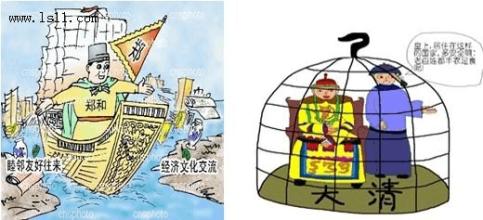中国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达1.9亿,相当于每六到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精神障碍,但治疗率不到10%
《财经》记者于达维《财经》杂志/总196期
10月10日,是第1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把2007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变化世界中的精神卫生:文化和多元性的冲击”(Mentalhealthinachangingworld:theimpactofcultureandpersity)。 这个主题对应着当今世界急剧的变化:无论是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财富的增长、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并不总是让人们变得更加快乐。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堪重负,甚至濒于心理崩溃。一些专家警告说,精神危机或许要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 而目前的中国,恰恰是精神危机的重灾区。 巨变压力 不久前,在上海开幕的“2007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上海区域性国际会议暨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学术年会”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上海精神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园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达1.9亿,相当于每六到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精神障碍,但治疗率不到10%。 精神危机是如何造成的?也许其本原或细节仍有待于科学界进一步的厘清,但一个基本概念已为大家所公认:对于外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体这种复杂的有机体必然会在生理上、心理上做出主动或被动的反应。一旦这种变化超越了个体极限,就势必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障碍。 这正可以解释中国精神健康严峻性的原因。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肖泽萍曾经引述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兄弟》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今天的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状态——“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的确,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这种感受十分强烈:在过去二三十年中,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几乎一切肉眼可见的差距都在迅速拉大。1979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比是1.4∶1,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扩大到2.8∶1。按照每人每年688元人民币的中国贫困标准,中国目前贫困人口仍在3000万人左右;根据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计算,中国贫困人群则为1亿人左右。 即使在一个城市内部,这种因差距而带来的压力,也无处不在地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深圳为例,作为最典型的新兴移民城市,它在20多年间从小镇迅速成长为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2006年由深圳康宁医院完成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深圳人心理障碍的终身患病率高达21.19%,即这个城市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会遭遇精神困扰。 根据2006年在深圳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63%接受访问的人认为自己的压力接近了极限;超过20%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超过了极限,接近崩溃;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 移民背后的农村留守人群,也同样属于精神障碍高发人群。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上海精神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园教授指出,中国有1.2亿流动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男性,都是农村家庭的支柱;而留守人群中,妇女有4700万、儿童有2300万,老人有1800万。家庭结构的改变,往往是导致精神障碍的潜在危险因素。 过度应激
把所有的精神障碍的发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归咎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显然也是不科学的。除了遗传性因素,包括各种感染、化学物质、脑和内脏器官疾病等生物性因素,也都可能把作为个体的人推到精神危机的阴影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艾滋病等慢性疾病,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产生。 通常,精神危机的出现是心理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由于社会变化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急剧性,使得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到这个环节。因为正常的心理应激,可以使机体能够对外界刺激做出迅速而及时的应答。但是,当外界刺激过于激烈,或长期反复出现,超出能够承受的极限时,就会造成病理性损害。 在肖泽萍看来,当人的身体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神经系统应激过度时,短期内就会在人的肾上腺系统有所反映;长期下来,则会导致神经递质过度消耗,造成丘脑、垂体,乃至整体免疫力水平改变,进而表现为抑郁、焦虑甚至神经综合症。 “中国变化太快,差距太大,人们来不及适应。”她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从目前的动物实验上看,环境频繁变化导致的过度刺激,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病率明显提高,虽然环境变化与精神分裂的联系还并不明显。 从目前普遍采用的抑郁试验模型来看,在慢性轻度应激环境下,试验动物均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典型抑郁症状。 精神障碍不仅会受到其它器质性疾病的影响,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其他疾病的发生。从1996年到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新华医院通过对位于杭州、绍兴、湖州等地的3万多例抑郁患者的血液循环动力学分析,发现抑郁与焦虑障碍,均会导致显著的血液循环动力学改变,主要表现为循环系统的能量消耗增加、机械效率降低,以及心脏工作处于低效率状态等。这意味着,抑郁与焦虑障碍人群的心脏病发病危险程度,往往比普通人高出1倍以上。 中国现实 “在中国,包括精神分裂、抑郁症、躁狂症等在内的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一共有1600万人,超过了北京的常住人口。”北京回龙观医院王绍礼医生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卫生部统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除了这些被定义为患者的,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并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更是达到了1.9亿人。实际上,神经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首位,约占整体医疗支出的五分之一;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这一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至四分之一。 与日益增长的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的匮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肖泽萍教授告诉记者,以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数量来计,日本为9.4名,美国为13.7名,澳大利亚为14名,而中国仅为1.29名;即使按照每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床位总数来看,中国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日本为28.4张,美国为7.7张,澳大利亚3.9张,中国只有1.06张。 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系教授拜伦古德(ByronJ.Good)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承,现在中国精神卫生的根本问题在于,精神障碍造成人体机能障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5%,而精神卫生在国家卫生整体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1%。 以精神危机的“重灾区”之一深圳为例,在深圳精神卫生研究所刘铁榜教授看来,“深圳的人均精神卫生资源,比几内亚还要少”。 从全球范围来看,将精神卫生服务机构整合进入社区和综合性医院,以取代收容所模式的精神卫生保健体制,已经成为基本共识。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患者康复和融入社会,但是也需要更大的投入,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 不过,拜伦古德也警告说,如果在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发展良好的社区服务替代的前提下,就取消现有精神卫生服务,所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2002年4月,中国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残联共同发布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制订了六大目标和16项完成指标,但却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张明园教授透露,目前中国正在讨论精神卫生体系建设方案,尚存在三大争议:一是按潜在需求来定,还是按实际需要来定。从流行病学调查上看,中国在精神卫生体系上需要很高,缺口很大,但从实际服务情况上看,有效需求又不足,床位利用率和门诊数量都不高;二是以市场化运作还是计划运作。市场化固然是全球的趋势,有利于改善服务,但是前几年有限的市场化运作效果并不好;三是以医院为主还是以社区为主。社区为主是国际提倡的方向,但是在中国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把钱投到社区恐怕是杯水车薪。 实际上,经费缺乏也是世界精神卫生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目前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心理干预和康复手段都有很大发展,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人权开始重视,精神卫生保健的财政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变,但这一切显然还都刚刚开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