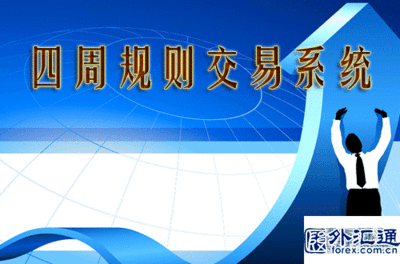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国内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撰稿/李宗陶
曹韵贞1941年5月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1963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肝癌的临床研究,1986年转向艾滋病领域。1990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毒发病机理的医学家。1993年起参与“鸡尾酒疗法”的病毒学研究工作,并致力于中外医学专家的学术交流。 1998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特邀委员。2002年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临床部主任;受聘于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及临床组组长。2007年7月退休。著有论文150多篇,摘要100多篇,书8本。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弄堂口或北京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 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DavidHo)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在各种学术场合,她有一说一,不来虚的,这是另一种厉害。在这个云集了政府官员、科学家、临床医生、法学家、社会学家、富豪以及民间英雄的圈子里,她风格明显,富有权威感,却不给人以权力压人的感觉。曾在某些充满外交礼仪的场合遇见她,看她飞快应付着,看她趁人不备转过头来,冲“自己人”眨眨眼睛。 退休。她保留了有限的几样职务,譬如几家医学杂志的主编、编委,其余一律不兼职、不挂名,“我不要藕断丝连”,她说。 茶几上一本讲清朝皇帝的书看了一半,她还打算把明朝皇帝一个一个看过来。“昨天在翻一本烧菜的书,第103页上,讲八宝鸭怎么烧。多少年了,天天6点钟起来……现在,我要去照顾小外孙、要为自己活了”66岁的曹韵贞宣布道。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妈妈28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17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就以高分进了上医。 1963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后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台了,被批斗,去世了。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我妈辛苦一生的积蓄被抄得一干二净,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不能参加一些会议,不能写大字报,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比同辈人得到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助他们应付造反派,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真是得益匪浅。但是,从1965年到1978年,我们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四次下乡,总共呆了6年半。没什么好怨的,谁让你出身不好。我只记着妈妈的训导: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1971年我被派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6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医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X光显示两肺37只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案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那里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给那位农民服用一个礼拜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我还用半边莲治好了嗜神经毒的蛇咬伤,等等。当时报上也登了,不过都归功于赤脚医生,并没有我的名字。 “放洋”和第一次回国 大学学的是俄文,虽然我妈一直省吃俭用想送我“放洋”,但当时受的教育让你觉得留洋就是崇洋。直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中外关系才慢慢恢复,医院开始有外宾来参观,也开始选拔医生脱产去学英语,我很羡慕,但知道自己没资格,也不敢想。 我妈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学英语呢?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了四册《医学英语读本》,可我连ABC也没学过,买了也不懂,就跑到旧书店,二角一分钱买了本《英语语法通读》开始自学,那时候我已经35岁。两年下来,我可以翻着词典看医学杂志,但不会讲、听和写。 1979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率120人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团里有12岁的杂技演员,也有78岁的政协委员,大部分是60岁上下刚复出的领导干部,从心脏病到糖尿病什么都有。市委要求派一个女医生,60年代毕业的,要求业务全面、动作迅速的。我们医院当时的院长裘麟教授刚好从“劳动改造”中解放复职,马上点名让我去。“领导委任出国”在当时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说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离启程还有一个半月,我从路边电线杆的招贴上找到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自己掏钱去学日文。 一进羽田机场,那感觉比起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38年,才明白为什么我妈为我不能留洋学而耿耿于怀的原因。踏上自动电梯,使馆陪同人员在耳朵边上一个劲地说“小心脚下,小心脚下”——5岁那年妈妈曾带我在当时大新公司乘过的呀,可那自动电梯从此沉睡好多年那一刻真是,我脑子里像开飞机一样,多少念头涌上来,恨时光不能倒流,后悔自己虚度年华。这一夜失眠,从此,我决心争取“放洋”。 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探索肝炎与肝癌的关系,正在做170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测定。1981年,哈佛大学一位流行病学的年轻教授来访问,科主任临时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语单词跟他说起这170例,他很感兴趣,临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后寄给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荐下,1981年6月26日,我去了费城FoxChaseCancerCenter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r.Blumberg肝炎抗原的发现者的实验室,他的助手Dr.London教授成了我的老板。Dr.London是个皮肤科专家,是美国第一个报道卡波氏肉瘤与艾滋病感染有关的医学科学家。费城一呆两年半,我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实验室训练。英语从一句不会讲,听见电话铃响只会发愣,进步到听说读写虽然不是很好但完全可以应付。 1983年,医院写信来要我回国。Dr.London一再挽留,我谢绝了,带了一些仪器、试剂回国。回来以后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后出任免疫室主任。我们这批人,真的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但那时候做科研很困难,什么都没有。我当时算是杰出青年科学家,什么三八红旗手、卫生部劳模、上海巾帼奖第一名,荣誉一大堆,还拿过5万元青年科学家的基金,但对科研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我拿出了在美国两年半的工资,购买实验设备和试剂,建立了中国的肝癌细胞株,但还是缺钱,做不下去。当时国家政策不像现在,对归国人才有一整套政策支持,而且气氛也不正常,如果做成了,人家就说,他国外回来的,做出来有啥稀奇;做不出来就说,喏,他国外回来的也做不成。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申请入党,一直不批,有人卡。大概想这个人业务又好,如果成了党员,就是双料人才了,不行。所以一直入不了。 在尿液中发现艾滋病毒抗体 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来开第一届国际肝癌会议,看了我的实验室说,你再出一次国吧。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跟院长也商量了,决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实一下自己,二是为医院再争取一些经费,把实验室扩大起来。当时肝炎五项指标测定用的都是国产试剂,结果不稳定,我带回的试剂是进口的,非常昂贵,后来就买不起了。 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AIDS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研究肝炎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一本艾滋病的书都没有。我记得到上海汾阳路医学情报站去查资料,只有第一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摘要,16开薄薄一本小册子。我对AIDS一无所知,本想另等机会,但纽约大学的人通过Dr.London劝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国,那是1986年7月。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设实验室的人。才去2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领导者是白血病/艾滋病专家,他那里已经建立起一套HIV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12天,基本学会了,又呆了8天,要求回去。老板说,为什么?我说,学完了。他说,really?我说,你叫我学的我学会了,你没叫我学的我也学会了。他说,那你回来能做吗?我说,如果不能做,你不要给我工资。他打电话给那边的实验室。血液科专家说,你赶紧让她回去吧,再不走我实验室要让她搬走了。说实话,那些抗体抗原检测很简单的,我两天就学会了,后来就在那里看别的,什么细胞培养啊,全看了一遍,记在本子上了。 回去后我招了第一位技术员,是个意大利小伙子,我们有了一间小实验室,从一个tiporder起家,发展到有五六个人,后来跟ABBOTT公司合作,做500例艾滋病毒抗原检测。以后又与CHIRAN公司合作检测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含量。由于这段渊源,这些公司对我回国以后筹建实验室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86年12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有报道说在艾滋病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但是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检测就想,干脆把抗体检测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心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1989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97%以上。 那时我已理应回到Dr.London的实验室去,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体情况跟London说了,他赶来纽约跟我新老板谈了2个小时,最后讲:“我把最好的人给你了,你要对她好。”又对我讲:“医学上一个新发现不容易,有时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放弃。”艾滋病当时还是全新的领域,我对新东西也挺感兴趣,就留下了,转向做艾滋病的研究。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我从1986年开始和艾滋病打交道,先是在美国实验室认识艾滋病毒,接着到患者身上去收集艾滋病毒研究艾滋病毒为什么会、又怎样使人发病﹖这些对我来讲绝对是个挑战。说实话,科学界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记忆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数聪明人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起点也不高,英文不好,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没读过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奋。我属于那种认定目标就坚定地走下去的人,而且要走到别人前面,不怕付出。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那些年补回来。后来回国在北京那几年也一样,没去过颐和园,没看过一场电影。衣服也不会买,以前是我妈买,后来是先生帮我买。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三样:飞机、旅馆,还有艾滋病朋友。 我是1989年认识何大一的。那时正是他研究的黄金期(1981-1996),他扎扎实实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在精液中发现HIV抗体。 那时候,纽约市有一个有钱老太太Ms.Diamond。她先生是一个移民,19岁刚去美国时据说身上只有一美元,后来做房地产起家。Ms.Diamond继承遗产后就成立了戴蒙德基金会,一块是提供给搞艺术的,还有一大块就是提供给医学研究和医院建设。1990年,他们想在纽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面试了100多个科学家,最后选了37岁、娃娃脸的华人何大一。 1990年10月15日,我来到了纽约医学中心对街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参加实验室筹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后的1991年4月16日,中心正式成立了。 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1992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8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那时候也想过是不是去读个PH.D(博士),何大一说,你M.D完全够了。他叫我“特快专递(express)”,因为我做起事来动作很快,有时他改主意都来不及,因为我已经动手了,手下的年轻人也常说跟不上我的节奏。越是做得多,越觉得知识不够,越是要拼命学,拼命做,好像这样一天才没白过。我的命很好,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教我帮我,我也努力,机遇来时就能抓住。艾滋病研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科学家的努力可以救全世界很多很多人。 我怎么入的美国籍呢?其实1989年我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证,但是1995年有一次去台湾开会,台湾方面刁难我,那边的说,你如果是美国护照我马上批。我一气之下就入了美国籍。飞来飞去确实方便了,但这下好了,现在回中国要签证了。我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深蒂固,改不了的,谁把我当外国人,我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1993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那年我陪他来中国,第一个引荐的人是曾毅院士。1996年何大一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卫生部发出邀请,1997年我陪何大一又一次回来,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 每一个出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漂泊感,这时候的爱国心就会非常强烈。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小渗透到血液里的情感,祖国培养了我,祖国有我的亲人我的师长我的同胞,我应该为她做点事。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有两点我永远记得何大一的恩:他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还有一次是,我刚回国,我丈夫郑医生在美国心脏病发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谈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医院装的冠状动脉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尽心尽力。 何大一在回信中说:Ourworkwouldnotbethesamewithoutyou.Whilewehopeyouwillenjoythetimewithyourfamily,donotbesurprisedifwecalluponyouforhelpandcounsel.Westillneedyou.WithdeepappreciationforyouryearsofcontributiontoADARCandChina'sAIDSeffort.(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希望你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别惊讶我们可能还会找你商量或帮忙,我们仍然需要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对中国艾滋病事业的贡献。) 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一支队伍 1990年在美国买了房,每月要付贷款1800美元。1998年回国,在美国没有工资拿了,很快就把房子卖了,因为供不起。 我回来不为挣钱,不想当官,也不求名,所以谁的马屁我都不拍。在中国要做事情是很难的,各种情况都会碰到,有时也看不惯。但下面病人是很苦的,跑下去一看你就想要深入去做。当年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老院长陈春明教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你只要想是为谁做,为老百姓做,什么怨言都没有了。”这话对我一直有用。 而且我后面还有许多在艾滋病领域工作的海外华人专家,他们也希望为祖国做事情,我算是牵根线吧。 回国的曹韵贞依然在跟时间赛跑。仅仅两个月,就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开始接诊。而她常常买两个花卷馒头放在办公室里,早上一个,中午一个,因为“正经吃饭太费时间”。 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亏欠了自己,只是觉得亏欠家人很多。我愧对母亲,她28岁守寡拉扯我们长大,很大岁数了还要帮我操持家务。她病倒了,我在家只守了几天就又得出去讲课,后来她因为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我自己还是医生!我觉得这个内疚是一生都没办法弥补的。我先生在美国做完心脏手术到北京,结果又变成他在照顾我。 小外孙Jake出生时我人在内地,只听说他不会吸奶,三个月大、五个月大时见了两次,发现一些症状,但接触时间太少,我想大概是发育迟缓,直到八个月时再见,他还不会坐、爬,我才警觉有脑瘫的可能,一查果然是。我女儿为了不遗弃这个孩子,放弃了国际贸易极为热门的工作,为他的治疗费尽心血。女儿需要我,可我为了艾滋病人长年在中国各地跑,没有办法帮她。 人到中年,本该是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儿女尽责,可一直是全家人为我服务,为我的工作服务。我现在很怕一个人开车,会不知不觉想到家里人,会想得出了神。 为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跑了7趟云南,2002年在云南省启动的治疗项目为300例感染者提供了3年规范治疗。8年来,她去了N次河南、山西,足迹遍布所有的重灾区,她负责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CIPRA项目,对山西省闻喜县700例HIV感染者进行了规范治疗。为了打进新疆,她去了不下10次,从一开始只欢迎讲课到后来能去病人家里探视,最终以一片诚意说服了当地政府,治疗得以全面展开,比尔·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也由她牵线进入新疆。 艾滋病治疗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曹韵贞说,就是要迅速提高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多的村医的水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都在叫要新药,其实新药来了不好好吃,出现副作用医生不懂得解释说服,动不动就停药,还是会产生耐药性。” 在河南郑州,她自己坐门诊看病人,带徒弟,这些医生又到更基层的医院去讲课,带更多的徒弟。她直绷绷地说:“没有一个省的领头医生不是我培养的,最自豪的就是培养了一支队伍。”她尽力给徒弟们创造深造的机会: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的孙永涛经她介绍到美国免疫学家BrooseWalker手下进修,他英语好,最后能在美国坐门诊看病人,回国后带回61万美元的基金项目,建立了实验室,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做CTL(细胞毒T淋巴细胞)测定的人;郑州六院的何云也在她的推荐下赴美进修;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周曾权、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跃新主任都已能独挡一面。 科学事业是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更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学术界有一些风气不好,就是垄断,什么都要把在自己手上,我就看不惯这种现象。尖端有两种,一种是宝塔形,一种是梯形,宝塔尖上是很突出、荣耀也大,但倒起来也快;梯形上面虽然站了一排人,但很稳固。一个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不是强项也攥在手里……要做老大,要靠自己一点点做出来。不过现在有些领导就喜欢敢说大话的人,做不到也无所谓。 中国一些地方的艾滋病治疗现在政治味越来越浓:为艾滋病人着想的少,对政绩工程、国际形象感兴趣的多。我这样说也许会得罪人,不讲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能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能做了,该激流勇退了。我不想当英雄,离开时就希望听一句话:曹韵贞为中国做了些事情。没有,也没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