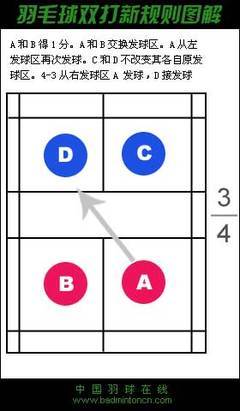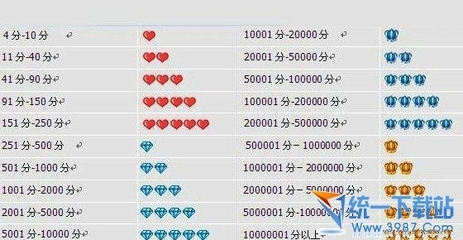因应受贿犯罪日益复杂化、隐蔽化的形势,“特定关系人”概念首入中国反腐败法律框架。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深谈最新“两高意见”背后的反腐败新策略
本刊记者段宏庆王和岩/文
专访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7月18日下午,62岁的王振川在自己的办公室,甫一落座,未做客套,便开门见山地对《财经》记者说。 午后的阳光照在僻静的北京市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院内,松柏、铁树点缀其间,其中一栋三层小楼的二层,副检察长王振川的办公室布局简单明快。房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办公桌后墙上的巨幅全国地图,还有一面国旗。 王振川,中央纪委常委、最高检分管反贪污贿工作的副检察长,中国反腐战线最前沿的重量级人物。而《财经》选择此时采访王振川,是因今年入夏以来,反腐败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于7月10日被处以极刑,被舆论普遍视为高层加大惩治贪官力度的一个信号。 据《财经》记者调查,最近三年中,中国因腐败问题“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有二十余人,其中过半数案件已审结。一些腐败高官受贿的数额,亦不低于郑筱萸的649万元人民币。如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有近65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来源不明财产,王于今年1月12日被山东济南中院判处死缓。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受贿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于2005年12月16日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缓。从这个角度看,郑筱萸的死刑,打破了近三年来所谓“部级高官腐败不死”的规律,其标本意义非同一般。 5月30日,即郑筱萸死刑判决一审宣判后次日,中央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下称“八条禁令”)。该规定中首次出现“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并具体指出,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财经》记者了解,这是中国反腐败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首次纳入这一概念。 “八条禁令”印发的同时,中央纪委明确表示,自2007年5月30日起30天内,涉嫌违反这一规定的党员干部主动说清问题的,可以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在规定发布之后违反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7月8日,即中央纪委30日“反腐大限”到期后的第十天,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两高意见”)。该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盘吸纳了中央纪委的“八条禁令”。 对比“八条禁令”和“两高意见”,不仅内容一以贯之,用词和表述也几乎完全一致;惟一的区别是,“两高意见”在“八条禁令”的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条款,强调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二者的契合,使“八条禁令”从党纪上升为国法,进一步加强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由是观之,中央权力高层在加大腐败个案惩治力度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构建、完善反腐败制度。 62岁的王振川是河北省安国人,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他1964年19岁时即入中办机要干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转任中办政治部任干事,再任机关团委书记、人事局办公室主任、秘书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机要局局长等职。 1996年,王振川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01年6月回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同年12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反贪污贿赂工作。 作为专业人士,王振川还在2002年获得了国家二级大检察官证书。 此次《财经》专访为事前预约,但与王振川交谈中,他仍因批文件、接听电话不得不暂停,工作显然十分繁忙。有一个电话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打来的。“我们讨论了一下有关职务犯罪的问题。”王振川告诉记者。 整个采访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以下为访谈实录。 党纪与国法“无缝”衔接 “自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当中遇到的比较隐蔽的、不太容易识别的、非传统的受贿形式,大体上都被包括到‘两高意见’中了” 《财经》:这次先有中央纪委的“八条禁令”,40天后“两高意见”出台,从党纪到国法完成了一个对接。过去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王振川:在我分管反贪工作以来,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次。 这次,党纪和法制确实结合得比较好。其实“两高”在制定“意见”的时候,也是由中央纪委组织协调的。中央纪委提出,现在非传统的腐败形式比较多,而且这些形式往往比较隐蔽,比如有的官员自己不直接收钱,而是通过特定关系人等等。对于这些新的犯罪形式,《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很多腐败犯罪没有受到应得的惩处。 于是,由中央纪委牵头,“两高”组织人力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进行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们组织了专家论证,征求了全国人大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意见,并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见”。 在“两高意见”形成过程中,中央纪委提出,(相关内容)先作为纪律在党内公布,这样能增加实施效果,体现教育在先,预防为主。所以在5月底,中央纪委发布了“八条禁令”,而且规定在30天期限,如果有违反禁令情形的党员干部主动坦白,依纪依法从宽处理。这样做,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警示和爱护,使一些人不至于走到犯罪的道路上去,也提醒大家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违纪问题。 经过党内一段实践之后,“两高意见”正式出台。因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从党纪到国法的完整衔接。 可以说,自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当中遇到的比较隐蔽的、不太容易识别的、非传统的受贿形式,大体上都被包括到“两高意见”中了。当然,不可能全部包括,但是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主要问题确实都包括进来了。 “两高意见”使得我们打击腐败的法网更加严密,力度更大。 《财经》:过去党内也有大量的反腐败的规定,比如1997年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其中提出“党员干部不准利用婚丧嫁娶借机敛财”。但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不少官员是利用这些机会敛财。此次“两高意见”中没有纳入这一条,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振川:利用婚丧嫁娶敛财,过去我们主要作为不正之风来处理;构成犯罪的当然也有,但比较少。这次“两高意见”,主要是将现实办案经常遇到的比较隐蔽的腐败形式规定下来。婚丧嫁娶的问题一方面不属于非常隐蔽的形式,因为这种机会敛财,群众举报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婚丧嫁娶中,敛财的界限也还是相对明确的。收少量的钱财,那是人情往来;但如果是大量敛财、受贿,有请托人,又为其谋利益,那也是受贿,肯定要追究责任。 总的来说,“两高意见”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形式都纳入进来。但是没有纳入进来,也不意味着就不受处理,关键还是看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只要符合,不论什么形式都要打击。 这次制定“两高意见”,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司法标准统一问题。过去由于大家思想认识有差异,有些情况可能在某些地方处理了,别的一些地方却没处理。比如官员长期借用房屋、汽车却没有过户的问题,如果按照《物权法》,没有过户产权没有变更,一些司法人员因此认为不能算作受贿。但这次“两高意见”就将其纳入受贿范围,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进而收受请托人的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我们认为,《刑法》上的受贿和《民法》上的产权问题不完全是一码事,关键要看有没有故意的实际占有。 《财经》:我们注意到,“两高意见”在中央纪委“八条禁令”内容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条款,就是强调刑事政策宽严相济,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振川:中央纪委“八条禁令”和“两高意见”出台之后,打击受贿犯罪法网更密,但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另一个问题,打击面不能过宽。 这个问题,我们在制定“意见”的过程中就关注过。“两高意见”要求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注意把握好分寸,掌握刑事司法政策。在这几个受贿形态中,要注意根据当事人的情况和作案的情节来分析。比如赌博,赌博的次数、是否有预谋、是否为权力人故意送钱?比如借钱,是以借的名义受贿,还是真的借贷关系?有没有还的意思、还的条件?这些都要具体分析。 贪官背后的“特定关系人” “过去我们打击受贿罪,重点关注‘利害关系人’,关注近亲属,但实际上有些近亲属与腐败官员的关系还没有情妇来得亲密” 《财经》:从中央纪委“八条禁令”到“两高意见”,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过去的法律规定是“利害关系人”,这次扩展为“特定关系人”,范围扩大了,而且加入了“情妇(夫)”的概念。怎样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情妇”或“情夫”呢? 王振川:情妇是一种统称,这个概念确实没有标准,严格来说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什么是情妇?有感情的女人?有性关系的女人?其实说不太清楚。我们在制定“两高意见”的时候也讨论过,要不要对“情妇(夫)”做个法律定义?但不管怎么定义,都还是有些问题。 不过,我们的司法工作和纪检实践当中,“情妇”这个现象十分普遍,很多腐败官员都倒在情妇问题上。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情妇明确列进来,这对实践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使得一些犯罪案件能够得到相应惩治;另一方面,对于预防犯罪,警示一些官员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也有积极作用。 情妇属于“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关系。过去我们打击受贿罪,重点关注“利害关系人”,关注近亲属,但实际上有些近亲属与腐败官员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情妇亲密;尽管情妇与腐败官员不是法定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为她谋利益,他对她也有特定的利益需要。 在我们查处的一些腐败犯罪案件中,情妇甚至比近亲属的危害还大。一些腐败官员为情妇谋了很多利,往往是几百万、几千万元的问题。足以说明情妇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财经》:“性贿赂”要不要写入法律,社会上争议也很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振川:这个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工作者中也多有讨论。从世界范围内看,有些国家是纳入法律范围了。 但我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条件下纳入法律范围还不成熟。这个问题很复杂,如何认定,如何处理,都存在很多理论和现实争议。我们毕竟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腐败犯罪还处于高发期,比这要直接明显、后果更严重的腐败犯罪还很多,我想我们现阶段主要抓紧处理那些问题。目前暂时不能考虑把这个作为犯罪来处理。 当然,随着今后法治的进步,不排除把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更为隐蔽的犯罪形式逐步列入《刑法》调整范围。不过这是通过立法机关来完成。 财产公示制度暂难以实现 “收入申报和财产申报不一样,正常的收入申报很难发现、惩处贪官” 《财经》:我们注意到,很多腐败官员都是案发以后才曝出资产高达上百万、上千万元。其实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过《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个制度至今每年也还在实行,官员一年申报两次。通过这个申报,为什么还不能及时发现贪官? 王振川: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申报的是收入,不是财产申报。在国外,人家是财产申报,所有公务人员都要申报财产。这和收入申报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收入申报当然很难发现并惩处贪官,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又不能实现完全的财产申报。 其实我们的报告制度很多,比如去年,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重大事项包括官员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的情况”;等等。 但是从这里面要真正发现贪污贿赂犯罪,其实也很难。但这样做也是在强化监督,对反腐倡廉也有积极意义。 《财经》:为什么现在还无法实现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 王振川: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比如国外的实名制,这是防止腐败、治理腐败的必有制度,我们也在推进,但很难完全落实。其他很多配套制度,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反贪机关,依靠纪检部门,毕竟只是事后惩处。从目前来看,我们检察系统每年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达到4万余件,力度很大。但仅仅惩治是不够的,关键还要预防。 腐败案件六大特点 “目前我国逃往境外的贪官,据我们统计应该不到200人” 《财经》:当前腐败犯罪的情况都有哪些特点? 王振川:我想,对腐败案件的情况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说明反腐败是有成效的。但问题是大案、要案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高中级官员严重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十分巨大。据统计,十六大以来,最高检直接立案或者指定省级检察院立案查处的省部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0件;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百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高达5929件。 二是贿赂案件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明显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受贿案件。 三是贪污贿赂犯罪行业特征越来越明显。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行业和领域,往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一些重点岗位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如近年来,全国先后多名交通厅正副厅长被检察机关查处;城建领域犯罪高发,如国土局长、规划局长因受贿被查处。 四是窝案、串案现象突出。许多案件一旦发案,会牵涉到多个干部和行贿人。最典型的如湖南郴州窝案,目前已经有多名市级官员受到查处,同时牵涉到一批县处级干部和企业老板。 五是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相交织。如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既有受贿犯罪,又有渎职犯罪。 六是犯罪隐蔽化、智能化趋势明显。大量贪污贿赂犯罪都非常隐蔽,腐败分子不断采取新的犯罪方式和手段规避法律,实施犯罪后转移赃款。潜逃境外现象增多。 《财经》:当前贪官出逃的情况比较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振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追逃有专门的明确规定。一些媒体上披露说我国境外逃犯有几千人,资金几千亿元,这其实不准确。从反腐败意义而言,追逃的严格定义就是贪官,不是指一般的逃犯;而且我们所说的追逃贪官,主要是逃往境外的。目前我国逃往境外的贪官,据我们统计应该不到200人。 当然,不论逃往国外的还是躲在国内的,我们都没有放松。为了惩治腐败,让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追究,追回违法资产,我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些问题,每年都有一些成果。但这是个复杂的事情,需要综合治理;一方面是要从法律上更加严密,另一个是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问题上,各国的法律制度不一样,国情差别很大,所以需要加强沟通理解。今年我们从日本引渡了一个逃犯,这是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的成功案例。过去和美国我们也有过成功遣返的案例。因此,虽然没有引渡条约,只要双方加强合作和理解,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国外也同样不容忍贪官,反腐败是一个国际共同的课题,这方面有很多潜力可挖的。 从国内来看,如何完善司法、纪律以及各种制度,这对防止外逃很重要。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规定,也都是为了防止出逃问题。我们最近正在研究建立防逃的机制,各部门正在积极工作,可望建立一个更有效防逃新机制。 《财经》:现在社会上普遍感觉在查处受贿案中,对行贿人打击力度不够。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王振川: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呼声,要求既要追究受贿者,也要追究行贿人,认为是行贿人腐蚀了受贿人,行贿人有非常重要的责任。这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对于打击行贿人的问题,“两高”在2000年专门发布过《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这说明我们对打击行贿犯罪是很重视的。 但是,在实践当中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刑法》规定,行贿罪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事实上,谋取的利益“正当”还是“不正当”有时很难界定。另外,我们为了办案的需要,往往需要通过行贿人来揭露犯罪,因此纪检、检察机关往往会给行贿人一定的承诺,只要把问题讲清楚,就减轻处罚,甚至不处罚。这在国外叫“污点证人”,道理是一样的。 《财经》: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贪官在纪检部门“双规”的时候往往认定数额很多,但到检察起诉好像会“缩水”。比如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纪委部门的通报中公布的数额很高,达到上千万元,但在北京二中院起诉时是600余万元。这应该怎么看? 王振川:纪检部门是从违纪的角度来查的,有些违纪不一定是犯罪。所以到了司法机关,必须要按照犯罪的证据来认定,不是犯罪的只能做纪律处分,二者当然不能完全等同。 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也有相反的时候,到了司法机关,查处的数额反而高了。像刘金宝(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记者注)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深挖犯罪,发现新的犯罪线索,最后查出涉案金额比纪委移交时多了好多。 密织法网,松缓刑罚 “国外法网很密,刑期往往不长;我们法网还不够密,刑罚就必须严厉一些。这也是一种平衡” 《财经》:我国《刑法》规定,受贿5000元就起刑,10万元以上甚至可以判处死刑。但这个数额目前让司法实践很为难。据我们了解,很多地方,可能受贿几万元不会立案;同时,现在的贪官动辄受贿上百万元,判处死刑也很难。这些将来会不会做调整?甚至像国外一样,取消受贿数额的规定? 王振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现在的《刑法》规定,受贿5000元就要立案,这个标准其实已经改过好几次的。1979年的《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数额,1982年检察机关定了1000元的标准,但到了1988年改成了2000元,1997年新《刑法》改到了5000元。 为什么这么改?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标准跟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们的财富情况还是比较吻合的。在1982年,1000元就很多了,当时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2万亿元;到了1988年定2000元的时候,达到了7万亿元。现在已经23万亿元了,就应当提高立案标准。 但问题是中国太大,贫富各异,现在有些穷的地方还要求降低标准。法律有明文规定,不照办有违法之嫌,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又难以统一。可以说,司法机关现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要承认各地差异,但一方面又要各地不脱离此标准,尽量向5000元立案标准靠拢,不要差异太大,尤其在同一个地方。 至于说能不能彻底取消这个标准,目前很难掌握。我觉得修改标准还是取消数额规定,还得认真研究。 完全用数额标准来衡量犯罪,其实并不科学。比如郑筱萸受贿600多万元被判死刑,比他收得多的却只是判死缓。毕竟具体情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收钱很少,但是干的事情很坏,影响很大,或者说损失很大;有的收钱很多,但没那么大的影响和后果。 从长远来说,我们的《刑法》修改趋向应该是越来越严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的规定就很密。比如贿赂罪,我们《刑法》规定,必须是给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取财物。《公约》不是这样的,它规定凡是收取一切不正当好处都是受贿,不一定非要有形的财物;而且包括答应、允诺,不一定实际获得。也不一定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只要是作为或不作为,这都算受贿。 还有受贿的主体,它包括所有的公司企业,一切机构。在这些规定上,我们的法律差得还很多。但我们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约国,是要实行的。 另一方面,从国外情况看,法网很密,但刑期往往不长;关键在于剥夺腐败分子谋取私利的条件,一般最高刑期也就七八年。我们的刑罚就很重,严重到受贿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判十年以上甚至死刑。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办法,因为我们法网还不够密,刑罚就必须严厉一些;既是惩治也是警示,由此产生一定预防作用。这也是一种平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