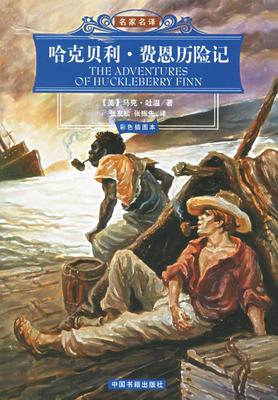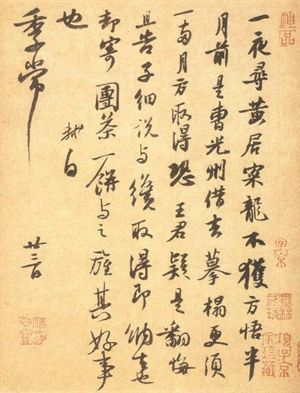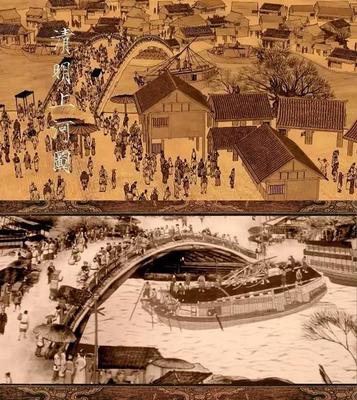记者/贺莉丹
现在媒体在娱乐、体育领域里的自由空间很大,但恰恰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一种相应的责任诉求。
5月13日,"林黛玉"陈晓旭因罹患乳腺癌去世。
1987年版《红楼梦》的播出,让21岁的陈晓旭一夜成名,这部重播700多次的电视剧也让林黛玉的荧屏造型与陈晓旭血肉相连。自此,陈晓旭一生的任何转型,都难逃媒体的追逐与公众的审视。 早在今年年初,"林妹妹"出家的新闻就为新年冷寂的媒体娱乐版打了一针强心剂。媒体探究陈晓旭的出家原因:是身患重病?是夫妻感情不合?还是宿命造就?有人说,陈晓旭之死是"林妹妹"惹的祸,她注定是从"黛玉"到"妙玉"的宿命。柔弱、多病、孤傲、敏感、清高……陈晓旭一些与林黛玉相似的特征被媒体逐一放大。 如今,正在红楼海选如火如荼的当口,陈晓旭辞世,不少媒体再次投入巨大的热情:是手术去世还是昏迷离逝?陈晓旭的亿万身家与京城400多平方米的豪宅终将归属何人?连日来,从陈晓旭的家人、同事到昔日《红楼梦》剧组导演与演员,乃至陈的前夫与昔日恋人,都遭到媒体的轮番盘问。大嘴宋祖德甚至在媒体放话,称陈晓旭诈死是希望公众淡化她"偷税漏税"的"罪行"。 媒体有没有"出格"?《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体伦理研究所教授王天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柠,请他们从媒介传播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陈晓旭事件。 起因:明星身份与猎奇心态 记者:陈晓旭出家和去世的消息,在很多媒体都是连篇累牍,你们怎样看待这种热情? 王天定: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艺人的生或死,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 张柠:一个人的出家或死亡这些断裂性事件,对公众不构成任何冲击,反而勾起了媒体刺探秘密的欲望,这是"狗仔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尽管我认为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更为复杂,不完全是媒体自身的责任,但我依然要说这种媒体炒作是很可悲的。 记者:陈晓旭的皈依关乎个人信仰,但被很多媒体用类似于王菲生子的方式进行报道,这种现象正常吗? 王天定:媒体要抓人眼球,要追求最大公约数。在商业社会里,媒体追求商业利益很正常。否定媒体的商业利益,等于否定了媒体的存在。 问题是,我国的高级媒体与大众媒体没有明显区别,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大众化、"狗仔队"化现象。我觉得,不同媒体面对这样一个事件应该有不同反应,比如严肃媒体,应该用一种较严肃的报道方式,有助于引导受众正确看待这个事件;但大多数媒体都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娱乐事件。 张柠: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媒体承担了对突发事件进行叙述的重要职能。这一职能却经常被猎奇心理所淹没。猎奇心态是商品文化的重要特征,它追求符号生产的新奇性,以吸引公众眼球为目的,而不是让人们思索生活的意义。在"陈晓旭事件"中,我们没有看到传播者为活着的人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东西,反而是让人们沉迷、猎奇、瞧热闹,甚至在电视上攻击死人。 记者:陈晓旭有3个引起关注的身份:明星、成功的商人与妙真法师。但媒体似乎都在强调她的明星身份。 王天定:如果陈晓旭不是明星,她不可能得到媒体如此巨大的关注;在大众传媒时代,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代价,就是必须每天面对媒体的质疑、曝光,有时甚至是一种骚扰。 张柠:最困惑大众和大众媒体的是陈晓旭的选择,大众媒体最想得到的是明星身份和商人财富,也就是所谓的"成功"。不管陈晓旭的动机如何,她最终选择了放弃,而这恰恰是大众媒体避之不及的。 过程:报道事实还是忠于谣言? 记者:3月1日,妙真法师曾发出个人声明,表达"云游四海,潜心修佛"的愿望。不少媒体就强调陈晓旭走的是从"黛玉"到"妙玉"的宿命,她深陷"林妹妹"的个人命运无法自拔。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报道中,都能看见这种强作解人。对此,你如何看待? 王天定:我觉得这完全建立在一种臆测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很多媒体离专业道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离本应坚守的基本道德底线。媒体报道的是事实,而不是臆测。 记者:媒体总是试图找出陈晓旭出家的原因,为公众寻找一个"合理解释",比如"夫妻感情不和"说、"身患绝症说"、"为公司造势说"…… 王天定:媒体的底线是什么?真实。受众关心陈晓旭为什么要出家,也需要媒体找寻答案,但这期间有很多媒体把臆测、传闻当成事实来报道,不是在报道事实。如果对陈晓旭有面对面的采访,让她讲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就是严肃的。 记者:当初李娜出家,媒体也有过很多类似猜测,为何有如此惊人相似的轮回?
王天定:传统的新闻价值强调反常、新奇。一个明星、一个红颜佳人突然出家,本身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件;另外,媒体总是遵循商业逻辑。 张柠:是陈晓旭、李娜、杨丽娟,还是超级女声,跟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新闻符号生产逻辑,媒体报道永远在低水平地重复,不断搞笑。 记者:大嘴宋祖德也没有消停,他说陈晓旭诈死是希望公众淡化她"偷税漏税"的"罪行"。媒体明知宋祖德所言大多不属实,为何还屡屡邀其做客?今天媒体的底线在哪里? 王天定:媒体的底线是坚守事实。把宋祖德的东西拿出来炒作,媒体已有点自轻自贱了。宋祖德就是想利用媒体进行自我炒作,这个过程中宋祖德达到了目的,媒体哗众取宠,赚取了商业利润,最后真正的受害者是整个社会风气和受众利益。 张柠:邀请那些胡说八道的人去做节目,貌似勇敢地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哗众取宠,甚至用丑陋和恶心来招徕观众,借此搞事,制造新奇符号,是在法律的底线上制造垃圾,放弃职业操守。 追逐:不过八卦而已 记者:我们在陈晓旭事件中也看到了不少八卦新闻。比如陈晓旭如何出道、几次婚姻、有无生养等个人隐私一一公布;被媒体不断逼问与陈晓旭的恋情,王小帅甚至当众发怒。公众需要娱乐报道,但娱乐报道有没有规则呢? 王天定:我倾向于新闻和娱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们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损害了我们的新闻专业精神,让老百姓对我们的媒体产生了一种空前质疑,影响了媒体公信力。如果一个媒体的娱乐报道真假难辨,时间长了,老百姓就怀疑,你的时政报道、经济报道是不是也这样?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某种程度上还使很多人变得麻木,削减了人应该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陈晓旭事件,我们首先要报道她的死亡及原因,表达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惋惜。如果像"鞭尸"一样挖出她生前的各种隐私,是很成问题的。 记者是寻求、挖掘事实;但对现在的很多娱乐记者而言,真实不在他们考量范围之内,他们第一关注点是明星的隐私,是能不能造成轰动。 张柠:当代社会舆论表达的言谈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文学语言(夸张、激情、修辞);一种是现代公民语言(简捷、清晰、明确)。公民语言应该是既有表达的自由,没有话语禁锢(包括游戏的乃至俗气的),又有公民自身的责任和尊严。只有前面那种,就是一种市井无赖语言,只是后面那种,就容易堕落为权力话语。 导致当代大众媒体语言的"偏至",乃至"偏执",当然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公民社会言谈方式的偏颇和不健全,使得我们的媒体更偏向表达的嬉戏,实际上是"嬉皮笑脸",是一种自由的摇头丸,最终只能变成一种话语符号的泛滥。 所有媒体都在一哄而上制造一种娱乐话题时,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用泛滥成灾的单一娱乐话语,来取代以前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原来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向了今天单一的娱乐话语,使得我们错过了其他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多元的、理性的、不同的声音对话。如果我们的空间更大一些,允许大家在一个理性层面上展开充分的讨论,可能会压倒那些八卦。现在的八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儿童"状态,你开玩笑、说胡话是允许的,说过头了就批评一下。而有理性分析能力的成人状态反而行不通。娱乐至死的、制造骇人听闻符号体系的文化传播方式大行其道。受众从中得不到更有意义的东西,不过是八卦而已。 反思:自律与自由的博弈 记者:从王菲生子、杨丽娟事件到陈晓旭出家,对于相对放开的娱乐报道,媒体自身是否应该有一些反思,加强一些自律? 王天定: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必然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要受到媒体关注、牺牲很多私生活。 我认为,受众最想从媒体上得到的是与个人、生活、决策有关的信息和有助于了解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媒体的关注,一是要有新闻价值,二是要与社会公众利益有关。如果既无新闻价值又与社会公众利益无关,同样不应该拿到媒体上去炒作。 国外的严肃媒体与大众媒体的界限较清楚,《纽约时报》就不需要去做娱乐八卦,有一批专门的小报去做。但我们的界限不明确。比如,我们以前评价某一张都市报的出现提升了都市报的水准,是都市报走向严肃化、精英化的标志,但从去年窦唯事件看,我们就搞不清它到底算一个精英报纸还是娱乐小报? 某一张主流大报报道的杨丽娟事件,也显示不出它所标榜的专业精神,我觉得它和小报没什么区别。对阿甘镇的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成了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阿甘镇这么多人,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丽娟?尤其是大段报道杨丽娟母亲的婚变、私生活,这完全是个人隐私。杨丽娟主动走到前台,她已变成某种公众人物,但媒体报道总有一个度的问题。 杨丽娟事件中,我觉得最恶劣之处是,一批媒体纯粹把杨丽娟一家人当作拉升他们收视率、发行量的一种道具。一个记者给了杨丽娟一家钱,声称帮她,这是不是把杨丽娟一家人当道具?但人不是道具! 我觉得,加强行业自律确实很有必要,现在媒体在娱乐、体育领域里的自由空间很大,但恰恰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一种相应的责任诉求;面对这种自由,我们有时无所适从,将自由变成一种狂欢,变成没有任何自律。 张柠:它已经被当成一个孩子,不是被启蒙后有责任心、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成人。全社会都是装嫩的、装孙子的文化,所有的媒介变得儿化、好像"童言无忌"似的。大家都愿意装扮成一个无须担当的"儿童",反正有"父亲"在那里管着。我们就这样沉迷在一种"人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健全的市民社会语言的成熟状态是通过市场来培育的。当然,媒体有打打闹闹的自由挺好的,但有时还是要想想稍微严肃的事情,真正的严肃是维护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现在是只有单一的声音,有的是板着面孔出现,有的是嬉皮笑脸出现,从单一的权力话语转向单一的娱乐话语,表现形态不一样,却展示出一种文化的两个不同侧面,这两个极端实际上是同一个深层逻辑。
 爱华网
爱华网